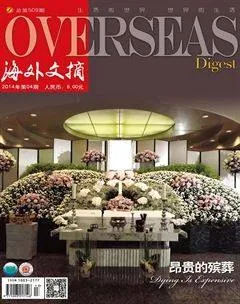熱特瑪麗的美食熱力


“再吃一個!再吃一個!”人群高呼。此時此刻,我恨透了他們每一個人,包括帶頭喊叫的那位——我老媽,她的臉上洋溢著驕傲和期待。
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在吹牛,說自己一定能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區第二屆年度熱“特瑪麗”節上贏得五分鐘競吃比賽的桂冠(熱“特瑪麗”,hot tamale,即墨西哥玉米肉棕,是傳統的拉丁美洲小吃,玉米葉子里裹著用上湯攪拌的玉米面、肉類、芝士或蔬菜,蒸制而成)。但是,令人作嘔的場面僅僅進行了三分鐘,我便發現自己在考慮要不要逃之夭夭。
這是我老家密西西比州格林維爾鎮的光輝時刻,上萬名觀眾在節日期間前來感受密西西比熱特瑪麗的美食熱力。小時候還不會講話前,我就愛吃它。咬一口熱騰騰的特瑪麗,感覺像是乘坐魔毯回到過去的時光。我仿佛又重回10歲,成為那個將世界拋在腦后、不管不顧地跑下大堤的魯莽少年。在我看來,熱特瑪麗就代表著家鄉,滿是辛辣而質樸的香味。
為了家鄉,我現在不能放棄。而且,我畢竟不是一個肚量平平的普通人,而是屢獲殊榮的吃貨:20年前,我曾在路易斯安那州牡蠣節的吃牡蠣比賽中,一路過關斬將,15分鐘內吃掉135只,獲得第二名。
肚子漸漸舒緩下來,我費勁地松開被肉粽弄得油膩膩的手,毅然決然地拿起下一個犧牲品,剝開外皮,表情痛苦地看著我興奮不已的老媽,將它一整個地塞進嘴里。
密西西比三角洲是一片傳奇的土地,出產過很多聞名遐邇的東西,從肥沃的沖擊土,到藍調音樂,再到包括沃克·珀西在內的數位作家。現在名聲在外的“大明星”要數熱特瑪麗了。它們在20世紀初隨墨西哥工人到來,然后作為一道深受喜愛的下午茶點被完好地流傳下來。一個密西西比熱特瑪麗的份量相當小,但熱量很高:肉糜、孜然、辣椒粉、大蒜和胡椒是每個肉粽中幾乎必不可少的幾種配料,將它們作餡,一起包在一張用玉米粉或玉米面精制而成的外皮里,再用一片玉米殼整個漂亮地包起來,長6英寸左右,呈管狀。它可能比正宗墨西哥產玉米肉粽要小些,但在味道和熱量上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般情況下,一種地方特色小吃,從新英格蘭的奶油蛤蜊濃湯,到洛杉磯的卷餅,再到路易斯安那州的麻辣小龍蝦,受到熱捧的原因和方式一目了然。被人街頭巷議的主角一定來自本地區,可大量出產,并且對當地人來說,價格便宜,容易做,好賣。可熱特瑪麗卓爾不群的原因似乎與密西西比當地無關,它來自完全不同的文化,堪稱最耗時、最難做的食品之一。我還記得與老媽及姐姐們一起花兩天時間嘗試自己包玉米肉粽的情形,整個過程可謂苦不堪言,最終作品是一些搖搖欲墜、味同嚼蠟的煮面團,漏著醬汁和肉糜。
為了改變我小時候愛在地上撿東西吃的習慣,老媽曾經把在辣椒汁里浸泡過的餅干灑在地板上,害得我誤食了一大口,哭聲連天。除了這件事之外,小時候我對食物最鮮明的記憶要數大嚼辣味熱特瑪麗了。睜大雙眼,盯著多汁、豐厚、飽滿、鮮美、鐘愛已久的美味,仿佛做夢一樣,小小的我就能一口氣吃下十幾個。長大后,對這份美味思念至極時,我會買機票飛回老家格林維爾小鎮,專程為了飽餐一頓,卻向家人和朋友們謊稱,我確確實實是來看望他們的。只要能吃上一個密西西比熱特瑪麗,我全豁出去了,甚至如你所知,不惜闖入一場競吃大賽。
在格林維爾的鬧市區,兩條平行的大街一直延伸到大堤,這條大堤是1927年為防止密西西比河水沖垮市鎮而修建的。在平常的日子里,它只是一處偏遠而略顯壓抑的市區中心,關閉的店面與營業的店面在數量上相差無幾。但是,在去年10月熱特瑪麗節期間,這里卻搖身一變,成了密西西比州最繁忙的商業區。成千上萬面帶渴望的人們充塞了大街,他們品嘗著新鮮出爐的熱特瑪麗,觀賞著居民自產自銷的藝術品,和著當地人鐘愛的布魯斯民謠翩翩起舞。節日期間,除了熱特瑪麗競吃大賽,還有烹飪大賽。最終,亞特蘭大市墨西哥太陽餐廳的老板兼主廚埃迪·埃爾南德斯,因烹制了三款不同風味的特瑪麗——肉質濃稠的手撕豬肉特瑪麗、淋上白色奶油醬的傳統特瑪麗,以及藍莓甜點特瑪麗——獲得烹飪大賽冠軍。
節日和比賽無疑是成功的,然而對我來說,這里或許是我到過的最糟糕的的地方,因為我每走不到10英尺,就忍不住要試吃一份樣品。密西西比熱特瑪麗的最奇妙之處在于它的適應性,像土豆泥一樣,它可以有無數奪人眼球的偽裝。你可以在特瑪麗里塞滿手撕豬肉、牡蠣、鹿肉、培根、鵪鶉、蝦、牛肉、羊肉、薩爾薩辣醬、藍莓、葡萄干,還有大量胡椒粉。對于熱愛者來說,吃特瑪麗不只是享用一頓飯,而是一種冒險。
前面幾個攤位上,有大肉量販店提供的油炸特瑪麗,雖然可口,但比起不含脂肪的斯巴達特瑪麗仍然黯然失色可。然后是魔鬼餐廳——好吧,吃了他們的特瑪麗,恐怕我也會變成魔鬼。雖然撐到不行,但我心中歡喜,因為它們確實是我從小到大吃過的最美味熱特瑪麗。魔鬼餐廳的老板佩里·吉布森告訴我,他制作特瑪麗已有21年,“因為吃得很多,所以我想,如果賣這個,肯定能賺些錢。”凡是市場出售的所有普通風味,在他的店里都能買到。除此之外,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家特瑪麗的玉米面外皮,一口咬下去,嘴里便回蕩著無窮無盡的玉米味,別提多帶勁兒了!再加上某種特定香料,我猜應該是肉桂吧,也就怨不得我吃得停不了口。
現在回到賽場。有人喊著:“還有兩分鐘!”此刻,我正努力把第12只特瑪麗塞進肚,最終它把我的臉和鼻子都弄得臟兮兮的。我知道我已經超過了左手邊的那位老兄,他雖然身材幾乎是我的兩倍,但卻落后我兩只之多。他的呻吟聲對我是巨大的鼓勵,卻無法讓擠在人群中的我的老媽滿意,因為我右邊那位四肢瘦長的公益辯護律師似乎仍有余力。恰在這時,我聽到給他“計數的人”說出14這個數字。我慢慢地解開另一只特瑪麗,盯著它看,時間仿佛在不經意間流過了幾個世紀。
“快吃!快吃!”老媽殘忍地懇求著。為了母親和家鄉,我拼了!不知不覺間我又干掉一個,然后又是一個。還剩下一分鐘,我第一次意識到,往我那毫無準備的肚子里無休無止地塞下一個個玉米面團、肥膩肉塊的后果,遠比塞進更易消化的牡蠣要嚴重得多。肚子正在醞釀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但我有能力將這場暴動暫時壓制。最后幾秒里,我精神抖擻地將第16只特瑪麗收入腹中,然后坐回自己的座位,滿懷勝利的喜悅。
我也許贏了,也許沒贏。當他們宣布最終被吃掉的特瑪麗數量時,我獲得了第四名,只比第三名少一只。亞軍是那位精瘦的律師,他吃下21只,然后宣稱他“再也不來了”。首屆的冠軍是22歲的饕客德克特里克·鮑迪恩,他的輝煌戰績為28只,足以青史留名,令人嫉妒得眼紅。所有人都稱鮑迪恩為“南方的大胃王”。
后來,在解決了肚子里的暴動后,我曾問鮑迪恩是如何訓練的?有什么制勝法寶?他沒有透露太多,只是說:“你真的必須愛上特瑪麗。”
[譯自美國《史密森學會》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