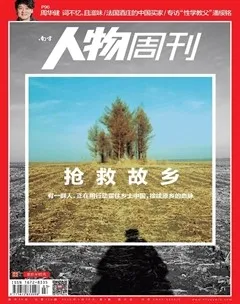Take Me Home,Country Road鄉(xiāng)村路,帶我回家


一
在窗戶邊上,我發(fā)現(xiàn)了那座獎杯。這是《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6月頒給藝術(shù)家歐寧的“青年領(lǐng)袖”獎杯。3年前,頒獎當天,我穿過車水馬龍的街道,去北京國貿(mào)旁邊的一幢公寓里接歐寧,那是他在北京的住所。如今,這座置放獎杯放在安徽黟縣碧山村的一個屋子里。歐寧把北京的房子退掉,搬到這里。這是由民國時期的徽派老宅改建而成:四合屋、別廳、廚房和院子。在北京,這等規(guī)模的房子屬于豪宅中的豪宅,在碧山,這棟房子的花費只夠在通州買兩居室。
歐寧的工作間里,桌上放著《天南》和《V—ECO》(他主編的兩本雜志)、蘋果電腦、半瓶洋酒、一頂帽子。帽子如今幾乎成為了他的標志。《碧山》是左靖主編的一本雜志書。今年其中一期的專題叫《去國還鄉(xiāng)》。封面上是一個人戴著酒紅色禮帽的背影。這是歐寧的背影,照片拍攝于碧山村的村口。那里有一座雕像——出生于碧山村的教育家汪達之。雕像由左靖和歐寧捐建。他們兩人是“碧山共同體”計劃的發(fā)起人。
我最早關(guān)注歐寧是因為紀錄片《三元里》。三元里是我在廣州短暫居住期間,去過的為數(shù)不多的城中村之一。2003年,歐寧受威尼斯雙年展委托,以三元里為對象,做了一個城市研究項目。“我從那時候開始意識到,城中村的問題與農(nóng)村有著緊密聯(lián)系。”為了弄明白這些問題,他開始閱讀有關(guān)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材料。他在書中遇到了晏陽初。“晏陽初的書深深打動了我,我在看他的書時,眼淚都流下來了。”
過的20年,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很瘋狂。資源重新分配,農(nóng)民失去土地,一部分人成為財富傳奇,另一部分人得到的是血淚故事,而大多數(shù)人開始在城鄉(xiāng)之間游走,他們已經(jīng)失去土地,卻無法被城市接納。這部分被漠視的巨大人群,誰來關(guān)心他們呢?這跟晏陽初當年意識到的問題是相似的,如何推動鄉(xiāng)村建設(shè)?如何提高民力與民智?如何平衡城鄉(xiāng)之間的矛盾,讓世人得以分享時代進程中的利益?
歐寧把自己在碧山村的家叫“牛院”,英文名叫Buffalo Institute,含有建設(shè)為一個農(nóng)村研究中心之意。在牛院一樓的壁爐旁,歐寧用PPT給我講了“碧山共同體”計劃。這是他在巴塞羅自治大學(xué)介紹此計劃時用英文寫的。歐寧出生于粵西農(nóng)村的貧困家庭,卻有著廣闊的國際視野。他向我推薦了一本叫《DEBT:The First 5000 Years》(債:第一個5000年)的書。當年他讀英文原著的時候,還沒有中譯本。此書作者大衛(wèi)·格雷伯想要說明的是:“5000年前,遠在貨幣出現(xiàn)之前,人類已經(jīng)在使用復(fù)雜的信用體系進行商品交易。從其定義上來講,一筆債既是一種信任的記錄,也是一種信任的關(guān)系。”
歐寧對于大衛(wèi)·格雷伯的理論贊賞不已。“我對自治感興趣,我會去研究人們?nèi)绾瓮ㄟ^交換勞動力而彼此互助,從而構(gòu)建一個無需貨幣的環(huán)境。這樣的想法是不可能在整個社會推行的,但在農(nóng)村社會的小范圍內(nèi)卻有推行的可能,這是我建設(shè)碧山共同體的初衷。”
“碧山計劃”發(fā)起于2011年,兩年的時間,對于一個社會改造項目來說,實在太短。讓人欽佩的是,歐寧真的住到了這里。他希望將來在“碧山共同體”計劃中推行“時分券”。“時分券”的概念香港已有,并有機構(gòu)進行實踐。什么是“時分券”?簡單說,大家各種勞動所付出的時間可以兌換成“時分券”,通過“時分券”交換勞動成果。這是沒有類似銀行的中間環(huán)節(jié)的更接近大衛(wèi)·格雷伯所說的5000年前人類就有的物物交換。
碧山村在皖南偏僻的田野中。這里不是旅游點,從黃山機場打車到過來需要兩百塊左右。拉我的安徽司機師傅一路上停下來問了好幾次路。“為什么不去宏村和西遞呢?這里有什么好玩的呢?”司機師傅不解地問了幾次。
按照網(wǎng)上搜索的路線,我住進了碧山村的豬欄酒吧的二吧。之所以叫二吧,因為豬欄酒吧的第一家店在西遞。在碧山村的油廠舊址,有正在建設(shè)的三吧。豬欄酒吧的主人是詩人鄭小光和他的妻子寒玉。
豬欄酒吧的名氣已經(jīng)不限于國內(nèi),它被寫入了Lonely Planet的中國旅游指南。我在豬欄酒吧所住房間的對面,是法國電影演員朱麗葉·比諾什住過的房間。“她在這里住了3天,她喜歡這里的一切,每天出去游玩,她都會趕回店里吃飯,對這里的飯菜贊不絕口。”寒玉說。
皖南的冬天是旅游淡季,田野里一片枯黃,偶爾飄來燒草的煙味。有時候,就我一個人坐在店里吃飯,窗外是掉光葉子的枝椏和平靜的池塘,魚兒游水。冬天是閑適的,店員大多來自碧山村。看著他們在白墻黛瓦的院子里摘菜聊天,你會產(chǎn)生“故鄉(xiāng)”之感。在碧山,我好幾次想起王朔《動物兇猛》的開頭:“我羨慕那些來自鄉(xiāng)村的人,在他們的記憶里總有一個回味無窮的故鄉(xiāng),盡管這故鄉(xiāng)其實可能是個貧困凋敝毫無詩意的僻壤,但只要他們樂意,便可以盡情地遐想自己丟失殆盡的某些東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個一無所知的故鄉(xiāng),從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這樣的一種故鄉(xiāng),有時并不是地理上的故鄉(xiāng),而是心理上的。讓人產(chǎn)生故鄉(xiāng)感的,有可能是你從未去過的地方。歐寧也有這樣的感覺。這也是他被碧山吸引的原因。“這里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從外面前來,購買和修繕舊宅,這樣的流動,不僅從物理上激活了更多的歷史遺跡,也促進了鄉(xiāng)村生活的復(fù)興。”在歐寧看來,“黃山景區(qū)風光奇美,但主要是一種‘被觀看’的旅游資源;而周圍的村莊,才是一種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它們沉淀著在行政概念上已不復(fù)存在的古老‘徽州’的種種細節(jié),那是一個時光深處的故鄉(xiāng)。”

這種對傳統(tǒng)心存敬畏,同時又追隨自己的心靈,營造出的自由舒適的居所,歐寧稱之為“心宅”。
“我和寒玉上中學(xué)的時候就認識了。”歐寧說,“當時我們都在《語文報》上發(fā)表了詩歌。”歐寧送了一本2013年秋季出版的《天南》給我,“入口”是寒玉的9首詩。
我入住豬欄酒吧的當天,詩人楊鍵正好從馬鞍山坐朋友葛亞平的車來到碧山。葛亞平也是歐寧在中學(xué)時代就結(jié)識的詩友。楊鍵無數(shù)次發(fā)出對皖南的感嘆。那兩天,他說得最多的一個詞是——皖南。楊鍵從馬鞍山來——那是皖東的一座工業(yè)城市。在豬欄酒吧的火爐前,他說起自己的寫作。讓我驚訝的是,他多年來所受到的困擾是他馬鞍山家里樓上腌咸菜的聲音。“樓上住的人天天發(fā)出很大的聲響,我說了多少次了,都沒用,他們說你去叫110來都沒用。”他非常無奈,只能這樣整天頂著腌咸菜的聲音寫詩畫畫。

他覺得到了皖南,能找到平靜。在皖南,或者說在碧山,你能真切感受到時序的變化。正好是冬至,天氣寒冷,樹木凋零,這讓徽派建筑的白墻黛瓦更像一幅水墨畫。
詩人龐培恰巧也來到碧山。于是有了詩人的聚會。冬至那天,飯桌上,忽然停電了。寒玉拿出手機,朗誦起穆旦的《冬》:“……我愛在冬晚圍著溫暖的爐火,/和兩三昔日的好友會心閑談,/聽著北風吹得門窗沙沙地響,/而我們回憶著快樂無憂的往年……”
冬至后的第二天,歐寧讓他的弟弟歐文帶我在村子里到處轉(zhuǎn)轉(zhuǎn)。這是一個出生于1986年的年輕人。頭一天晚上,他抱著吉他又彈又唱。世界在他面前剛剛打開,他能在村子里待多久呢?歐文說,他還是要出去的,現(xiàn)在是來碧山感受一下。當歐文帶我到村子里最大的祠堂時,遠在北京的女朋友與他通了很長的電話。通完電話,看得出來,歐文開始焦慮,“不好意思,我不能陪你逛了。”他說,“我得馬上去北京。”
他立即訂了當天從黃山飛北京的機票。這是現(xiàn)代社會鄉(xiāng)居的好處,即便遠隔千里,也能在數(shù)小時內(nèi)趕到。“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是北宋的時空觀。現(xiàn)在即便不能見面,覆蓋鄉(xiāng)村的網(wǎng)絡(luò),也能讓情侶們隨時聯(lián)絡(luò)。
告別歐文,我在村口見到了汪壽昌。剛才看到的那個大宗祠,變成鋼筆畫,掛在了他家的墻上。歐寧鼓勵汪壽昌寫書,把這些畫和文字拿去印刷。他看上去信心不是很足,但仍覺得值得一試。皖南的冬天冷入骨頭,我和汪壽昌坐在木盆里烤火,這是皖南獨特的取暖方式。
在汪壽昌家缺少光線的老宅里,他向我說得更多的是他的父親當年如何闖蕩上海灘的往事。他自己對于外部世界同樣充滿向往,“但是時代沒有給我這樣的機會。”所以,歐寧剛來碧山時,他感到不解。一個一直想走出鄉(xiāng)村的人,看到一個在中國大城市生活的后輩,選擇了到鄉(xiāng)村居住。“說實話,我并不能完全理解歐寧做的事情。”
這是上百年來做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人遇到的同樣的問題,怎么能夠讓這里的人明白他們到底要做什么呢?
歐寧則非常投入地學(xué)習(xí)鄉(xiāng)村邏輯和民間規(guī)則。他會向村支書和村民們請教。他會跟他們在不同的酒局上喝酒。有一次喝多了,騎著電動車回家,掉到田里,村民將他抬了回去。
黟縣的人口只有9萬多,這里的鄉(xiāng)土建筑卻保存得相當多,這是寶貴的接續(xù)傳統(tǒng)的資源,盡管這樣的傳統(tǒng)已然不多。從2011年開始,歐寧和左靖每隔兩年辦一次“碧山豐年慶”,邀請藝術(shù)家、作家、學(xué)者和鄉(xiāng)村建設(shè)者來到黟縣,進行研究和創(chuàng)作。有的人來到這里后,也開始購買老宅。
歐寧認為,隨著安徽省成為農(nóng)村建設(shè)用地流轉(zhuǎn)新制度的試點,宅基地可以入市交易,徽派民居的產(chǎn)權(quán)轉(zhuǎn)讓可以獲得更好的法律保障,來此購房的人將會越來越多。“如果農(nóng)村土地和房產(chǎn)全部落入那些只不過想來農(nóng)村度假、把農(nóng)村變?yōu)槌鞘械姆?wù)基地以賺取利潤的大資本手中,那將是另一場災(zāi)難。”歐寧說,“農(nóng)村需要更多逆城市化和認同鄉(xiāng)土價值的年輕人的回流,但購房歸田對于普通收入的他們來說仍是高門檻,如果農(nóng)村能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那對他們來說將是一個參與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更便捷的入口,這是‘碧山計劃’努力的方向。”
二
2012年10月,來自廣州的莫夜和他的藍田計劃團隊成員何子健、蔡遠河受邀參加了黟縣國際攝影節(jié)與碧山豐年慶。盡管到最后,大的豐年慶被取消了,莫夜還是完成了他們計劃——《撲克尋脈》。
他們將印有調(diào)查問題的撲克發(fā)給村民,既娛樂了村民,又做了田野調(diào)查。莫夜熟悉田野工作,他在大學(xué)學(xué)的是人類學(xué)。
公共空間是莫夜做田野調(diào)查時看重的。“各種各樣的公共空間功能相互補充,才能組建成一個完整的社區(qū)文化象征流通系統(tǒng)。在鄉(xiāng)村社區(qū)選擇合適的公共空間,將會更容易進入田野。一個社區(qū)或者一個族群,很可能都會有他們的公共空間,傳統(tǒng)的農(nóng)村有祠堂、廟宇、會館及其他地標建筑等。可以說這些建筑,是族群象征資本的‘容器’。”
社會學(xué)家布爾迪厄“象征資本”的理論給了莫夜許多指引。布爾迪厄?qū)ξ幕笳髻Y本的看法是,任何文化知識體系都有一種把社會權(quán)力體系引入并使之合法性的特性,而權(quán)力意識形態(tài)的結(jié)構(gòu)化將社會限制和支配剝奪合法化了。在布爾迪厄那里,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共同構(gòu)成象征資本。
“在一個較多年輕人外出打工的老人鄉(xiāng)村社區(qū)里,每個村民擁有的象征資本基本衡定的情況下,大樹下的公共空間可以算得上是一個文化象征資本流通的緩沖帶。這是供老人乘涼思考的地方,在田野工作中,你可以找他們聊天。”
2013年12月底的一個午后,莫夜開著車,帶我來到廣州海珠區(qū)瀝滘村的一棵大榕樹下——這是當?shù)氐墓部臻g。人們在看著地面的翻新。

莫夜不是他的真名,他不愿將工作與工作以外的事情混在一起。莫夜是他在開展關(guān)于文化保育的“藍田計劃”時所起的名字。
“為什么叫藍田呢?”莫夜說有藍圖的意思,他還提到了《夢田》這首歌——每個人心里一畝田。這首歌還唱道:每個人心里一個夢,用它來種什么?
莫夜和他的伙伴們給“藍田計劃”定下的宗旨是:“修復(fù)重建社區(qū)族群認同。藍田計劃將以行動組方式在鄉(xiāng)村社區(qū)尋找獨立試點,以服務(wù)鄉(xiāng)村社區(qū)原生文化藝術(shù)為參與方式,為青年人提供一個可以比較深入接觸參與傳統(tǒng)文化活動的平臺,并在過程中將鄉(xiāng)村尚存或重現(xiàn)的物質(zhì)及非物質(zhì)文化形態(tài)采集記錄下來,積聚成一定規(guī)模的資料數(shù)據(jù)庫,通過分享會、研討會和展覽及出版物形式在更大范圍的青年人群和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吸引關(guān)注,為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與延續(xù)尋找有價值的經(jīng)驗。”
吃完午飯,莫夜帶我去了瀝滘村。“未有河南,先有瀝滘。”瀝滘最大的姓氏是“衛(wèi)”。這里有多處衛(wèi)氏宗祠,最大的一間建于明代。
大宗祠上有副對聯(lián):“愛江海汪洋先入番禺開瀝滘;羨峰巒秀麗再過東莞辟茶山。”說的是此地衛(wèi)氏家族遷徙的歷史。
這副對聯(lián)引起了我的好奇,因為我的家人說,祖上可能來自東莞,而東莞衛(wèi)姓又來自瀝滘。所以,這里有可能是我這一脈衛(wèi)姓的上溯之地?“你看,我可能還給你先保育了。”莫夜笑著對我說。
莫夜對瀝滘村的文化保育工作已經(jīng)做了好多年。他幾乎每個星期都會來瀝滘一次,收集整理這里的歷史。在衛(wèi)氏的心和祠,莫夜進去之后,興奮地叫我去看,“這些東西還在。”這是當時做活動時,在墻上用粉筆畫的很多畫,既不損害文物,又能讓大家能看到這些建筑給大家的思考。墻上一條貫穿的紅線,“這是生命線的意思,寓意保護我們的傳統(tǒng),就是保護生命。”
這是“藍田計劃”在2010年3月份辦的第一個大活動:“瀝滘站——一個正在消失的坐標系”公益展。“細碎的鏡面映出龍舟的倒影,記憶中的地圖勾出曾經(jīng)的水鄉(xiāng);睡在地上的水車,破瓦、朽木、秧盤、蜆簍……所有這些舊物被放在年久失修、斷壁殘垣的古老祠堂中,展現(xiàn)后竟有一種震撼人心的效果。”這是當時媒體對于此次展覽的描述。
在2011年的TEDxGuangzhou大會上,歐寧偶然接觸到這些年輕人,便開始關(guān)注他們的工作和行動。“歷史意識和民間精神在他們身上提前蘇醒。”歐寧說。
這些年輕人進入城中村,收集遺失的關(guān)印、關(guān)帝經(jīng)、竹葉藏詩碑,在關(guān)帝廟進行送關(guān)刀的儀式,“試圖接續(xù)和傳承這一曾在南方非常興盛的民間文化”。
2013年,“藍田計劃”團隊在廣州方所進行了“保育之匙”的活動。歐寧參與了這次策展。莫夜一直強調(diào)觀眾的參與性。這又是一個類似“游園”的活動:在方所的空間內(nèi),放置54個分成6種顏色的保險箱,通過提示,觀眾可尋找藏于關(guān)帝經(jīng)拼圖中的密碼。“有些問題很難,沒有人全都答出來。”莫夜說。
與遠離繁華都市的徽州農(nóng)村相比,身處喧囂之地的廣州城中村,想保住傳統(tǒng)更為不易。“你看,那些都是紅砂巖。”莫夜指著瀝滘村巷中的地腳基石說,“這些都是老東西。”他已經(jīng)能從磚縫的紋理推斷出房屋的大致年代。巷子里還有一些散落的紅磚石,那是城市化車輪碾過之后的殘留。
莫夜帶我去了瀝滘村的一處診所,其實那是一座古廟,已經(jīng)被鋼筋水泥包裹著。他還帶我去了一座衛(wèi)姓人家的古宅,他曾經(jīng)跟宅子原來的主人聊過多次。衛(wèi)姓主人原本希望將此處來辟作博物館,但他不久前去世,“他的家人已經(jīng)將宅子賣掉。”莫夜說。這里不會有博物館了。
莫夜走在路上,看上去總是不太能快樂起來的樣子。“這樣的憂慮,一般都發(fā)生在被人目為保守的耆老遺民身上;難得的是,也有一些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投身于這樣的努力之中。藍田計劃,正是這樣一群懷德好古的后進們發(fā)起的一個長期的文化保育項目。他們成長于廣州,一個最早對外開放、啟動城市化進程的南方都會,也許正因身處歷史變動的漩渦,所以對傳統(tǒng)文化的凋敝和族群認同的喪失的體會更為深切。”這是歐寧在介紹“藍田計劃”時所做的論述。
莫夜帶我到衛(wèi)氏心和祠的時候,有人正在那里打乒乓球。1949年后,這里曾經(jīng)是生產(chǎn)隊宿舍、酒廠、養(yǎng)雞場……
瀝滘離市中心不遠,但沒有多少人知道這里的歷史了。“瀝滘”對于很多人來說,只是一個地鐵站的名字。就好像祠堂,這是一個可以參觀的地點,而祠堂的功能已不復(fù)存在。人們搞不清楚“我從哪里來,我是誰,我到哪里去”,或者說,許多人已經(jīng)不在乎了。這個社會到處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瀝滘站——一個正在消失的坐標系》的海報上有這樣的話:“歷史的文脈不會在我們這代斷裂!NGO組織藍田計劃集合了不可思議的力量,讓所有關(guān)心我們腳下土地發(fā)生過故事的人們,集合到一座荒草垃圾涂鴉密布的衰敗古建筑里。”

三
宗祠是一個村子保留鄉(xiāng)土傳統(tǒng)的重要標志。在福建連城縣培田村的一個早上,我看到一戶人家在宗祠進行了祭拜儀式,然后燃放爆竹,開始一天的活動。天氣已經(jīng)很冷,我在培田村里,沒有找到烤火的東西。“我們這里冬天不烤火,因為烤火容易得風濕。”吳家大院的小吳跟我說。管這里年輕的男性叫小吳,上了年紀的人叫老吳,肯定不會錯。因為這個村子里的人都姓吳。小吳原本在廈門的酒店工作,為了幫助家人經(jīng)營“吳家大院”,他回到了培田村。如今是旅游淡季,我入住吳家大院的時候,這座1600平米的明代院子里,只住著我一個客人。
穿過迷宮一樣的鄉(xiāng)間小路,我找到了培田客家社區(qū)大學(xué)。這是晏陽初平民教育發(fā)展中心和正榮公益基金會辦的社區(qū)大學(xué)。“直到現(xiàn)在,有關(guān)部門的一些人還讓我們摘掉‘社區(qū)大學(xué)’的牌子,他們覺得,你一個村子里的機構(gòu),怎么能叫大學(xué)呢?”潘曉婷跟我說。她是培田客家社區(qū)大學(xué)目前惟一在地的正式工作人員。“社區(qū)大學(xué)”在國外早已司空見慣,但在中國村子里出現(xiàn)的任何非官方的新事物,官員們都會報以習(xí)慣性的“警惕”。
選擇培田建設(shè)客家社區(qū)大學(xué),源于邱建生。他是晏陽初平民教育發(fā)展中心總干事,福建上杭人。“我們是不期然遇見培田的,盡管這朵客家奇葩已經(jīng)在我家鄉(xiāng)附近開放了800年,如果不是王麗老師在《中國青年報·冰點》上的文章,如果楊東平、梁曉燕兩位老師沒有邀我一塊去培田,我們可能現(xiàn)在也還不知道她的存在。必然在于,城市化、工業(yè)化的高歌猛進中,鄉(xiāng)村的身影正變得越來越暗淡無光,我們過去10年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實踐在洶涌的發(fā)展文化面前也已顯得力不從心,如何從鄉(xiāng)土文化的復(fù)興層面上對發(fā)展文化進行反思和修正,成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wù),而培田,恰在此時出現(xiàn)了。”
培田村已有五百多年歷史,村里有大量的明、清時期建筑群,2006年成為國家級文物保護村落。培田社區(qū)大學(xué)旁占地超過6000平方米的大夫第正在修葺。出生于培田的吳美熙站在屋檐下,給我講這座大宅的結(jié)構(gòu)和歷史。許多年前,他曾是培田小學(xué)的校長,而當時培田小學(xué)的辦公室是有千年歷史的南山書院。吳美熙退休之后,培田小學(xué)的教育曾是一派衰敗的氣象。
潘曉婷帶我逛了培田小學(xué)里的南山書院。這是培田村歷史上9個書院之一。在社區(qū)大學(xué)來到培田之前,培田小學(xué)已面臨撤校的困境,整個學(xué)校只有十幾個孩子。“我們當初剛來這調(diào)研的時候,有的年級只有一個孩子。”潘曉婷說。
培田小學(xué)的困境是中國鄉(xiāng)村教育的一面鏡子。教育的資源向城市傾斜,城鄉(xiāng)之間的教育也變得極度不平衡,而且,教育是統(tǒng)一制式的,差異化的鄉(xiāng)土教育幾乎是被忽視掉的。培田社區(qū)大學(xué)開始在村里組織夏令營,內(nèi)容多與傳統(tǒng)、農(nóng)耕、土地有關(guān),重點在于培養(yǎng)孩子們對于鄉(xiāng)土故園的價值認同。
“現(xiàn)在夏令營很受歡迎,報名的人數(shù)都超過原來限定的人數(shù)。”潘曉婷說。培田小學(xué)是潘曉婷帶我去過的村子里最熱鬧的地方,正值課間,同學(xué)們在操場上跑動嬉鬧,不斷有同學(xué)過來跟“潘老師”打招呼。
吳美熙對我說,要是過年時間來,能看到更多傳統(tǒng)。元宵節(jié)期間會有游龍,吳姓每一房出一條龍,非常熱鬧。而這樣的傳統(tǒng)曾經(jīng)中斷過,這幾乎是全國現(xiàn)象,舞龍舞獅逐漸從街巷上消失了。身處廣州的莫夜,他的“藍田計劃”中有一項就是組織醒獅隊,經(jīng)常聚在一起訓(xùn)練,他們希望讓傳統(tǒng)融入日常生活。
社區(qū)大學(xué)進入培田之后,經(jīng)吳美熙這樣的當?shù)乩先酥匦鲁h組織,“游龍”又開始回到培田的巷子里。
在我到達培田的第一個夜晚。村子里響起了鼓聲。這是培田的腰鼓隊。這并不是從來就有的隊伍,這是社區(qū)大學(xué)專門從河南請來的腰鼓老師給教的。
“要打破人心的隔膜,需要通過合作文化與合作經(jīng)濟的建設(shè),把村莊的精氣神重新激發(fā)起來。當村民從電視機前走出來,從麻將桌上走下來,參與到諸如文藝組織、合作經(jīng)濟組織的隊伍中來,他個人以及村莊的生命就悄悄地鮮活起來了。”這是邱建生的愿望。
邱建生希望互助并不只是停留在文化上。經(jīng)濟上的互助,會讓社區(qū)保持更持久的活力。社區(qū)大學(xué)給培田的定位是“生態(tài)村”。這是一條更漫長的道路。

在培田的一些小店里,會掛著印有“培田春耕節(jié)”的袋子。2013年,培田春耕節(jié)已經(jīng)舉辦了兩屆。春耕節(jié)以農(nóng)耕體驗為主,村民和市民共同參與,內(nèi)容涉及扶犁下田、鄉(xiāng)村工藝、小吃比賽、文藝表演等多個方面。
在春耕節(jié)上,吳來星放了他拍的紀錄片《培田土地記憶》。吳來星曾經(jīng)是培田的村支書,他是社區(qū)大學(xué)的積極支持者,希望自己的家鄉(xiāng)能夠有所改變,許多年前,還曾經(jīng)到華西村取經(jīng)。
下午4點,培田村老人公益食堂灶頭的大蒸籠里,已經(jīng)有煙氣開始蒸騰。村里一些獨自吃飯的老人,把飯菜拿到這里蒸。社區(qū)大學(xué)希望將老人們組織起來,建立他們自己的互助系統(tǒng)。
吳來星是公益食堂的負責人之一。他有著客家人熱情好客的傳統(tǒng),請我到他家做客,喝了許多當?shù)氐拿拙啤T谒奈葑永铮贸鲆淮筠麉鞘霞易V,這是寶貴的遺存,許多人從這里找到了與“故鄉(xiāng)”的關(guān)系。
吳來星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他喜歡講關(guān)于文化的任何東西。多讀書,在上了年紀的培田人看來,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養(yǎng)子不讀書,猶似養(yǎng)條豬。”吳來星讀得最多最細的書是《康熙字典》,他已經(jīng)反反復(fù)復(fù)讀過多遍。
吳來星正在寫一部120回的章回體小說《培田演義》。“山色消磨古今,水聲流盡年華”,是書中的詩句。
這是對培田的描述。爬上培田對面的山嶺,那里有一個觀景臺,可以看到培田的全貌。那些一片片連綴而去的灰黑色屋頂,很是壯觀。這是客家古民居的一種形式——九井十八廳。在另一處,是培田新村,完全是白色的盒子。
社區(qū)大學(xué)在培田的工作基本上處于社區(qū)動員階段,一個互助型社會系統(tǒng)的建設(shè)還需要太多時間。所有搞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人都會提到晏陽初,晏陽初是他們前行的動力。這種動力包括長時間的堅持不懈。
但除了搞鄉(xiāng)建的人群之外,許多人已經(jīng)將晏陽初遺忘了,“他成了故紙堆里頭的一個小人物。”邱建生對此非常感嘆,“思想是光,它總要從黑暗中透過來。晏陽初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是當我們回望20世紀的中國時,能夠使心靈感到溫暖的少數(shù)幾束光中的一束。今天,中國并沒有從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社會中走出來,廣大農(nóng)村的許多地方,‘愚、窮、弱、私’仍是主旋律,民智尚未全然開化,民力沒有得到足夠發(fā)揮,而民主建設(shè)任重道遠。”
在晏陽初的“定縣實驗”的鼎盛時期,那里聚集了數(shù)百位知識分子,其中有60位是博士、教授,晏陽初引領(lǐng)的平民教育當時被稱為“博士下鄉(xiāng)”運動。
晏陽初走的是改良的道路,但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激進主義的暴力革命思潮占據(jù)了上風。1949年后,晏陽初的思想在大陸被掃入故紙堆。
2010年,晏陽初逝世20周年,邱建生撰文《為中國找回晏陽初》,發(fā)表在《南風窗》上,他在文中引述了晏陽初的一段話:“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練兵、不是辦學(xué)、不是開礦,也不是再革命,我們?nèi)珖舷氯嗣袼毙璧模褪歉镄摹0涯亲运阶岳臓€心革去,換一個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會,有新社會而后有新國家。”
四
我到達海口博學(xué)村的“花梨之家”的時候,這個海南第一家民宿里,一個人都沒有,連主人都不在。我坐在院子的搖椅上等主人回來,兩只關(guān)在柵欄后邊的小狗不停地向我吠著。

這里的地貌真是獨特,一路上,各種熱帶樹木成片排闥而來。田野里的矮圍墻全用石火山巖壘砌。院子不遠處,有人在把火山巖搬上車,這能賣個不錯的價錢。
火山巖是不利于種植的。這里還缺水。為了解決水的問題,陳統(tǒng)奎曾經(jīng)多次給相關(guān)部門寫信,才得到解決。
陳統(tǒng)奎曾經(jīng)是《南風窗》駐上海記者,他也是村子里這么多年來第一個考上名牌大學(xué)的人。他畢業(yè)于南京大學(xué)新聞學(xué)院。如今,他的名片上一面印著:社會企業(yè)研究中心副主任;另一面印著:海南島博學(xué)生態(tài)村發(fā)展理事會創(chuàng)會理事長。
“花梨之家”是陳統(tǒng)奎將自家院子改造而成的。之所以叫“花梨之家”,是因為他父親陳召連在院子里種了六十多棵黃花梨。
博學(xué)生態(tài)村有一條山地自行車賽道,這是陳統(tǒng)奎建議修建的。我沿著這條火山碎石鋪就的賽道走了兩圈,沿途都是果樹,以荔枝居多,有的樹下能看到蜂箱。這里的荔枝蜜是往外推廣的主要生態(tài)產(chǎn)品。在快到村口的時候,我看到幾個年輕人在烤椰子玩。村口有許多椰子殼做的蜜蜂。陳統(tǒng)奎希望把這里建成“蜜蜂共和國”,這是受到臺灣桃米村“青蛙共和國”的影響。
2008年,陳統(tǒng)奎在北京逛萬圣書園的時候,淘到一本叫《再造魅力故鄉(xiāng)——日本傳統(tǒng)街區(qū)重生故事》的書,書中內(nèi)容為一群青年返回故鄉(xiāng),與在地青年發(fā)起再造故鄉(xiāng)的運動。日本建筑師西村幸夫在中文版序言中說:“中國的讀者若能像對待年長的老友、年邁的骨肉親人那樣,用溫柔的目光來看待自己的故鄉(xiāng),他就倍感榮幸了。”
70年代后期,日本開始了一場遍布全國的“社區(qū)營造”運動。“社區(qū)營造”指的是,居住在同一地理范圍內(nèi)的居民,持續(xù)以集體的行動來處理其共同面對的生活議題,解決問題的同時,也創(chuàng)造共同的福祉,居民彼此之間以及居民與社區(qū)環(huán)境之間建立起緊密的社會共同體,此一過程即為“社區(qū)營造”。整合“人、文、地、景、產(chǎn)”五大發(fā)產(chǎn)方向,是許多“社區(qū)營造”計劃的目標。
2009年,陳統(tǒng)奎去了一趟臺灣。他看到臺灣早在90年代就引入日本“社區(qū)營造”的經(jīng)驗。在南投的桃米生態(tài)村,陳統(tǒng)奎看到這個“社區(qū)營造”的典范。這讓他深受啟發(fā)。返回大陸后,他就開始著手在自己的老家海口博學(xué)村進行“社區(qū)營造”計劃。
剛從北京吉利大學(xué)畢業(yè)不久的陳統(tǒng)夸,成了哥哥陳統(tǒng)奎的得力助手。陳統(tǒng)夸是真正完全回到了博學(xué)村,成為了“民宿主人”。
陳統(tǒng)夸騎著他的電動車回來了。這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晚上,號稱“廚房男”的他做了兩個菜,就著一瓶啤酒,就算是跨了年。這里沒有電視,上網(wǎng)的信號也不好。“你會問我孤獨嗎?”我還沒問這個問題,陳統(tǒng)夸就先自己說了。“你說我孤不孤獨?”一晚上的談話,大部分話題是陳統(tǒng)夸喜歡的女生。你能感覺他正深陷暗戀的苦悶之中。他期待高速公路能盡快完善,這樣到海口市區(qū)就不那么遠。這里離市區(qū)確實遠了點,我打車過來,花了120塊。晚上,陳統(tǒng)夸彈起了吉他,其中一首是《老男孩》。“這說的不就是我嗎?”陳統(tǒng)夸抱著吉他說。
很多時候,“花梨之家”是陳統(tǒng)夸一個人在打理。我看到他一個人洗床單、做飯、洗碗、遛狗、修理木質(zhì)平臺、招待客人。你能驚嘆他的脾氣之好和能量之大。
小時候家里窮,哥哥陳統(tǒng)奎給過他很多照顧。所以,當哥哥要做這件事情時,陳統(tǒng)夸就回來幫忙了。客人沒來的時候,他會一個人坐很遠的車到海口市區(qū)打籃球。訂房電話是他的手機。
有時候,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有人來。元旦的中午,一群人蜂涌而來,在院子的草坪上燒烤,留下一堆垃圾,然后走了。陳統(tǒng)夸不喜歡這樣的方式,他認為自己辦的不是農(nóng)家樂,而是一處人們能有更多交流的民宿。所以,這里不提供麻將,不提供wifi。
“民宿”一詞源自日本,在臺灣得到發(fā)揚。民宿不同于傳統(tǒng)的旅館,也許沒有奢華設(shè)施,但能讓人體驗當?shù)仫L情、感受主人的服務(wù)。
2013年8月,第二屆返鄉(xiāng)大學(xué)生論壇在海口舉辦。陳統(tǒng)奎是該論壇的發(fā)起人之一。陳統(tǒng)奎曾經(jīng)發(fā)布一份倡議書《183鄉(xiāng)向前行》:呼吁海南籍大學(xué)畢業(yè)生回到海南的183鄉(xiāng)鎮(zhèn)創(chuàng)業(yè),開民宿、開咖啡店、搞有機農(nóng)業(yè)和社區(qū)營造,再造魅力新故鄉(xiāng)。
陳統(tǒng)夸很好地詮釋了他名片上印著的“民宿主人”的定義。但在很多村里年長的人看來,這幫年輕人像是小孩在玩游戲。在成立博學(xué)生態(tài)村發(fā)展理事會時,不同年齡段之間的人、返鄉(xiāng)青年和村民們的看法就出現(xiàn)了矛盾。這是所有做鄉(xiāng)建的人遇到的問題,如何適應(yīng)鄉(xiāng)村邏輯,這是必須要過的一關(guān)。
花梨之家的院子里有幾株長了9年的花梨樹,陳統(tǒng)夸的父親陳召連正在護理,他光著腳走在火山碎石上,“習(xí)慣了。”這些長了多年的花梨樹看上去仍然跟小樹苗似的。海南黃花梨之所以價值不菲,就是因為成長周期極長,有點像鄉(xiāng)建工作。
五
我在2014年的第二天離開海南,去往山西和順縣的許村。這一路采訪,我?guī)缀醵紱]事先跟受訪對象打招呼,遭遇誰就采訪誰,我覺得這更容易捕捉到日常生活的狀態(tài)。所以,當我到達許村的時候,發(fā)現(xiàn)季節(jié)對于鄉(xiāng)村建設(shè)也有影響。我沒找到留宿之地,因為冬天來了,沒游客,農(nóng)家樂基本處于歇業(yè)狀態(tài)。我到村子里走了一遭,看到許多改建過的老房子,看到戲臺,看到酒吧,看到工作室,都關(guān)著門,這是許多鄉(xiāng)村建設(shè)起步時的現(xiàn)狀。

楊麗萍在家鄉(xiāng)大理的房子似乎是某種隱喻,原本是詩意棲居的象征,后來成為了排污是否影響洱海的爭議話題
那一刻,我想到了另一個地方——大理。那也是一個許多人會生發(fā)“故鄉(xiāng)”之感的地方。許多人也去那里建房子,成為了常駐居民。洱海邊那些瘋長的房子讓你感到隱憂。你能感覺到某種變化。我在雙廊經(jīng)過洱海邊的時候,有人指著不遠處的地方告訴我,你看,那就是楊麗萍的房子。楊麗萍的房子似乎是某種隱喻,原本是詩意棲居的象征,后來成為了排污是否影響洱海的爭議話題。
有的“新都市主義”者說,別隨隨便便就回鄉(xiāng)村建個房子,愛護鄉(xiāng)土的辦法就是別長在那里住,讓故鄉(xiāng)成為“故鄉(xiāng)”,就拉開距離吧。有的人說得更直接,“故鄉(xiāng)”回不去,之所以稱“故”,那意味著屬于過去,而時光一去不復(fù)返。
在碧山村的冬至飯桌上,寒玉朗誦完穆旦的《冬》,龐培接著念了一位不知名詩人未曾發(fā)表的詩歌。這是一首關(guān)于“故鄉(xiāng)”的詩歌。詩中語句擊中人心。龐培念完后,大家的掌聲并不是客套,而是心有觸動。有幾句大致是這樣的:“昨天出生的人/今天是不可能再出生的/歸宿已提前到來/從此/誰給我故鄉(xiāng)/我也不要。”
詩人們圍桌念詩喝酒的情形讓歐寧感嘆,“這讓我仿佛回到了80年代。”許多人在回憶80年代的時候,會有“故鄉(xiāng)”之感,時間的概念有時會化為空間的概念。
晚飯后,大家聚集在豬欄酒吧的三吧,在爐火邊彈琴歌唱,喝茶聊天,直到夜深。
三吧位于碧山村北端的田野之中,不遠處便是群山,漳河流過,清澈見底,水草豐美。走出三吧大門的時候,半個月亮掛在天上,你能看到地里剛種下去的大片油菜,我想到了宮崎駿的《龍貓》,那些在暗夜的田野里瘋狂生長的植物,將你送上云端。塤,響了起來。
宮崎駿的電影也是那種能產(chǎn)生“故鄉(xiāng)”感的作品。他監(jiān)制的《側(cè)耳傾聽》中,甚至有一首改編成日文的歌曲《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曲中許多句歌詞變了,不變的那句是:“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母親出身大戶人家,父親是清末民初水師(海軍)好幾任艦長,從小接受開明的教育,已經(jīng)有機會拍攝生活照。上世紀40年代,母親成了廣州著名商業(yè)電臺的主播,而父親則是電臺的兼職高管。1962年2月18日,一家七口合影。
2013年9月19日中秋節(jié),四代同堂全家福。2013年歲末,母親安詳辭世。若有可能,下輩子還愿做她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