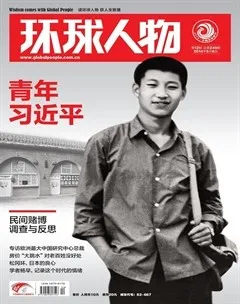邱震海:想做國師的時候,獨立性就喪失了


邱震海的語速很快。在遇到他感興趣的提問時,他會先說一句:“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有一個問題,他回答了將近20分鐘。“對不起,我說的有點多。”正當環(huán)球人物雜志記者想要問下一個問題時,他又接著說:“我再舉最后一個例子……”
這是邱震海的典型風格,不把意思說透他絕不會停下,就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直到觸及問題的核心——他把這種風格稱之為“解構”。在自己的兩檔電視評論節(jié)目——《震海聽風錄》和《寰宇大戰(zhàn)略》中,他反復呼吁理性探討“反日”、“戰(zhàn)爭”等公共話題,民眾因此對他褒貶不一,有人說他“愛國”,也有人稱他是“漢奸”。
他本人則并不在乎這些稱謂,他只關心“解構”問題時是否客觀與冷靜。2003年,中國宇航員楊利偉首次進入太空。香港《明報》采訪邱震海:“你有什么感受?”邱震海回答:“沒什么特別的感覺。”記者又問:“你難道不愛國嗎?你難道不為我們的民族感到自豪和歡呼嗎?”邱震海說:“我當然愛國,當然感到自豪,但沒有特別的雀躍和欣喜若狂。因為我也看到,一個有宇宙飛船的國家,依然有巨大的貧富差距等社會矛盾。”他解釋說,自己會對民族榮辱感同身受,但同時又在無意中保持了一種冷靜,“我會用這種更加平和的思維去看待問題。”
一邊罵娘,一邊奮斗
很難想象,今天以理性見長的邱震海,也曾經是一個叛逆少年。
邱震海的父母都是喜歡讀書看報的人,這給了他良好的成長環(huán)境。讀高中時,他很崇拜當過記者的語文老師,想追隨老師去讀新聞。可惜陰錯陽差,考大學的時候,邱震海進了華東師范大學德語專業(yè)。
“語言學是個非常枯燥的東西,學的時候恨透了,但學完之后影響很大。”邱震海說,研究詞法和語意的結構性分析法,對他后來從事時事分析有很大幫助。“我認為什么東西都有一個框架,有一個結構。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我也會試圖找到他們的內在聯(lián)系,架構一種關系出來。”
那時候的邱震海年少輕狂。當?shù)抡Z班團支部書記時,他領著同學曠課、抽煙、穿喇叭褲,最終被“革職”。有一個學期他曠了30節(jié)課,靠拼命寫檢查,才保住了學士學位。1984年本科畢業(yè)后,他又到同濟大學讀了3年碩士,之后留校任教。
1991年,已經29歲的邱震海突然決定放棄安穩(wěn)的生活,赴德國留學。回憶自己的這段經歷,邱震海說:“男人在35歲之前是沒什么想法的,當時想著去德國,無非是在大學里教教書,到電臺做新聞,去某個大公司做做中國生意,最差就是開個中餐館。這些在經濟上都很有吸引力。”邱震海記得,1990年,自己每個月的工資加獎金是114元。有一次,女朋友過生日,他們吃了一頓西餐就花掉60元。而到了德國之后,他的獎學金折合人民幣有5700元。
為了去德國,他“把菜刀都賣了”,沒錢買機票,就坐火車。列車穿過西伯利亞,走了9天9夜,才剛到莫斯科。在德國,他一邊研究傳播學,一邊給“德國之聲”電臺撰稿,還是上海《文匯報》駐德國特約記者。這種日子非常愜意,直到四五年之后,一股更大的危機感讓他惴惴不安。
“年輕人的抱負無非兩種,一是生活境遇的改善,二是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邱震海說。近距離接觸德國之后,他很快發(fā)現(xiàn)年輕人在西方很難有真正發(fā)揮作用的機會,因為西方社會已經很成熟了。反觀中國,還在爬山的過程中,充滿矛盾、辛苦、焦慮。而在邱震海看來,這種狀態(tài)是最美的,“因為你永遠覺得前面有希望,可以一邊罵娘,一邊奮斗。”
1997年,快要拿到德國永久居留權的邱震海,在人們驚呼“瘋了”的懷疑聲中,選擇離開。這一次,他決定到香港。“算是在大陸的門口徘徊吧,可進可退。最好的選擇是回大陸,最差就是回德國。”將近20年過去了,邱震海的生活空間基本固定在香港和深圳,“完全沒有回德國的想法了”。
“如果當年不回來,現(xiàn)在對中國的實際參與度就少了。”在邱震海心目中,中國社會依然是他渴望實現(xiàn)人生抱負的舞臺。
與出租車司機的一番對話
2004年,邱震海加盟鳳凰衛(wèi)視。3年后,他有了自己的欄目《震海聽風錄》。一開始,一些人并不看好一個長達45分鐘的深度討論節(jié)目,但邱震海始終堅信,中國觀眾需要這樣的節(jié)目,他們也有能力消化這種內容。事實證明邱震海的判斷是正確的,《震海聽風錄》剛開播的4期中,有3期創(chuàng)下了鳳凰資訊臺最高收視紀錄。
除了做節(jié)目,邱震海還寫書,并擔任一些大學的兼職教授。今年,一向以深度分析見長的邱震海換了口味。在他剛出版的新書《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中,他用很淺顯的例子,分析了轉型中國遭遇的很多社會問題,語言也非常直白。“這本書不是我原來的風格,我原來是很深奧的。”邱震海笑著說,“去年我寫了《中國成熟嗎》,我有幾個朋友說,晚上睡不著覺讀那本書最好了。”
邱震海說,新書是寫給高中以上學歷的人看的。之所以寫這樣一本書,源于他的一次親身經歷。2013年的一天,邱震海坐出租車從廣州白云機場去市中心,將近40分鐘的時間里,司機師傅一直與他聊中日關系。
“我現(xiàn)在就盼著打仗。”司機說。
“打仗有什么好的?說不定就家破人亡了。”邱震海問道。
“打仗好啊,這樣就可以重新洗牌。不然像我這樣的人,可能到80歲還在開出租車。”司機的回答非常坦率,這讓邱震海感到很吃驚。
他試著讓這位司機理性看待后果:“不打仗,你說不定還能開個出租車;一打仗,你不但出租車開不成,說不定還得上前線,命都沒了。”
“命沒了就沒了。我不像很多人有房子、有錢,更不像貪官有財可貪。我是無產者,無牽無掛,還不如索性搏一下。”司機的回答讓邱震海感覺越來越沉重,而真正讓他沉默的是司機下面的話:“我告訴你,今天的中國,有我這樣想法的人,在社會底層有很多。”
這讓邱震海意識到,作為一個媒體人,如何淺顯直白地和普通大眾對上話至關重要,因為他們是社會的基礎。另一方面,這讓他看到轉型中國的“立體型困惑”。“這位司機就是一個例子,他對戰(zhàn)爭的熱衷,與其說是在表達愛國情懷,還不如說是在宣泄對個人命運的焦慮。當今的中國是內政連著外交,經濟連著社會,社會連著政治,是一種立體式的結構。一個經濟問題沒整好,就變成政治問題了;一個外交問題沒解決好,就變成軍事問題了;司機對經濟和民生的焦慮,一不小心就會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領域。而這些領域的交界處就像城鄉(xiāng)結合部,是最亂的地方,也最容易出問題。”
在邱震海看來,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缺少能夠“解析中國”的人。“過去我們談的是一個個分離的領域,專家的研究領域也是很清晰的。所以,我們不缺各個領域的專家,缺的是能夠把各個領域的交界處講清楚的人。”
體制造成的困惑究竟占多少
環(huán)球人物雜志:您覺得誰應該承擔起“解析中國”的責任?
邱震海:本來應該由公共知識分子來承擔。但“公知”這個概念在今天的中國被污名化了。這也跟民間情緒有關,民眾對公知有些不理解;也跟某些所謂的“公知”自身的惡劣表現(xiàn)有關。現(xiàn)在一提公知,就是盲目相信西方價值觀的、對中國充滿惡意批評的、對中國問題也沒有實際認識的,甚至是在網上炒作情緒的一幫人。這離公知本來的含義差很遠了。
環(huán)球人物雜志:那您認為應該如何定義公知?
邱震海:所謂的公知是說他本身是知識分子,有獨立性,但他又能夠用老百姓聽得懂的方式來解析、傳播一些東西。他區(qū)別于象牙塔里的純學者,后者是高深的,不接地氣的。公知是走向民間的,但又有獨立性、超越性、有思想的感召力。
我認為互聯(lián)網時代有3種東西很寶貴:資訊、知識、思想。今天中國不缺資訊,不缺知識,缺的是思想,有力量、有邏輯、有理性基礎的思想。公知最主要的任務是要提煉、發(fā)展、傳播思想,傳播尤其注意要放到正確軌道上。
環(huán)球人物雜志:什么是正確的軌道?媒體又該如何發(fā)揮作用?
邱震海:現(xiàn)在我們談到媒體的時候,很多人會表現(xiàn)出一種無奈,認為媒體的手腳被綁住了,說這跟體制有關系。但體制造成的困惑在我們整個的工作環(huán)境中究竟占多少?我認為只有5%,最多只有10%。我們每天觸及和解析的大量問題,都是轉型期中國的問題。老百姓面臨的問題,跟中國政府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不分體制內外。有些矛盾,老百姓沒弄明白根源,以為是政府的問題;政府也不了解全面情況,以為是有人在煽動情緒。
我個人的經驗是:當你用很激進的語言去迎合老百姓的時候,可能你還沒有觸及問題本質就被叫停了。當你用很溫和的語言,你一樣可以很犀利,甚至可以觸及到問題核心,而百姓、學者、政府也都很有興趣聽你說話。因為你是在解構問題,而不是在煽動情緒。媒體有責任去營造一種理性的公共討論文化,一個社會具備了這種文化的時候,才是成熟的。
說不了真話,也絕不說假話
環(huán)球人物雜志:您在新浪微博上寫:若不能影響社會,至少應守住公正客觀。
邱震海:這是我對自己職業(yè)的要求,也是做人的要求。中國有句古話“先做人再做學”,如果人品很差,做學問就只是一種工具了。做評論,我認為有三種境界:第一種是最高境界,一般人達不到,我也達不到,就是在歷史關口起到引領作用,甚至是改變作用;第二種是對事物能提出客觀的解釋,比如把朝鮮問題六方會談的細節(jié)和來龍去脈講清楚,不要含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場;第三,如果啥也做不到,至少要守住底線吧。公正客觀,不說瞎話,不懂得不要亂說,違心的假話也不要說。我的底線是,決不允許商業(yè)介入,否則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哪怕說不了真話,也決不說假話,無奈不是良心泯滅的代名詞。
環(huán)球人物雜志:您說的第一種境界,影響歷史的發(fā)展是您所追求的嗎?
邱震海:當然是這樣。不過這個東西很難做到,也很難量化,也許有些東西已經在發(fā)揮作用,但我們無法去衡量。而且千萬不要自以為是,認為有些改變是因為你的評論而發(fā)生。我聽到有些同行說,中央現(xiàn)在做出這個決定是看了我昨天的節(jié)目。哎呀,我說,不要感覺太好,中國聰明人很多。我們只是發(fā)出一種聲音而已。
環(huán)球人物雜志:您會預設“潛在受眾”嗎?有沒有想過影響高層決策?
邱震海:有時候會有。但我不會想要去做國師。我們有的同行說,我的節(jié)目只給一個人看,他心目中那個人就是總書記。可當你想要做國師的時候,你的獨立性就喪失了。從我的角度來說,我認為這定位完全錯了。我把我節(jié)目的受眾群定位在有一定知識、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他們是各個行業(yè)里的中堅力量或者說精英階層,年齡在25歲到60歲之間。這些人是中國未來的力量所在,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喜和憂都牽動著中國未來的方向。
環(huán)球人物雜志:您對自己的定位又是什么呢?
邱震海:學者型的媒體人,這可能是我的一個終身事業(yè)。觀察社會、監(jiān)督政治成為我的終身使命。但我永遠不會去期待,自己明天會去改變一個政策,也不會設定自己大富大貴。我的目標是經濟上能夠相對獨立,思想上又能去影響一部分人,在這個過程中找到內心的滿足感,我認為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