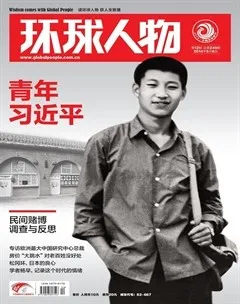用腳寫成的傳記

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尋找·蘇慧廉》,被多家媒體都列入到2013年的年度好書中。在這本著作的影響下,蘇慧廉這個名字,在這一年來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道。
蘇慧廉是個英國人,傳教士,教育家,后來更成為歐洲一流的漢學家。1883年,22歲的蘇慧廉漂洋過海來到中國。那時的中國人稱自己的國家為天朝,是世界的中心。蘇慧廉記下了一個故事。一個中國男孩在教會學校接受人種知識的測試,老師問他:“黑人是什么膚色?孩子。”“黑色,先生。”“不錯,那美國印第安人是什么膚色?”“紫銅色,先生。”“對極了,英國人呢?”“白色,先生。”“現在問你,中國人是什么膚色?孩子。”“人的顏色,先生。”孩子驕傲地回答。
可想而知,金發碧眼的蘇慧廉在中國人眼中如同怪物。可他依然定居溫州,布道傳教。未婚妻追隨而來,他的孩子也出生在這里。直到1907年離開,蘇慧廉一生最好的時光都在中國度過,而那卻是中國近代最動蕩的歲月,甲午中日戰爭、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別說蘇慧廉,即便中國的當權者,也未必知道自己的命運。
相比起“傳教士蘇慧廉”,他在中國留下的更清晰的身影,是“教育家蘇慧廉”。定居溫州二十余載,他設立過書院、禁煙所,為溫州留下了第一所西醫院、第一所西學堂,一本溫州方言版《圣經》和便于外國人學習中文的《四千常用漢字學生袖珍字典》。他還將《論語》翻譯成英文——該譯本成為牛津大學最認可的經典作品,至今已印了30多版。此外,蘇慧廉曾在一戰前線服務華工,代表英國處理庚子賠款,使千萬英鎊退還中國。
由于蘇慧廉在教育方面的杰出才能,他被聘為山西大學堂的總教習,并在返英后受聘于牛津,成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他的學生,正是后來大名鼎鼎的美國漢學泰斗費正清。蘇慧廉的女兒長大后,回中國創辦了培華女校,這是林徽因的母校。胡適、晏陽初、蔣廷黻、蔡元培,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都與蘇慧廉有著或近或遠的聯系。
蘇慧廉來中國,不遠萬里。《尋找·蘇慧廉》一書的作者沈迦對蘇慧廉,也可以說是千萬里的追尋。今年45歲的沈迦是土生土長的溫州人。小時候,他總跟著祖母去教堂,主殿有6根黑色的大圓柱,非常醒目。老人們說,那是從英國運來的。“誰會把木頭不遠萬里運到中國小城?”小沈迦心里埋下了問號。長大后,在報社工作的他有次去圖書館查資料,知道了蘇慧廉的名字,躍入腦海的第一個念頭竟是“運大柱子來的會不會就是他”。
2007年,沈迦下決心要把蘇慧廉寫出來。一下筆方知難,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地方史、教會史查遍了,連蘇慧廉的簡歷都拼湊不全。沈迦想起了當年采訪寫作課上老師的教導——好文章是用腳寫成的,于是,他開始了自己的尋找之路。
《尋找·蘇慧廉》的書名仿佛就在宣告作者寫作方式的不同,這既非一般意義上的人物傳記,也非以作者為中心的尋找過程,而是將二者雜糅。書中以時間為線索,拼貼出作者所能找到的所有資料,從各個角度還原蘇慧廉的人生歷程。沈迦是歷史門外漢,卻寫出了比圈內人更好的文章。
40余萬字的著作里,一半篇幅是引文,注釋便有千余條,有的讀者可能會覺得讀起來頗為費解。對此沈迦說是故意為之。“中國的歷史,離今天越近竟然越模糊。我只能盡量用這些來自第一手、并用第一人稱記錄的材料,提醒讀者,這才是當事人眼中實實在在的歷史細節與角度。”
在書的自序中,沈迦寫道:“政治與經濟在其間交織往返,纏纏綿綿,歷史只能以一種混沌的姿態向前寸進”,而他的寫作則是“試著想借蘇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國一個世紀的歌哭”,“給今人回首百年時一個可資分析和詠嘆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