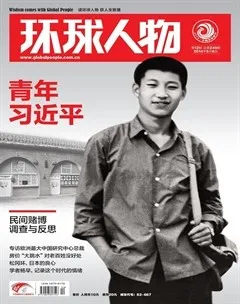學者楊早,記錄這個時代的情緒

人物簡介:楊早,1973年生于四川富順,北京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現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著有《野史記:傳說中的近代中國》《民國了》等著作。
英國政治哲學家以賽亞·伯林將學者分為兩類:“狐貍型”學者和“刺猬型”學者。簡單地說,前者思維活躍、興趣廣泛,是對很多個別事物都有獨到研究的人;后者則思想深邃、善于集中,是要找準一個點鉆研畢生的人。按這個劃分,學者楊早無疑偏向于“狐貍”——他關注的東西很博雜:從文學到歷史,從傳統到現代,都作文著述,快意評點。
學術研究以外,楊早在公眾媒體平臺上也很活躍。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和他約采訪時,他一開始建議用微信進行訪談,倒是記者不夠新潮,保守地選擇了當面對話。采訪過程中,他還向記者展示了他新近下載的一些熱門App運用,分析它們爆紅背后的社會心理,興致盎然。
從2005年起,楊早與他的同事薩支山一起,針對每一年的熱點事件和公共話題,約請專門作者進行深入淺出的歸納和解讀,主編了年度書系《話題》。到2014年,《話題》已連續出到第九本。這套書既有學養,又不艱深,慢慢積累了大批固定讀者。
《話題》的緣起
《話題》的緣起要追溯到2005年12月17日。那天,楊早和同事薩支山、施愛東一起,在北京通州區的一家咖啡館聊天,討論2005年的一些熱點事件,如臺海局勢、中日關系、房價上漲,等等。三人越聊越有興致,碰撞出不少火花,后來覺得,這些觀點白白流失了太可惜,應該把它們記錄下來。楊早就建議:為什么不把它弄成一個年度的文化評論集呢?
第二天,他們便行動起來,先是擬定大概的選題。定位很明確:這不是一本年度文化盤點,不會像新聞報道一樣事無巨細、面面俱到,而是要選擇一些令他們有感而發的切入點,從個人角度探討出一些新意來。在這個訂計劃打草稿的階段,楊早在心里畫了一張藍圖,要把未成形的這套書做成一個系列,每年出一本,一直弄下去。
想法和選題有了,找誰去寫呢?一開始,施愛東提出一定要是博士,而且是文學博士。這在后來的操作過程中雖然沒有成為絕對的準則,卻為選擇《話題》作者立下了參考標準:必須是一群有學養,經受過學術訓練,思想立場都有見地的人士。
《話題2005》新鮮出爐時,已經到了2006年夏季。全書由9位作者寫作,其中包括了“超女”、芙蓉姐姐、房價等一系列問題。這些2005年轟轟烈烈的熱點,到此時已成明日黃花。無論從新聞還是出版來說,這都是大忌,但楊早卻對這種“反季節行動”充滿信心。因為他堅信,這本書提供的不僅僅是“資訊”,更重要的是“看法”。比如,《“芙蓉姐姐”的迷思》一文作者張慧瑜是北京大學戴錦華教授的博士,他把“芙蓉姐姐”當成研究對象,梳理她的誕生及其流行過程,分析不同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總結這個現象背后的社會文化心理,并深層次地歸納出“芙蓉姐姐”爆紅所反映的中國權力關系的變化。文章像博士論文一樣扎實,卻不像論文那么晦澀和難以理解,全文行云流水,是真正意義上的“深度解讀”。
照楊早的話說,“《話題》系列,實際上就是一批學者在觀察與記錄中國當代社會生活。”獨立的立場是《話題》團隊一直堅持的寫作原則,“沒有利益集團收買一批‘無用的’博士”,楊早打趣,“這反而造成了我們的獨立立場。”
繪制“感受”的時代拼圖
《話題》系列每本封底上都會有一句話:“列譜系,破虛妄,播新知。”這是楊早他們編寫這套書最強調的東西。
“列譜系”,把一個事件放到歷史中去觀照,追根溯源,挖掘“動態事件背后的靜態過程”;“破虛妄”,即打破一些大眾媒體生產的神話和偏見;“播新知”,有些問題在專業學術領域已成為常識,但在公共領域完全還是陌生的,他們就去努力打破這堵“墻”。最能表現這九字要求的是2010年曹操墓事件。楊早他們調查后認為,曹操墓確定是真的,但在媒體上,質疑的聲音卻占據上風,為什么?《話題》中作者歸納的觀點是:因為地方政府過度介入,加劇了官民對抗的情緒,專業知識和理性判斷反而缺席。
2012年,《話題》寫作團隊開始提煉“年度關鍵詞”,那一年是“去魅”,2013年是“觀弈”。“2012年,從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到韓寒被質疑,甚至《甄嬛傳》引發的后宮文化流行,等等,很多東西都在褪去光環,露出本色。”楊早對記者這樣解釋“去魅”一詞的含義。至于2013年的“觀弈”,“其實就是一種社會心態——大家都如同在看別人下棋,有很強的無力感。”而對于年度詞匯的選擇標準,楊早說:“當然沒有詞可以規范所有事件,但有一個詞也許可以代表大多數事件。在選擇年度詞匯的時候,其實就代表了我們這個團隊對社會情緒的大致認知。”
《話題》也分“大小年”,比如2008年就是一個大年, 奧運、抵制家樂福、汶川地震、金融風暴等,都發生在這一年。而《話題2009》則被網友評論為“最沒勁的一年”。
在記錄大事件時,楊早他們有著自己的角度。比如《話題2008》中,寫奧運重點在于“錯位的想象”,講述西方媒體怎么報道奧運,中國媒體怎么看待這些報道,在不斷地互動之中,文化的錯位被放大。再比如,書寫因奧運火炬傳遞引發的抵制家樂福事件時,《話題》選擇了《中國抵貨運動103年》這個角度,從1905年中國第一次抵制洋貨運動開始,追溯了歷次運動的“成效”。得出的結論是:“抵制洋貨對外國經濟影響并不大,甚至馬上就會有一個反彈。最后落到實處的往往是中國人和中國人的矛盾,而不是中國人和外國人的矛盾。”楊早說,“我們的預言是正確的,2013年釣魚島事件后出現了‘砸車’現象。最終損害了誰的利益?誰來承擔這種成本?其實很明顯。”
在連續9年的《話題》編寫中,楊早越來越強調情緒的把握,對于大事件引發的公眾反應和思想撞擊,他概括出“哀慟、憤怒、驕傲、惶惑、反諷”5種情緒。事實上,關注并記錄大眾思想情感的軌跡,正是《話題》的初衷。楊早他們在最初策劃時就發現,以往媒體平臺稀缺,能在媒體上說話的往往都是知識分子和精英,找不到普通人對事件的即時反映。“事件留得下來,但大眾情緒很難把握。所以,我們其實是在為后人留一份資料,以此來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心態和情緒。一人之見聞,當然偏頗,然而匯集起來,或許就是一張有關情緒的時代拼圖。”楊早說。
在楊早看來,歷史真實永遠不可能追尋到,但學者可以記錄情緒,把媒體和公眾對事件的反應留下來,“也許一年兩年,你還看不出它的價值。但今天,當我再回頭看這9年,就覺得很有意思,整個社會對很多事情的寬容度不一樣了,時代已經發生了很鮮明的變化。”
不忽悠學問
從連續9年編《話題》就能看出,楊早不是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者,他不想寫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學術論文,而是要讓學術文章和大眾文章有所結合——他希望自己寫出的學術文章不枯燥,大眾文章有深度。“靜坐書齋的知識分子,是非常寂寞、尷尬的,嘔心瀝血寫出來的論文,可能面臨著無人欣賞、無人回應的境遇。而寫一篇博客、一條微博,馬上有讀者回帖,你就能獲得一些滿足感。”但是,他又反思:“不得不承認,微博讓人太快得到滿足,缺乏一個沉淀的過程。”
楊早出生于四川,父母都是高校知識分子,父親是教文學的,母親在圖書館工作。小時候,楊早常常看到父親寫論文時的痛苦情狀,抓耳撓腮拍腦袋,最后耗盡心力鉆研出來的學術成果,卻總是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頭,能影響到的人著實有限。父親從來不勸兒子繼承自己的衣缽,倒是希望楊早以后多干一些實事,從事經濟或法律的工作,真正和社會緊密相連。所以,盡管楊早有學術理想,但從中山大學畢業后,并沒有繼續讀研,而是先從事了幾年媒體工作,這段經歷也影響到他后來做學問的方向:把新聞和歷史相結合,帶著明顯的媒體思維。
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時,楊早師從中國現代文學領域的著名學者陳平原教授。導師要求他寫文章要“能夠把一些重要的東西壓在紙背下”。當研究生快畢業時,楊早提出要考博,陳平原并沒有立刻同意,而是對他說:“從事社會批評,當一個評論家,對社會也是很重要的,并不一定要搞學術。只是,如果讀了博士,又不從事學術研究,未免有點可惜。”
楊早最終還是堅持選擇了學術之路,跟著陳平原教授學了7年,“導師不僅在知識、眼光等方面影響到我,最讓我受益的,是他對待學術問題始終保持冷靜、懷疑的態度。”2005年畢業后,楊早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有一次,在電梯口碰到一位老學者。他問起楊早從哪兒畢業、是誰的學生,末了淡淡說了一句話:“陳平原的學生,想來不會忽悠學問嘍!”這句話,楊早一直銘記多年。
看楊早自己撰寫的作品,也能感受到這位才子的功底與個性。他以高芾為筆名寫作的《野史記》瞄準了近代中國,全書分為“政事本紀”“報人世家”“大學列傳”“文壇行狀”四輯,似乎有意和司馬遷開玩笑。他力求將舊史寫出新意,如寫一件奇事,多用旁觀者視角;寫一段逸聞,會借兩人對話來交代,新聞報道體、回憶錄體、民間故事體、獨白體、小說體,交互著使用,繪聲繪色,讓人感覺那個逝去的年代依然與我們骨肉相連。
楊早的另一本著作《民國了》,則以新聞特寫的方式寫辛亥革命,盡可能地讓筆貼近現場,還原氛圍。讀這本書,仿佛在讀楊早從1911年發回來的關于辛亥革命的現場報道。
《民國了》出版時,正好趕上了方興未艾的“民國熱”,對于兩年前那場席卷全國新聞界和學術界的熱潮,楊早說:“中國人對那段歷史感興趣不奇怪。民國是中國人的第二次童年,就像馬克思說過希臘是人類的童年。民國的知識分子待遇高,政治局勢變化快,戰亂頻繁,但它的魅力就在于亂,充滿無限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研究民國,楊早有自己獨特的方式。他在圖書館里專門抄報紙,抄了1912年整整一年的《申報》,共100多萬字。之所以那么做,是他不相信僅僅通過已經出版的那些歷史書籍,能夠真正觸摸到當年的精神脈搏。而當年的新聞紙片,反而讓他感到更為鮮活、更為真實。他把自己想象成一個1912年的普通知識分子,通過翻閱當時的報紙,去“部分抵達”百年前的情境之中,體味普通人的心態和感受。“有時我覺得我簡直像一個穿越者,在文字構成的世界中穿行摸索。”
楊早不太希望遵循一條現在學者發展的通常軌道:多寫論文、多參會,慢慢變成權威。他更愿意選擇自己鐘愛的研究課題,哪怕走的是一條更具風險的道路。“我最怕重復的生活,每天感到很強的無力感。”在他的博客上,偶爾會見到一些詩句,他自己寫的也好,引別人的也好,都是“民氣昂昂狂若舊,島圖汲汲議難休”“更能消幾番風雨?最可憐一片江山”這種慷慨激昂型。他寫過一句話:“吾之大患,在吾有身。如果人生不追求意義感,過得渾渾噩噩,或許也很幸福吧?”看來,相比起幸福,楊早追求的更是人生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