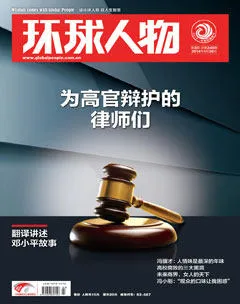春運,在怨聲中埋頭前進
春運仿佛一個神奇的開關,只要摁下它,整個中國就一下子切換了模式,集體踏上歸途。無論是大街上騎著電動三輪車的快遞小哥,地鐵口招攬貼膜生意的年輕小伙,還是小區里往返巡視的保安大叔,餐廳中端盤送菜的女服務員,城市尋常角落這些平日不起眼的“小角色”,突然間有了一致話題:買到回家的票了嗎?
有人說,“鄉愁是一枚小小的火車票”,年年歲歲怕春運,歲歲年年票難求。每年此時,鐵路部門總要被推上風口浪尖。雖然“鐵道部”已成為歷史,但排隊購票的焦慮表情、候車大廳的擁擠不堪、行李架上的大包小包,依然每年準時見諸報端,刺激著人們緊繃的神經。
不過,一樣的春運有了不一樣的抱怨。短短幾年里,人們對春運的“吐糟”明顯“更新換代”了。從前抱怨站在天寒地凍的火車站廣場上通宵排隊有多冷,現在“吐槽”坐在辦公室里刷12306購票網站有多累;從前抱怨民警為什么不管管那些霸占住售票窗口的“黃牛”,現在質疑“網絡黃牛”利用專業軟件刷票囤票究竟歸誰執法;從前大聲疾呼火車票實名制以遏制倒票行為,現在則爭議倒手實名制車票到底是倒賣車票罪還是代購行為;甚至就在去年,還是怒斥12306購票網站登錄不上去、訂票電話打不進去,而今年已在指責網站登錄后反應遲鈍、電話打進去后“系統繁忙”……
雖然這一切都會被數億回家人歸結為一句憤怒的“鐵路部門無能”,但毫無疑問,人們對春運的新抱怨、新不滿,正是時代變遷、社會進步的注解——從擠綠皮車到搶高鐵票,從“人肉排隊”到“網絡購票量近50%”,從“團體票面向200以上的企業”到“5名務工人員即可自行組團買團體票”,中國的春運在怨聲載道中埋頭前進。這背后,是包括路基、橋梁、鋼鐵、機車、通信、電力、環保在內的諸多基礎設施建設的進步。可以說,春運的每一個小進步,都是靠整個國家綜合實力向前邁進一大步支撐起來的。
追根溯源,就連“春運”這個詞本身,都是社會進步的產物,是記錄中國前進的“大腳印”。1981年3月,“春運”二字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的新聞標題上,此后便作為觀察中國的一個獨特窗口,每年都未缺席。試想,假如沒有改革開放,如果整個社會仍是“鐵板一塊”、人口遷徙仍被嚴格控制,“流動”就不會成為人生常態,那么“春運”自然不會變為國家議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春運雖然伴生著許多問題,卻也代表著機遇、活力,孕育著希望、夢想,它映照著時代的進步,也意味著改變的可能。
翻越時光的年輪,1981年的人們一定不敢想象,農民工數量會超過2.5億,高校在校生會達3000多萬。正是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構筑了每年春運日益擴大的人口基數。發展中的問題,倒逼我們用發展來解決。所以今天的人們也無法想象,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的父輩從廣州坐火車到北京要花費90個小時,究竟是怎樣一幅圖景。
同時,春運也是記錄中國社會復雜性的“大剪影”。畢竟,36億春節遷徙人口中,也許上億人在為車票焦慮;畢竟,“超萬公里高鐵”的另一面是“人均鐵路長度不足一根香煙”,交通運力仍然短缺。基礎設施建設的道路,仍然很漫長。更深層次上看,春運的背后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更是中國負重前行的一條短腿。正如有專家所言,生產力要素配置不均,是導致春運出現的直接原因。
因此,春運是道綜合題,其答案也只能從春運之外去求解。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破冰以及新型城鎮化的推進,相信越來越多的人將不必再用長途奔波換取團圓,而那時的鄉愁,也自然不會僅僅寄托于小小的車票。
這就是春運,不容回避的年度公共話題,流動時代無法抹去的集體記憶。它問題叢生、矛盾重重,但圍繞它的變革從未停頓、努力也不曾止步。春運背后種種復雜情緒所對應的,正是一個問題講不完、但又快速前進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