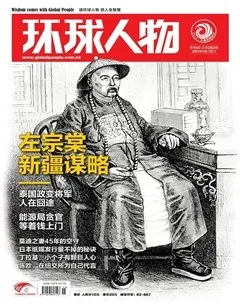士無定主
“士無定主”語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描述的是戰國時代的士人,意思是說當時的士既不像戰國前的貴族之“士”,也不像戰國后的官員之“士”,他們沒有固定的“主人”(家主或君主),而是可以在各家各國之間自由地流動,戰國之士已成“游士”。
“士無定主”既可以說是失落,又可以說是解放。士人失去了某種保障和庇護,現在只能依靠自己的才能,但同時也失去了一國一家一姓的約束。過去的貴族倫理要求他們要死忠一個主人——往往是他們出生地的主人,而現在出現了一種新的士人倫理。這種倫理使他們不再將自己視為一國一家一姓的臣仆,而在某種意義上是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對當時各諸侯國競爭的中國社會來說,有這樣一種自由流動的人才資源也的確使社會充滿活力,使許多有才能——當然主要是外交和軍事才能的人大放異彩,使戰國既是一個血火蹂躪的悲慘時代,也是一個人才輩出的壯觀時代。
我們從戰國時代“士”的稱號的繁多也可以看出“士”的性質和功能的廣泛性,例如“謀士”“察士”“策士”“勇士”,還有,“巧士”“銳士”“精士”“良士”“庶士”“吏士”“通士” “國士”“虎賁之士”“筋力之士”“文學之士”,甚至“枯槁之士”等等,不一而足。謀士為人出謀劃策,察士明察說辯,策士善于游說,勇士孔武有力,各有分工,且分工之細讓人咋舌。
這一中國歷史上游士時代的形成,正是基于各諸侯國君主與外來游士的結合。
從游士個人方面來說,他們沒有強烈的家國意識的束縛,反而有強烈的個人主體的選擇意識。當時既是列國爭強,又保持一種一致性和連貫性,有一個共有的“天下”的觀念,各國政治經濟本來就有密切的聯系,曾經共同尊周天子,語言文字大致相通,不會有交流和心理的障礙。
作為一名游士,既有生存的壓力,又有出人頭地的誘惑力,以及實現自己政治理念和才能的吸引力。而從最終的結果來看,這些游士實際發揮的作用,可以說遠在他們所得到的資源之上。
戰國期間,除了國君所代表的國家,常常就只見個人。社會上沒有有力的中介組織,不見強大的宗族、宗教或政治機構。只有極其松散的學派和同鄉,會做推薦,但同時也有激烈的競爭。可以看出,戰國時代的“士”基本上還是以個人為本位的。
而另一方面,即從各諸侯國來說,緊迫的政治和軍事競爭使各國求賢若渴。這當中最需要的,就是那種除了才能幾乎沒有其它資源的外來人士,而“游士”往往都是這樣的“窮士”。當然,不乏有大才的游士和君主一旦遇合即一步登天。游士在君主那里雖然容易暴起,卻也容易暴落,根基并不穩固,那時也沒有制度的保障,常常要看君主的一時喜怒。
虐士殺士雖然在君主的權力范圍內,但也要相當忌憚天下的輿論,如果蒙上“動輒殺士”的惡名將對其統治相當不利,所以往往只是驅逐或冷藏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