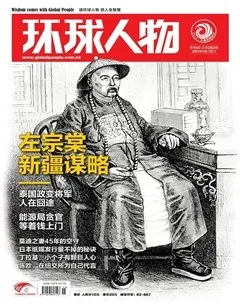“現在的城市藝術讓人啼笑皆非”



人物簡介
王中,1963年1月生于北京,1988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現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城市設計學院副院長。其作品多次參加國內外各大雕塑展,曾獲中國環境藝術杰出貢獻獎、新中國城市雕塑60年建設成就獎等,并參與、主持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世博會的設計策劃。出版專著《公共藝術概論》《奧運文化與公共藝術》等。
王中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雕塑藝術家,更是一位從學院、工作室走向城市空間的公共藝術家。他也是德國思想家本雅明筆下的“都市漫游者”,喜歡用自己的雙腳丈量城市。王中說他對城市有天生的敏感,總是能很快把握它的脈搏。城市離不開文化,在拉丁語里,“文化”就是聚居的意思,和“城市”是同一個詞。“那些有魅力的城市,讓我們向往的是什么?幾乎都是文化意象。如果沒有這些,城市就只是一些街道、建筑,沒有靈魂。一個城市,它的表情應該是友善的,故事是動人的,空間是有品質的。”2014年5月下旬,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對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說:“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正在向文化積累厚重的城市轉移。中國飛速的城市化進程,已經到了一個拐點,要從規模轉向質量。時代正將注意力轉向城市公共藝術。”
我們這一代最痛心的事情
王中是地道的老北京,父親做制版印刷工作,母親是電影放映員。小時候他經常騎著自行車大老遠跑去少年宮畫畫,坐在畫架之前,他特別愉悅,每當創作出一幅好作品就很得意。他學畫是“野路子”,到廢品收購站找老頭兒淘小人書來臨摹,畫《三國演義》中“騎馬打仗”的場景,樂此不疲。14歲時,他被一部羅馬尼亞電影《第八個是銅像》迷住了,電影一開頭講一位雕塑藝術家為英雄塑像。雕塑家把煙頭一捻,抓起泥土就創作,動作無比瀟灑。當時正好趕上北京工藝美術學校招生,父親讓他報考裝潢,志愿表都填好了,他一出門就把志愿表摁在墻上改成了雕塑專業。
在工美學了4年雕塑后,王中分配到北京工藝美術研究所,從事木雕創作。這在當時是個眾人羨慕的鐵飯碗。但王中卻一直想著要報考中央美院,在他心里那是“殘廢了拄著拐杖也要進去的地方”。美院雕塑系3年招一次學生,而且名額只有寥寥幾個,王中背水一戰,最終考上了。在美院5年,他練就了扎實的基本功,連性情也沉穩精細起來。
畢業后,王中留在美院雕塑系任教,同時也開始了藝術創作。他用作品表達著藝術家的個人體驗。比如創作于2000年的“生命系列”,就源自接連發生的兩件事情。在相隔不到4個月的時間里,王中的父親去世、女兒降生。當他推著父親的遺體走向太平間,漆黑的通道里投射過來一束光,這樣的情景觸動了他,被他直接運用到了作品之中。
同時,他也在用創作表達對現實的思考。作品《老北京系列》《拆遷系列》和他對這個城市的記憶息息相關。他小時候住在前門大柵欄大江胡同,就在城墻根上,不遠處就是護城河,那是他兒時和小伙伴們玩耍的地方。后來搬了幾次家,搬到哪里都是“拆”。他的作品定格了類似這樣的歷史瞬間:一個蹣跚的老人拄著拐杖尋找他昔日的家園,他的記憶卻被身后的一片斷壁頹垣阻斷。
“最可怕的不是拆遷,而是老北京人精神的失落。這是我們這一代最痛心的事情了。”王中說。
藝術家不應該“躲進小樓成一統”
上世紀90年代的一次日本之行,對王中的創作觀影響至深,讓他覺得藝術家不能只顧著“躲進小樓成一統”,要盡可能影響更多人的生活甚至思想。
那次王中受邀去給一個日本寺廟畫壁畫、做雕塑。兩個多月的時間,他一邊工作,一邊被日本蔚為大觀的溫泉文化深深吸引。日本的溫泉有雪山上的、樓頂上的、懸崖峭壁上的,他在各個溫泉流連忘返,“不是貪圖享受,而是充分地感受到了日本人把文化藝術和生活完全融為一體的境界,這種方式讓日本人將東方文化很好地傳承下來。”
由此,王中開始思考“公共藝術”的價值。那時候,“公共藝術”在中國還是個完全陌生的概念。“公共藝術不是簡單的公共空間的藝術,它強調的是以藝術作為一個紐帶,來連接我們的生活,使我們的文化具有生長性。公共藝術不僅提升城市文化形象,還關系到培養什么樣的民族。”王中解釋道。
其實,看看那些文化名城就明白了,公共藝術是城市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凱旋門、埃菲爾鐵塔、自由女神像、悉尼歌劇院,你到一個城市旅游,看到的最有魅力的部分很多都是公共藝術。最開始它們可能只是用來美化城市,但是后來更大的功能是為城市居民創造文化福利,進而影響這個城市居民的審美,甚至影響他們的行為。”
在隨后的十幾年里,王中一直倡導要在城市建設中導入公共藝術。這十幾年,也是中國城市化進程最迅猛的時期,在他的設想中,本該有一批優秀的城市藝術范本誕生,但現實還是讓他深感無奈。“我們總是把城市規劃和城市設計混為一談,而今天我們仍然沒有真正的城市設計。很多城市的‘公共藝術’都讓人啼笑皆非,比如有個城市建了新的政府廣場,請來一家廣告公司,設計建造了4個立柱,上面是一個大球,意為‘四大班子托起未來的太陽’。可市民不買賬,說是‘四大班子頂個球’,后來夜里偷偷把球拿掉,市民又說‘四大班子不頂個球’。所以我說,現在很多城市只是在制造垃圾,而這些城市垃圾的危害性很大。電影拍不好,還可以不看,但這些東西是強制性的,它們每天在你的眼前晃悠,你不可能把眼睛閉起來。”
“您在這方面做了哪些嘗試?”記者問王中。“鄭州東風渠1904主題公園算一個吧。”他回答說。2008年,鄭州的官員考察了羅馬的城市建設,希望將鄭州也建成“雕塑之都”。但王中說服了他們,羅馬的雕塑是經過上千年的積淀形成的,這明顯不適合鄭州。他的團隊查閱了大量資料,認為在近代史上,“火車”與“工業懷舊”是這個城市的關鍵詞,他們還發現了1904這個年份,它是火車最初駛入鄭州的歷史節點。他們以現存的廢舊鐵軌為依托,做了一些等大的人像,有的等車、有的趕車,還做了一個火車頭,試圖恢復當年車水馬龍的情景。鐵軌的設計尤其匠心獨運,一對情侶塑像手拉手走在上面,鑄銅的枕木上寫著關于愛情的各種預言。建成后,這個雕塑公園人氣越來越旺。
去年,王中開始做北京4條地鐵線的公共藝術項目。“北京地鐵每天有超過1000萬人次的乘客,如果他們都能看到地鐵里的公共藝術,那將是博物館、美術館每天觀眾總量的千倍。”在南鑼鼓巷地鐵站,他建了一堵由4000多個琉璃塊組成的墻,命名為“北京·記憶”。6厘米見方的琉璃塊里,封存著來自市民和一些老字號的“記憶”,都是他們收藏并免費提供的紀念品。通過旁邊的二維碼,觀眾還能夠上網閱讀相關故事。
這件作品的政府投資本來是75萬,但如今已花費了175萬——有100萬是王中自己投的。如果簡單做個壁畫,可能只需花35萬,他還能賺40萬。“想節省成本,用樹脂塊就行,但琉璃高貴啊,完全是手工磨的。對我來說,做出滿意的作品更有價值。”王中說道。
城市有歷史、現在和未來
2013年,王中創作了“方舟一號”,他運用青銅和不銹鋼兩種材質,代表“陰陽”兩種屬性,表現傳統與現代的沖撞、人性與秩序的沖突。
這種沖突,也是一個藝術家內心對當代城市建設的反思。“我們無限制地發展,很可能是給自己挖坑,或許有天我們都會被埋葬其中。”王中說,“有個美國朋友曾對我說,美國人考慮事情頂多不過10年50年,你們中國人太厲害了,思考問題以千年計算。中國皇城的布局,早在2000多年前《周禮·考工記》里就有了規劃。明清北京城,被稱為‘人類地球表面最偉大的個體工程’。但現在,這座城市的整體性已被破壞,留下的古跡都是孤立的,整個視覺體系凌亂不堪。外國人來了,除了看長城、故宮,印象里就只有裝修豪華的娛樂中心、大飯店,這特別可怕。100年后再回頭看,我們都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城市永遠不是終結體,它有歷史、現在和未來。王中的理想是能通過一面墻、一座雕塑、一條街道,讓城市的歷史長河流動起來,讓人們感受到這座城市綿延不絕的生命。“我已經看到希望了。”他笑道。他創作的公共藝術作品像是植入城市的種子,在發芽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