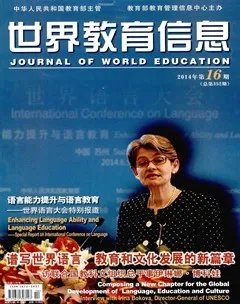跨文明對話 填平鴻溝 構建新人文主義
各位來賓,各位專家,
女士們,先生們:
本次世界語言大會的主題——“語言能力與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鮮明地揭示了語言事業當前所承擔的歷史性任務。語言,是人類最偉大的創造。它為交流和思維而生,是人類思想、感情的直接現實。人類進入工業化時代,語言的功用急速地跨越了民族邊界,成了不同文明間溝通的重要手段。但是,在近兩個世紀中,“我對你說”或“我說,你聽”成為常態,那往往是強制、訓誡和灌輸。在度過了痛苦的殖民時代之后,特別是隨著民族覺醒、經濟全球化和關注文化多樣性的呼聲日益強烈,語言的交流功能在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全面交往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在許多國家,為了自身的全面均衡可持續發展,也把消弭方言之間、不同民族之間信仰、觀念和倫理的隔膜寄望于語言的溝通。總之,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人類要可持續發展,國家要穩定,世界要和平,就需要多層次、多國別的,多民族之間的對話。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對話”(dialogue)逐漸成了在國際間使用頻率越來越高的詞語。“我說,你聽”變成“你說,我說”,這是世界的一個極大變化,意味著平等、尊重和協商得到了國際交往“正宗”方式的地位,意味著歷史所造成的鴻溝有可能逐漸填平,也意味著語言的交流功能超越了日常生活和相對固定的“話域”,面對的是無限的空間。
女士們,先生們:
人類的智慧,是靠對話而成熟和傳播的。讓我們回顧軸心時代的偉人們,孔子、孟子,蘇格拉底、柏拉圖,耶穌、釋迦摩尼,豈不都是在和學生、公眾無數次的對話中迸發出智慧的火花、探尋到真理的嗎?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因對話而實現和平的事例,也有數量或許更多的因拒絕或不充分、不善于對話而發生的慘劇。正是因為看到了對話是不同文化間消除誤解與隔閡,取得共識的最主要的手段,所以在1993年世界宗教大會上由6000位宗教領袖為了世界持久和平而通過了《走向世界倫理宣言》,聯合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則從世紀之交起,著力提倡并組織不同文明間的對話,成效顯著。另一方面,在剛剛過去的幾十年里,以維特根斯坦和哈貝馬斯等人為代表的交往理論哲學家們,對于對話的邏輯和規則、公共領域中的語言溝通和演變,做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對話”已經成為世界哲學界近年來研究的熱門課題,哲學家們有意無意地把語言的溝通作為構建人類共同倫理或新人文主義必須解決的前提。
但是,要達到聯合國和教科文組織提出的目標,要實現世界人民,特別是前殖民地國家人民和平幸福的愿望,要如哲學家們所倡導的那樣,通過對話追求人類共同倫理和宇宙的真理,國際組織的號召和呼吁需要扎實地付諸實施,學術精英們的研究和呼吁需要讓世界廣為知曉。顯然,對話必須要有億萬民眾的參與。但是,目前的情況是,雙方乃至多方交往的人們更為關注的是商品、古跡、景致和食品,意欲了解他者人文、信仰和倫理的不多。出現這種情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天是一個物質第一,精神被忽略的時代;物質的東西直接刺激人的感官,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就語言的運用而言,有關日常生活所涉及的物質和技術的語言,在不同語言間的對應較之人文的,尤其是比關于信仰、倫理的,要簡單得多,雖然句子結構之間的對應也是極為麻煩的事。
這對語言事業是一個新的挑戰。與經濟全球化同時出現并且應該強調的,是文化的多元性,而后者就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精神領域概念的表達。在這一領域,句子結構和修辭的差異反而退到了第二位。摩洛哥哲學家、2003年教科文組織沙迦獎獲得者,2009年至今擔任該國文化部長的本·薩利姆·希姆什教授(Bensalem·HIMMICH)在201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里說到:
為了使不同信仰或文化間的對話變得更為明確和嚴謹,應當抵制雜亂、頑固和不規范的術語模式,并盡量使事物名稱符合其性質和功能。
他舉例說:
數百年來,歐洲人一直把伊斯蘭教(Mahametisme)、伊斯蘭和伊斯蘭主義作為同義詞或同源專有名詞的變異。
因此他呼吁:
重新審視文化間對話的全部詞匯并對其進行概念批評,這是為名副其實的和平文化創造重要條件。這種和平文化的基礎是合作者間真正的對話。(《Diogene》,2010)
他所提出的問題在中國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史中實際上已經存在了幾百年。例如16世紀的偉大傳教士利瑪竇和17世紀的偉大數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茨等人都是以基督教的“神”“愛”“善”“禮”等概念來理解中國的儒家文化,甚至認為儒家所信仰的也是人格神,因而可以證明基督教教義具有普世價值,這一誤解直至今天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障礙。近幾十年,這個問題已經引起歐美和中國學者的高度注意;但是在沒有出現希姆什所期望的那種情景時,人們只能用一種權宜之計,或者說是過渡的方法處理,在遇到中國文化的概念時,直接寫出漢語拼音,例如道(Dao)、理(Li)、仁(Ren)、性(Xing)、氣(Qi)、孝(Xiao),等等。但是,這個辦法最終只能用于少數詞語,局限性是顯然的。如果要想廣泛而深入地開展不同文明的對話,希姆什所提出難題必須解決。當然,不同文明間的對話所涉及的必須解決的語言問題遠不止希姆什所說,例如以下一些問題近年來不斷被人們提起:
在未來的人際交往中一人多語(含本民族方言、本國其他民族語)的現象會越來越多,社會如何滿足這種需求?
與此相伴的一個重要趨向是作為文化的符號,記載著不同民族或地區歷史的少數民族語言、方言和人數較少的國家(例如馬爾代夫)的語言,呈現出迅速衰落的跡象,我們應該采取怎樣的對策?如何挽救和保存?
許多國家已經采取多種措施以保護國內少數民族語言和少數人使用的語言。但是,保護的目標能否達到?按照語言分區分校進行母語教學,利和弊孰大孰小?對少數民族學生的過度資助是否是“逆向歧視”?師資和教材的匱乏,所需成本過高的問題如何解決?外語教學和母語教學如何不相抵消,做到相得益彰?
為不同文明對話服務的雙語或多語辭典如何編撰?在涉及他種語言人文學科的語匯時,按西方詞典學的路徑,是否能做到被釋詞和解釋用語“等值”?
為了培養適應未來需要的語言人才,我們的語言教學和研究需要作哪些調整和改革?
日新月異的IT和網絡技術如何直接為不同語種間的對話服務?
女士們,先生們:
這類問題的單子,我們可以拉得很長很長,這說明為了建起人類交流合作的語言之橋,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極其嚴峻的,需要長期奮斗。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就是,為了填平國際和人際間的鴻溝,首先受到挑戰的將是語言政策、語言教育和語言技術;首要的任務是說服各國政府采取足夠的措施,說服具有經濟和技術實力的企業積極參與搭建語言之橋的工程。
單就IT和網絡技術協助語言教育和交流而言,就有巨大而急迫的需求,當然這也是語言技術一個巨大的發展空間。現在一些國家在機器翻譯和人機對話的研究和使用方面已經投入了不少資金和人力,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除了少數公司著眼于提高人們的語言能力、挽救瀕危語言,制作了詞典、教學軟件(包括視頻)外,多數還是圍繞著經濟事務和技術利益進行開發。這是資金來源的局限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以我所領導的一個技術團隊為例,我們所開發的應用技術中英對譯軟件(主要是專利文本),三年來耗資已經近1000萬人民幣。到目前為止,面對真實文本的譯準率和召回率已經達到85%,預計到2014年底,這一數字還要提高。如果擴大翻譯范圍、繼續提高譯準率,所需資金將更多。我之所以專心研制應用技術的翻譯軟件而不敢旁顧,一方面是因為我知道,要達到人機交流,必須先解決不同語種的對譯難題,另一方面也是目前的課題籌集資金相對要容易得多。
很久以來,我一直夢想著能夠研制用于人文交流的軟件,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機對話的技術。我知道其中的難度,并且正是因為難度大,所以沒有更多的資金后盾是無法著手的。人類在這一漫長道路上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但是在這里停留得太久了。從我自己的經驗中,我有這樣的感觸:這是一項需要引起世界注意的事業,更是需要無疆大愛的事業。因此我建議:希望IT業和網絡商能夠把人類的交流對話作為一個長遠的事業,減少對眼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希望各國政府高度重視語言教育,調整語言政策,保障不同語言間的完全平等,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應該慷慨地幫助新興國家;希望有關政府在資金和政策上支持IT業,鼓勵網絡商跨過純商業的視域,關注人類長遠的共同利益,加大語言交流技術的開發;當然我同時希望教科文組織在這一進程中發揮更大的推動作用。
女士們,先生們:
我們在不斷強調不同文明對話重要性的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對話在解決世界和國家和諧問題上并不是萬能的。那些以優越種族和上帝的現代選民自居,一意把利潤、權力作為行動準則,堅持奉行殖民式思維,視人民為奴役對象者,對話不過是遮人耳目的游戲。但是,我們對人類的未來仍然充滿信心。誠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組織法》中所說,“戰爭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務須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衛和平的屏障。”這句話反映出人類在經過了歷史上最為殘暴酷烈的戰爭之后,已經自覺到出路在哪里。我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三屆尼山論壇上說了下面一番話:“這里的‘戰爭’一詞,指的是人類危機在層層積累之后最終爆發的極端形式;‘人之思想’之所指,美國過程哲學家,密歇根偉谷的斯蒂芬·勞爾的一段話,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較好的解讀,他說:
現代性最糟糕的部分,是沉溺于物質主義的一己私利的“道德疾病”;對“消費主義”的過度迷戀;導致意識形態僵局的不成熟的將凡事都絕對化的傾向。
最大的問題是高分貝地謳歌物質生活而貶低精神生活,貶低我們的人性。(《2014年的一次對話》,見《光明日報》,2014年4月16日)
女士們,先生們:
教科文組織所提出的“保衛和平的屏障”將由誰來筑起?人民!人民的團結是戰勝邪惡的最有力的武器。要團結,就要了解他者之心,擴大自己和他者的視野,大家一起從對物質的迷戀中解脫出來;要了解他者的心,就要無障礙地交流;要無障礙地交流,就需要提高語言能力;要提高語言能力,就需要行動,而且不限于各國自己內部的行動。這是一個基于理性的因果邏輯鏈,而從事有關語言事業者,各國政府和專家,則處于這一鏈條的終端。
女士們,先生們:
讓我們攜起手來,努力!
(文章系作者2014年6月5日在世界語言大會上的主旨發言)
編輯 李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