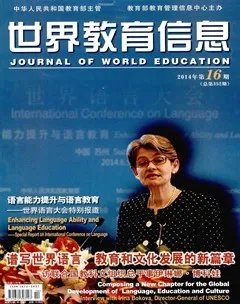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中的語言問題
各位來賓:
大家好!我將以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為背景,站在殘疾人語言及其語言教育的角度,與大家分享語言和語言教育的話題。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已經簽署了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非常有意思的是,公約中也提及了殘疾人語言和語言教育這個問題。在這里,我想向大家重點介紹與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相關的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與語言和教育政策有關的特殊人群,第二個主題是語言、文化和社會和諧。下面我將以手語為案例進行分析。
一、殘疾人受教育機會的缺失
正如我向大家所展示的那樣,在發展中國家,太多失聰或者殘疾兒童沒有獲得開發其潛能的機會。試想一下,一個正常人的潛能沒有被開發將對他(她)產生何種影響。對殘疾人而言,這種消極影響只會更大。一般來說,一個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成功的機會就越大。沒有受教育機會的殘疾人與正常人相比,差距極大。
普遍來看,獲得大學本科或者以上學位的人預期的工作機會和收入比高中畢業生更多。無論是正常人還是殘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不容易落后于他人。如果一個殘疾人在早期能夠接受教育,并且能獲得足夠的后續教育機會,那么他們就更有可能追趕上正常人。正常人和殘疾人工資收入的對比進一步證明了這個觀點。數據顯示,有繼續教育或成人教育相關資格證書的人的預期收入要比高中畢業生高30%,獲得至少一個學位的人的預期收入要比高中畢業生高60%。可以這樣說,殘疾人獲得的受教育機會越多,他們與正常人的差距就越小。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二章第三十條指出:“締約國應當采取適當措施,使殘疾人能夠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并使自己在創造、藝術、智力等方面的潛力得以開發”。實際上我們經常看到的情況是,很多殘疾學生無法在學校獲得語言學習的機會。一般的學校往往認為,正常的教育方式對殘疾兒童來說太具有挑戰性了,而且也沒有適合殘疾兒童的教材。這最終導致殘疾兒童難以獲得智力訓練的機會,在教育的起跑線上就已經大大落后,更不用提獲得后續的高等教育的機會。語言學習上的歧視使殘疾學生站在了高等教育(語言技能作為入學的基本要求)的門檻之外。
二、語言學習的機會至關重要
然而,我必須指出的是,學校提出的“正常的教育方式對殘疾人挑戰過大”這一言論站不住腳,一些國家已經有興趣或經驗向閱讀障礙人士甚至聾啞人提供外語教育。比如,對盲童進行培訓使他們成為合格的口譯員。
對于這樣的特殊群體,不少國家已經有提供相應的語言教學和語言療法的成功經驗。有這樣一則新聞:一個精通4種語言的10歲盲人女孩成為歐洲議會最年輕的工作人員。這個女孩叫做阿萊克西亞(Alexia),她2歲時因腦瘤手術而失明。雖然身患殘疾,但這個小女孩卻有著驚人的語言天賦,10歲時就已精通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和中文,并且現在正學習德語。如今,英格蘭東部歐盟議員(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羅伯特·斯德第(Robert Sturdy)邀請她前往位于布魯塞爾的歐盟議會體驗口譯員工作。
阿萊克西亞的媽媽是法國和西班牙混血,爸爸是英國人,所以她很小就掌握了三門語言。4歲時,她能用盲文閱讀和寫作。6歲時,她又學習了漢語。她很快便通過了GCSE(英國普通中等教育證書)的法語和西班牙語考試,兩門成績均為A,現在她在劍橋大學學習德語。從6歲起,成為一名口譯員就一直是阿萊克西亞的夢想。她獲得年度青年成就獎后,羅伯特·斯德第邀請她體驗歐盟譯員的生活,并與頂尖的口譯員一同工作。阿萊克西亞說:“這真是太棒了!我已經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名口譯員,任何事情也阻止不了我。”
從這個活生生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對殘疾人來說,依然有許多語言學習的機會,而很多學校卻以挑戰過大為由沒有給他們提供這樣的學習機會。
三、手語:制定語言政策,
以創造一個文化和社會和諧的典范
我也想借此機會探討一下手語方面的情況。我想請大家相信一點,目前我們沒有大力推動手語發展,但是這方面有很大發展空間,因此彌補起來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進一步制定與手語相關的政策,在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方面意義重大。
手語是由聾人以及有聽覺障礙的人創造出來的,目的是幫助聾人群體之間以及與他人的交流,但是關于聾人群體的語言和文化身份本身就有很多爭議。作為殘疾人群,聾人被認為是語言和文化的少數群體,而手語也沒有通用語法。其實,手語的確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同家庭、地區使用的手語淵源不同。但手語是由聾人群體而不是教育者創造的,有文獻記載,手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學校教育產生之前;手語的語法更類似于英文和中文,有主謂賓的形式;從類型上講,手語和正常人所用的口語存在著極大差別。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四章第三十條為手語的推廣提供了參考:“殘疾人特有的文化和語言特性,包括手語和聾文化,應當有權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承認和支持。”有必要再次強調,已有146個國家簽署了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很多國家都有支持土著或少數群體的口語的語言文化社區,以保證土著口語或方言的生命力。遺憾的是,至少到目前為止,并沒有適用于手語的類似規定,手語沒有享受到這種“公平待遇”。在教育、就業、社會、經濟、公民機會等方面,聾人一直受到排斥。
因此,一些國家的土著口語支持工作做得很好,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聾人手語的境遇十分尷尬。手語沒有得到充分支持,這與《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背道而馳。只有對手語給予足夠的重視,才能夠在此基礎上,慢慢扭轉聾人在教育和就業方面所面臨的不公平局面。
有時候,我們不愿意與聾人交流(這也被貼上了“歧視”的標簽)并不是因為他們聾,而是因為他們使用的手語我們不懂。所以,應該考慮把發展手語納入國家的語言發展政策,這方面急需更多發展和努力。
四、尊重聾人社群,保護聾人文化
聾人之間的交流無法通過聽覺系統傳達,因此,他們就自然而然地優先使用完全視覺化的語言。由于聾人仍處于社會下層,相應的,其所使用的語言——手語的社會地位也比較低。手語的使用也不可能被普遍傳播,因為對手語感興趣和學習手語的人并不多。聾人自認為是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少數派,但是用翻譯作為中介,其依然是促進理解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到手語的翻譯會顯得更加獨特,因為翻譯過程不僅僅是雙語的,而且是雙通道的。所以,綜合考慮這些方面,我們應在界定手語的時候進一步拓寬視角。
同時,手語也增進了我們對于語言的理解。語言研究者指出,手語的確是一種語言,對手語進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進一步審視口語的核心特點是什么。語言用的是什么通道(比如是口頭的通道還是手語的雙通道),將會直接影響到這種語言的表達和理解。此外,對于手語的研究視角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語言(包括手語和口語)在神經層面是如何工作的。
雖然一般人對于學習手語的熱情并不高,但對于有聽覺障礙的孩子來說,他們有著極強的學習手語的欲望。在英國,大概每年有5萬人參加不同級別(1~6級)的手語考試。由此可見,學生學習的需求非常強烈,但現在面臨的窘境是沒有足夠數量的手語教師。
最近幾年,我們也聽到了一種“聾人文化”的說法。由于聾人把自己視為少數群體,他們也在積極地探索自己的內部世界。聾人希望能夠保留自己的文化,他們也在積極開發相關技術。
我想給大家展示一些聾人文化。這是一個聾人詩人所表達的手語詩歌,詩歌沒有任何翻譯,是一首沉默的詩歌。他在這首詩歌里面表達的是感覺、味覺、嗅覺、觸覺、聽覺和視覺。通過對每一種感覺進行描述,用詩歌化的手勢,用手的不同形狀、方位來表達,就像口語表達中不同的聲調、語氣。最后,他還基于人體的一個特點——無名指無法單獨工作,人們有時會覺得無名指比較笨拙——借此表達了如果有一個感官失效,其他感官會受到怎樣的影響,而各個感官之間又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
聾人文化的探索被歸結為“Deafhood”(這是聾人文化的術語,倡導的是“聾”也有其積極意義,這和現在普遍使用的“聽覺障礙”有所不同,聾人認為這并不是障礙)。聾人群體有其身體特性、基因遺傳和社會身份,聾人文化是藝術、成就和財產。
五、未來殘疾人語言教育優先考慮的事項
最后,我想談談未來殘疾人語言教育需要優先考慮的事項。首先,我們要拋棄殘疾人就是“不健全的人”的觀點。殘疾人是擁有自己文化的特殊群體,能夠對這個世界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所以不應當把他們視為異類。
我們要做到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序言中所要求的那樣:“確認無障礙的物質、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醫療衛生和教育、信息和交流,這些因素對殘疾人能夠充分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至關重要。”當前政府采取的個人主義(主要在醫療方面)的觀點抑制了交流、語言和文化的認可程度,這與《殘疾人權利公約》的要求背道而馳。因此,必須改變這種現狀,讓殘疾人能夠享受基本人權和自由。
(文章系作者2014年6月5日在世界語言大會上的主旨發言)
編輯 郭偉 許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