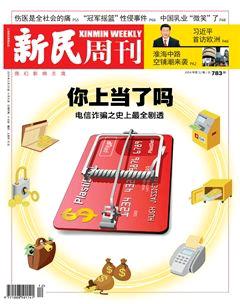見幾個活生生的人
王小木

終于有了亞紀子的消息,她發郵件來打聽我兒子就讀的幼兒園的情況,下個月她和兩歲多的兒子就會回到我們相識的這個美國南部小鎮。“我老公會來日本接我回來”,她在郵件里刻意強調了這句話,去年6月帶兒子回日本度假三個月的她取消了原定9月回美的行程,她當時說不打算回美國了,不能再忍受沒有親朋好友在身邊的日子。在這兒,走出家門,除了我,她連一個可以說話的朋友都找不到。
我們是在小鎮書店里認識的。這家美國最知名的書店每周四都有給孩子們的免費故事時間。我第一次去那兒時就留意到了亞紀子,親切的亞裔面孔。幾次碰面后有了交流,她還帶著兒子來我家玩,雖然我們雙方都說著蹩腳的英語。她兒子太重太胖,一歲半時還不會走路,個子不高的亞紀子根本抱不動他,到哪兒都得依賴推車,于是大多情況下她寧愿呆在家里不出門。但是我從來不知道,她在這邊生活了幾年,竟然沒交往過一個日本朋友。
我比她幸運,我們住的這個小鎮有一所知名度不錯的大學(有很多的中國留學生和家屬們),有三四家業界頂尖的科技和工程公司(有很多來自中國的技術移民和家屬們)。兒子八個多月時,我帶他去小鎮公立圖書館聽故事,整個教室2/3都是說中國話的媽媽們和同齡的娃娃們。混熟了,平時娃娃們一起玩,周末帶老公聚會,異國他鄉也能感到些許友情親情。
但是一兩年過去了,學走路的娃娃們都開始上幼兒園,媽媽們也改為時髦的微信聊天。我忽然間感受到了亞紀子說的那種寂寞感:每天接送兒子上下學時和老師的交流(如果她不忙的話),竟然成了我唯一和人說話的機會。哦,或許我還應該把在小區里遇見鄰居和在超市結賬時說的“HOW ARE YOU”算上。
幾年前還在國內上班時,同事說起過一個認識的美國朋友,年過五十了還在上醫學院的護士課程,當時我們感嘆美國生活太不易。現在我明白了,的確有很多在美華人需要做各種零活來養家,但很多人去超市收銀、去學校修課,完全就是為了見幾個活生生的人,說一句活生生的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