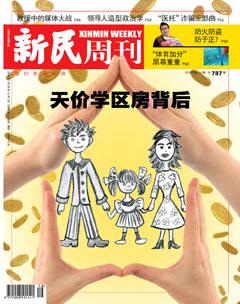中國需要創(chuàng)造“復雜外交”模式
劉迪
最近幾個月發(fā)生的對日民間索賠事件,引起日方高度緊張。2月27日,37名二戰(zhàn)期間被擄勞工聯(lián)名向國內法院提訴,要求加害日企賠償,3月19日國內法院受理。4月15日, 700余名二戰(zhàn)期間被擄往日本的中國勞工及遺屬聯(lián)名向國內法院提訴,要求加害日企認罪賠償。4月19日,上海海事法院在國內某港扣押日本一家公司輪船,理由是該公司未對法院賠償令做出回應。這些動向,在日本引起震撼。日本媒體憂心忡忡,表示擔心這種動向波及其他日本在華商企。
中國民間對日戰(zhàn)爭索賠,起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最初,中國民間受害者均通過日本代理人,向日本法院提出賠償請求。但是今天,中國受害者開始向中國法院提起索賠訴訟請求,而中國法院不但受理,已經(jīng)開始強制執(zhí)行。這在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史上尚屬首次。日本輿論認為,這與安倍參拜及中日關系惡化有關。
4月21日上午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說,中國扣押日本輪船事,“可能從根本上動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精神”。應該說,菅義偉所說的“邦交正常化精神”的動搖,不是因為民間受害者對日索賠造成的。而是最近一段時間,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形成的“1972年體制”遭到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動搖了“1972年體制”。 所謂“1972年體制”,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圍繞中日間存在的領土、歷史等問題雙方達成的共識。近年圍繞釣魚島問題、參拜問題,兩國達成的1972年共識已然無存。前述索賠案例,正是在“1972年體制”松動的前提下發(fā)生的。
應該說,如果僅是“1972年體制”瑕疵問題,那么兩國外交當局,還可以通過協(xié)商、交涉彌補這種瑕疵,但是在中日關系大環(huán)境惡化時,這種瑕疵可能無法通過外交當局交涉做出彌補。從現(xiàn)實狀態(tài)觀察,中日既非敵國,但也不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種狀態(tài)的友好國家。中日關系處于“非戰(zhàn)非全面友好”狀態(tài)。當今中日關系,成為世界最復雜的大國雙邊關系。中日關系,正在錯綜復雜中推移,雙方既斗爭又合作。
中日官方高層交流,自前年日方購島后已停止。經(jīng)貿(mào)交流、民間交流、觀光往來、學術交流仍在繼續(xù)。但近年中日貿(mào)易增長已陷入停滯甚至下降,日本對華貿(mào)易序位退至第5位。此外,雙方前往對方國家的留學人數(shù)下降,彼此成為最不喜歡的國家之一。這是中日關系的現(xiàn)狀。
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國外交需要高度技巧。對兩國來說,打開目前“僵持”尚需時日,但“維持”與“促進”并非完全不可。那么,中日外交需要在“僵持”、“維持”與“促進”三個方面做出高度平衡。
在政府高層接觸方面,中日已陷入僵局。但在非政府層面的人際交流,雙方仍要“維持”。現(xiàn)實中,中日雙方都在展開相當程度的非政府層面交流。4月上中旬,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訪日,與日本朝野密集會面。5月,將有一批日本國會議員密集訪華。這些動向表明,中日雙方在非政府層面,還有很多人仍然意在克服超越兩國政府關系的僵局。
另外一個方面,在全球化時代,不論中國或是日本,彼此都有經(jīng)濟往來需要。盡管中日雙方政治交流陷入僵局,但經(jīng)貿(mào)往來卻依然不斷。在這個方面,盡管日本政府不斷構筑“中國包圍網(wǎng)”,但日本企業(yè),仍在熱心投入中國市場。筆者以為,兩國經(jīng)貿(mào)領域的交流,仍然需要“促進”。
4月21日菅義偉說,中國法院扣押日本商船“可能導致在華日資企業(yè)萎縮”。筆者以為,從博弈角度看,中方不可能沒有事前評估這個問題的后果。更重要的是,中日經(jīng)貿(mào)關系不會因一起法院判決,而導致迄今40余年來的努力崩盤。
今天中日外交必然是復雜的。在這樣一個復雜的時代,需要高度的外交技巧。我們希望在中日外交領域,創(chuàng)造一種復雜外交模式,以應對目前中日關系的復雜局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