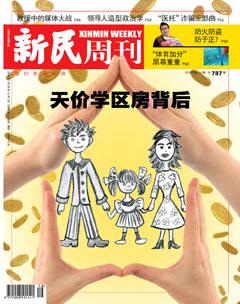這不叫抄襲,這叫“梗”?
黃平
在沸沸揚揚的瓊瑤指控于正抄襲事件之前,筆者以為自己和于正只有一點是相似的,就是都對《小時代》系列頗有微詞;現在發現還有一點是相似的,都看過瓊瑤的《梅花烙》。于正兄比我年長幾歲,但作為同一代人,我們小時候都深受瓊瑤劇影響。不過,于正在回應瓊瑤指責時,還講到看《梅花烙》之前就看過一個黃梅戲,情節也是“偷龍轉鳳”。所謂偷龍轉鳳,就是瓊瑤《梅花烙》與于正《宮鎖連城》共同的核心情節:某某大人物的老婆生下女孩,偷偷換出去抱回來一個男孩,以此討得歡心。若干年后,待這個小女孩身心發育成熟,和當年的小男孩來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地位懸殊、賤人嫉妒、命運詛咒……
于正提到的這部黃梅戲,筆者回憶了黃梅戲的經典,發現無一合適。可能容易混淆的是《女駙馬》,但那是女扮男裝,和偷龍轉鳳大大不同。不過,以民間戲曲之豐富,于正涉獵之廣博,偷龍轉鳳情節之爛俗,《梅花烙》之前有類似情節,或有可能。于正還舉了2000年的電視劇《絕色雙驕》為例,說我是借鑒這個的,有來往短信為證。當然,《絕色雙驕》是《梅花烙》后來的作品,說服力不那么夠,這相當于倒數第一抄倒數第二的作文,結果和倒數第三的相似,有經驗的老師會得出倒數一二兩位好漢聯合作案的結論。
無論是莫須有的黃梅戲,還是直言不諱的《絕色雙驕》,于正為自己辯論的核心,在于強調任何故事都有一個“梗”(網絡用語,類似橋段),差不多并不奇怪。于正以此反擊瓊瑤,說你的《庭院深深》和《呼嘯山莊》也挺像啊。筆者覺得和《呼嘯山莊》不像,和《呼嘯山莊》作者的姐姐寫的《簡·愛》倒有點像,大概于正激動之余混淆了姐妹:《庭院深深》結尾處講到女主人公含煙重回燒成廢墟的含煙山莊(這名字甚不吉利),發現了沉浸在孤獨與痛苦中的男主人公,嗯,他在大火中瞎了一對眼睛。
但是,《庭院深深》和《簡·愛》的相似,只是個別情節的雷同,認真讀完這兩部作品,沒有誰會認為在讀同一本書。就藝術水準而言,瓊瑤與夏洛蒂·勃朗特有天壤之別,瓊瑤的《庭院深深》女主人公之出走,在于老套至極的婆媳式沖突,瓊瑤筆下的女孩子,如何能夠達到簡·愛的靈魂深度?夏洛蒂女士如果讀過《庭院深深》,也絕不會認為這樣的作品在抄襲自己,而只會好奇這寫的是什么。這是經典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區別,二者固然或有相似,但細讀下來,骨子里涇渭分明。
而瓊瑤訴于正,是大眾文化內部的沖突,在目前這個泥沙俱下的文化工業時代,這種抄襲屢見不鮮,判斷起來,有些棘手。原因在于,所有的大眾文化,在作品的靈魂層面都是相似的——它們都沒有靈魂。這樣似乎只需要判斷情節是否雷同就可以了,但所有的大眾文化,在情節層面都是受幾個原型模式所驅動,所派生出的橋段都是相似的。于正屢次面對抄襲的指責,但死守不放,就是抓住了這個道理。而且,由于大眾文化的讀者是階段性的更替,不斷有毫無文化記憶的“小白”讀者涌入,“抄襲”對他們并不構成困擾——這些年里韓劇已經發生太多起車禍,產生了太多的植物人了,你可能慢慢醒悟,再看到植物人不是找紙巾而是爆粗口,但你的弟弟妹妹們剛剛注冊了人生中第一個視頻網站的賬號。
然而,相似的原型模式,不應該推出雷同的情節,情節相似,即為抄襲。這就像你我都有骨骼,但除非你克隆我,否則長相應大有不同。金庸小說的原型也很相似,比如屌絲成長記,比如一男多女,比如洞窟奇遇,但老先生不斷翻出新的故事,這就是大眾文學的大家。瓊瑤與于正所爭執的“偷龍轉鳳”,既是原型模式,也涉及到情節構成。筆者不好妄下結論,但瓊瑤一方只要對比雙方的相似之處,一條條列下來,還是可以辨別的。
怎么辨別?筆者舉個例子,古龍名著《陸小鳳》之《銀鉤賭坊》篇,陸小鳳和他的小伙伴要從七個人中判斷出誰才是大BOSS,分別是佩劍的、玩暗器的、修指甲的、搬箱子的兩條大漢、紫衣少女、中年婦人;而在郭敬明的《幻城》中,卡索和小伙伴也要從佩劍的、用毒的、修指甲的、彈琴的、一條大漢、中年婦人、捶腿婢女中找到所謂的太子。當然,你可以說古龍用兩條大漢搬箱子,而郭敬明讓其中的一位彈琴去了,這不叫抄襲,這就是于正所說的“梗”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