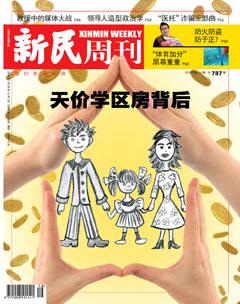世界好公民斯諾登
潘飛
美國作家亨利·大衛·梭羅撰寫短文《論公民的不服從》,創設了 “公民不服從”概念,對此后從事公民不服從研究和實踐的人士均產生了廣泛影響。“公民不服從”理論包括以下基本要點:第一,不服從的是“惡法”;第二,采取的是靜坐、罷工等非暴力手段;第三,是一種公開的行為,試圖引起更多人圍觀甚至加入;第四,它看上去可能是“違法行為”,但表達的卻是對法律的尊重和忠誠,是公民個人出于良知,對道德、正義、自由等公共理念的保護;第五,它不是消極的行為,反而是積極的抗爭;第六,抵抗的目標是邪惡本身,而不是作惡的那些人,目的是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法規發生一種改變;第七,只適用于民主、法治的社會,因為在這個社會,正義感不僅普遍被人們擁有和熱愛,也能借助法律等手段來伸張。
自2013年6月“斯諾登事件”爆發以來,斯諾登本人更被視為一個敢于向不健全或者被異化的法律權威發起挑戰和質疑的“不服從者”。
西方有句名諺,“最好的政府掌管最少”,可由于9·11事件給美國造成了泛濫成災的恐慌,基于國家安全考慮的美國政府,放松了法律監管,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英國政府通信總部利用這一“間隙”,動用各種技術手段來“管控互聯網”,加大了對本國及國外的信息監控范圍,導致情報機構開展電子竊聽的現象已經處于失控邊緣。斯諾登認為,得不到有效監管的權力如猛虎下山,侵害了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公民正當利益(特別是隱私權)。他的動機便是要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未經懷疑就監聽”的狀態發展到了什么程度,號召媒體和公眾對政府這種“全景監獄”(邊沁語)式的非法管控行為展開一種“反監控”。
斯諾登的“不服從”是慢慢形成的,《斯諾登檔案》一書解釋了這一過程。甚至從一開始,他反而是反對阿桑奇等“揭秘者”的所謂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的,在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等機構擔任“安全專家”的工作機會,讓斯諾登能更為直觀地接觸真相,加之受到各種激進思潮的影響,才使得斯諾登對政府的非法監控行為逐漸產生了反感。可以說,內心良知的蘇醒促成他從一個贊成捍衛者搖身一變成了一個不服從者。對于政府的種種欺騙行為,“如果民眾根本不知情,讓民眾認可就是一句空話”,這種超越個人,以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己任的強烈公民意識,也促成他敢于選擇公然戳穿政府的把戲。
當然,他最終能成功實現自己的目標,在《衛報》上開展報道的格林沃爾德作為同行者的影響也不可忽視。這個一直批判政府監控行為的知名批評家、資深記者,非常懂得并擅長借助“媒體”這個社會結構中的“第四權力”,與政府那種失去約束的“更具進攻性的權力運用”展開對峙,做到以“權”制“權”。
雖然選擇媒體將政府的丑行公之于眾,不惜損傷美國的國家形象,可斯諾登始終保持著理性的克制,比如在如何與媒體交涉,如何根據內容有選擇性地選擇揭露的渠道等問題上,他都有周密的規劃,恪守著一條原則:絕不將證據交給美國的敵對方(如俄羅斯)。如此一來,他有效規避了自己成為徹頭徹尾的叛國者或者外國間諜的可能,保持著對國家核心利益的保護以及對國家的忠心。
斯諾登的舉報和不服從行為在全世界范圍引起了令人振奮的反響,包括許多新法律的出臺,民眾的社會覺悟也有提高。至今,斯諾登流亡國外,幾無回國的可能,可他甘受懲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斯諾登不僅是美國的好公民,而且是一個超越國界,具有全球示范意義的世界好公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