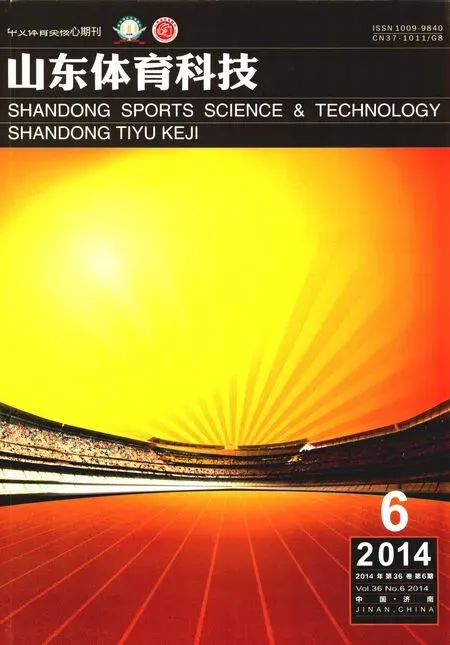隨遷子女的體育參與對城市同伴信任的影響
——運動友誼質量的中介作用
趙溢洋,曹 莉
(曲阜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山東曲阜 273165)
隨遷子女“同城不同待遇”的現實與污名化的刻板印象,加劇著“流動與城市”兒童和青少年間的疏離和排斥。有調查顯示“流動兒童的同伴信任、溝通維度得分顯著低于本地兒童”[1],更現實的社會背景是“中國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程度在進一步擴大”,“總體信任已跌破底線”[2]。而體育運動在建構和維持社會信任上具有特殊的功能,帕特南(Putnam,1995)關于獨自打保齡球與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研究中,可以看到體育參與與社會信任關系的詳盡論述;仇軍,鐘建偉(2010)也曾提出“體育參與可以提高個體的人際信任水平”的命題[3]。面對隨遷子女的境遇、社會信任滑坡的現狀和體育的積極功能,本研究的目的是考量隨遷子女體育參與程度、運動友誼質量與城市同伴間的人際信任關系。
1 文獻綜述與假設提出
1.1 體育參與與人際信任
體育與信任討論中常見的結論是體育參與影響一般信任或普遍信任水平。其中重要解釋依據是體育社會資本理論——體育參與建構了社會關系網絡,也相應地增加了社會資本,而信任、互惠和社會網絡聯接是高度生產性的社會資本功能[4]。在家人以外的群體關系水平上,隨遷子女的社會網絡主要由同學構成。他們的體育活動方式也主要是和同學一起參與為主,其中的人際信任符合“熟人”間“特殊信任”的結構和特征[5]。因此,針對同學、同伴間交往的社會關系情境,以及體育參與與信任的研究基礎,本研究提出,假設1:隨遷子女的體育參與對同伴信任有正向影響。
1.2 運動友誼質量與人際信任
運動友誼質量影響信任相關的諸多社會和心理效益[6],包括:1)認知效益,涉及對體育群體成員的認識和了解,是形成信任的重要前因。2)吸引效益,可解釋為情感增強論、時空接近論、個人特質論等,影響體育群體的人際信任。3)依戀效益,體育運動對親子依戀和同伴依戀都有預測作用,有助于培養人際信任。4)忠誠效益,表現為多次參與群體活動,信守承諾,并具有信任群體成員的傾向。依據運動友誼質量的特征,以及運動友誼質量的認知、吸引、依戀和忠誠等與人際信任高度相關的積極效益,本研究提出,假設2:隨遷子女的運動友誼質量對同伴信任有正向影響。
1.3 體育參與與運動友誼質量
體育參與會影響同伴接納和友誼。研究表明,體育參與可滿足與友誼相關的3種社會需要,幫助、支持和共同興趣。青少年在青春期對家人的依賴會減少,逐漸增加對朋友的依賴。同伴友誼包含兩個特殊要素,友誼質量與社會支持,友誼的質量越高,同伴間的相互支持程度也越高[7]。體育運動情境中,兒童和青少年同伴間的互動對建立社會關系,發展友誼具有重要作用。據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3:隨遷子女的體育參與對運動友誼質量有正向影響。
1.4 運動友誼質量的中介作用
行為科學研究中,中介變量是自變量對因變量發生影響的實質性的、內在的原因,也就是說,自變量通過中介變量對因變量產生作用。

圖1 本研究假設關系示意圖
中介變量的作用原理如圖1所示。c是 X對 Y的總效應,a、b是經過中介變量M的中介效應,c'是直接效應[8]。結合本研究已提出的3個研究假設,隨遷子女的體育參與對同伴信任有正向影響(c),體育參與對運動友誼質量有正向影響(a),運動友誼質量對同伴信任有正向影響(b),本研究提出假設4:運動友誼質量在隨遷子女的體育參與及其對城市同伴的信任間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與資料收集
被試資料的收集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預試調查。在濟南隨機選取一所公辦中學和一所公辦小學,對非本市戶籍的隨遷子女發放預試問卷150份,回收有效問卷150份。第二階段為大樣本正式調查。根據整群隨機抽樣法在濟南市4所公立學校的隨遷子女發放4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356份。調查對象的分布為11~13歲209人(11歲61人,12歲70人,13歲78人),14~16歲147人(14歲62人,15歲49人,16歲36人),平均年齡13.21±1.57歲,男生204人,女生152人。
2.2 測量工具
2.2.1 隨遷子女體育參與程度量表
采用福克斯(Fox,1987)測量體育參與程度的方案,由被試回憶過去7天的運動參與,并通過體育參與程度公式加以衡量:體育參與程度=運動頻率×(持續時間+運動強度)[9]。運動頻率賦值從“1=每周運動1次或以下”到“5=每周運動5次或以上”,運動持續時間賦值為“1=0~15分鐘”到“5=1小時或以上”,每次運動強度的賦值為“1=非常輕松”到“5=非常累”。
2.2.2 隨遷子女對城市同伴的信任量表

圖2 隨遷子女對城市同伴信任驗證標準化示意圖
依據McAllister的人際信任量表[10]修改而成。原量表包括2個維度,應用于組織中“同事”間人際信任的測量。本研究針對兒童、青少年的“同伴”關系進行修訂。首先對修訂的量表進行預試分析(n=150),量表數據呈現正態分布,11個題目通過了項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萃取出兩個因子,符合研究預期。而在“認知信任維度”的信度檢驗中,剔除了一個題項刪除后整體分量表信度Cronbach’α系數增高的題項。最終的城市同伴信任量表為認知信任5題,情感信任5題,以5點分進行測量。第二階段采用大樣本驗證性因子分析(n=356),分析顯示兩因子模型擬合良好(x2=144.09,df=34,RMSEA=0.07,CFI=0.92)。如圖2所示。
2.2.3 隨遷子女運動友誼質量量表
采用 Weiss和 Smith的運動友誼質表(SFQS,1999)[11]。原問卷含6個維度22個題目,適用于8至16歲的兒童和青少年。本研究中22個題目均通過預試分析(n=150)。“增強自尊與支持”維度,“忠誠與親密”維度,“共同性”維度,“陪伴與娛樂”維度,各4個題目;沖突化解3維度和沖突維度各3個題目。每個題目以5點計分,其中沖突維度反向計分。本研究中,驗證性因子分析(n=356)顯示6因子模型擬合良好(χ2=664.22,df=191,RMSEA=0.06,CFI=0.95)。如圖3所示。

圖3 運動友誼質量驗證標準化示意圖
3 結果
3.1 變量的適切性檢驗及描述性統計分析
3.1.1 區分效度和同源方法偏差檢驗
為保證隨遷子女的“體育參與程度”、“運動友誼質量”和“對城市同伴的信任”三組變量的獨立性,需要對正式調查的大樣本數據進行區分效度的檢驗。表1中,基準模型含35個觀察變量(體育參與3個、運動友誼質量22個,信任10個),而多因子的區分效度檢驗模型包括:1)運動友誼質量與城市同伴信任合并后(32個變量)與體育參與程度(3個變量)的兩因子模型;2)運動友誼質量、體育參與(25個變量)與城市同伴信任(10個變量)的兩因子模型;3)體育參與、城市同伴信任合并后(13個變量)與運動友誼質量(22個變量)的兩因子模型;4)體育參與(3個變量)、城市同伴信任(10個變量)、運動友誼質量(22個變量)的三因子模型;5)控制非可測潛在方法的四因子模型。從表1統計結果可知,本研究中的三因子模型與其它模型相比擬合度更佳,其中χ2/df值小于5,RMSEA未大于0.08,RMR小于0.05,CFI大于0.90。因此3因子模型能夠更好地代表研究結構,驗證了三組變量結構的區分效度。
由于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由單一來源受測者(隨遷子女)填答,需要檢驗同源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控制不可測潛在方法因子的檢驗[12],即表1中的四因子模型——將同源方法偏差當作潛變量納入結構方程模型進行擬合檢驗。結果表明,包含共同源方法偏差的結構擬合不可接受,沒有有效降低χ2值,說明本研究的同源偏差問題未對研究結構造成嚴重影響。
3.1.2 描述性統計分析
如表2所示,通過觀察各變量間的相關系數與差異顯著性,發現體育參與程度,運動友誼質量的6個變量,以及城市同伴信任的2個變量間均顯著相關,符合研究預期,有待利用多元線性回歸和結構方程模型進一步驗證其內部關系和作用機制。

表1 測量模型比較(N=356)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注:括號內為 Cronbach’α系數。*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表3 自變量與因變量多元回歸分析(N=356)
3.2 多元回歸分析
表3中,第一步回歸中,性別、年齡對運動友誼質量的6個測量因子,以及城市同伴信任的2個測量因子均未達到顯著的預測作用。第二步,引入了運動參與程度變量,該變量對運動友誼質量、城市同伴信任各個因子的影響達到顯著水平。可見,在本研究中自變量運動參與程度對因變量城市同伴的信任具有預測作用,符合進行自變量與因變量的中介效應分析的前提條件。為明確體育參與程度、運動友誼質量與城市同伴信任的關系,需要引入結構方程進一步討論。
3.3 結構方程模型的建立與檢驗
通常考慮中介變量的前提是因變量于自變量的相關顯著,自變量對因變量具有預測作用,這在上文中已經得到證實,即運動參與程度與城市同伴信任相關顯著。在此基礎上,引入中介變量后,中介作用的研究假設的檢驗,需要檢驗3組回歸系數——自變量與因變量、自變量與中介變量、以及中介變量與因變量的線性關系。本研究中,如果下面條件成立,則中介效應顯著:1)體育參與程度對運動友誼質量的回歸系數顯著;2)運動友誼質量對城市同伴信任回歸系數顯著;3)體育參與程度對城市同伴信任的回歸系數顯著(部分中介)或不顯著(完全中介)。
隨遷子女體育參與程度、運動友誼質量與城市同伴的關系模型如圖4所示,其中,體育參與程度為自變量,城市同伴信任為因變量,運動友誼質量為中介變量。結構方程模型與實際調查數據擬合關系良好,各路徑系數均達顯著,如表4所示。
中介效應的結構方程模型中,體育參與程度對運動友誼質量的回歸系數為0.71,體育參與程度解釋了運動友誼質量50%的變異量,而運動友誼質量對6個觀測變量解釋變異量在40% ~72%之間,其中“忠誠與親密”以及“共同性”兩個測量變量在模型中并非獨立的,兩者間的相關系數為0.15。在加入了變量運動友誼質量后,體育參與程度對城市同伴信任的回歸系數為0.30,運動友誼質量對城市同伴信任的回歸系數為0.74,體育參與程度和運動友誼質量兩者共解釋了城市同伴94%的變異量;同時,城市同伴信任也解釋了認知型信任和情感性信任57%和49%的變異量。

圖4 本研究體育參與程度、運動友誼質量、對城市同伴信任的結構方程模型
可見,自變量體育參與程度通過影響變量運動友誼質量來影響因變量“對城市同伴的信任”,運動友誼質量為中介變量。如表5所示。鑒于加入了變量運動友誼質量后,運動參與程度仍然對城市同伴信任的路徑回歸系數達到顯著,本研究中運動友誼質量屬于部分中介過程。其中,體育參與程度對城市同伴信任的總效應0.83是直接效應路徑系數0.30與間接路徑系數0.71×0.74的和,中介效應比為間接效應與總效應的商,為0.62,即運動友誼質量在體育參與程度和城市同伴信任的關系中具有62%的中介效用率。
4 討論
4.1 隨遷子女體育參與對城市同伴信任的正向影響
以體育參與程度為自變量,以隨遷子女對城市同伴的信任為因變量的多元回歸分析驗證了假設1,即體育參與程度對城市同伴信任產生了正向影響(多元回歸中,P<0.001)。本研究中,隨遷子女對城市同伴的信任由認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兩個維度構成。認知型信任代表隨遷子女對本地同伴可靠性和可依戀性的預期,隨遷子女會依據城市同伴正直、誠實、能力或善意等特質的不同選擇是否信任或給予信任的程度。情感型信任源于流動和城市同伴的情感交流,伴有人際互動和心理認同。無論是認知型信任還是情感型信任,在研究中都可以被隨遷子女的體育參與程度預測。假設1得以驗證也是進行“運動友誼質量”中介效應檢驗的必要條件。

表4 結構方程模型整體擬合情況表(N=853)

表5 友誼質量中介效應分析表
4.2 隨遷子女運動友誼質量在體育參與程度和城市同伴信任中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應的檢驗首先需要自變量與因變量顯著相關,進而再引入中介變量進行檢驗。本研究中假設1得到驗證,因此滿足了利用結構方程進行中介效應檢驗的條件。假設檢驗中,實際的經驗數據與結構模型擬合良好。結構方程模型驗證了如下關系:1)體育參與程度對運動友誼質量的回歸系數顯著,路徑系數為0.71,假設2得到驗證;2)運動友誼質量對城市同伴信任回歸系數顯著,路徑系數為0.74,假設3得到驗證;3)體育參與程度對城市同伴信任的回歸系數顯著,路徑系數為0.30,表明該中介效應為部分中介而非完全中介;4)就結構方程模型的整體而言,隨遷子女的運動友誼質量在體育參與程度和城市同伴信任關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部分中介效應,中介效應率為62%),假設4得到驗證。
友誼和情感的需求促使隨遷子女參與屬于分享快樂的體育運動,其中的體育群體網絡有助于創造更多的溝通機會,發展友誼關系,增進人際間的信任感。本研究中的運動友誼質量與人際信任在概念上的邏輯關系需要說明。首先,友誼和信任雖然關系密切,但卻是不同的概念。友誼是指一種親密與關懷關系,會導致互惠、信任、依戀與包容等心理和行為發生。本研究中的運動友誼質量操作化為6個維度構念,該6個維度構念也構成了隨遷子女體育參與程度和同伴信任的中介變量。體育運動能預測運動友誼質量,而運動友誼質量又能預測隨遷子女對城市同伴的信任水平。無論是信任同伴,或是被城市同伴信任對隨遷子女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學校與同輩群體的體育互動中,隨遷子女與城市同伴的友誼有了生成和維持的特殊場域,運動友誼質量概念的引入豐富了體育參與與人際信任關系機制的解釋途徑。
5 結論
5.1 隨遷子女的體育參與程度正向影響隨遷子女對城市同伴的信任,其信任的兩維結構得以驗證,即認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體育參與程度正向影響隨遷子女的運動友誼質量,且運動友誼質量的6維結構得以驗證,包括自尊與支持、忠誠與親密、共同性、陪伴與娛樂、沖突化解和沖突。
5.2 通過結構方程模型的中介效應分析,表明在三組變量的共變關系中,運動友誼質量在隨遷子女的體育參與程度及其對城市同伴信任的關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1]王婷,李慶功,何佳萍.認知情緒調節對流動兒童同伴依戀和孤獨感的調節作用[J].應用心理學,2012,18(3):256-262.
[2]王俊秀,楊宜音.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43-46.
[3]仇軍,鐘建偉.城市中體育參與與社會融合的理論研究——以大眾體育為例[J].體育科學,2010,30(12):29-33.
[4]Seippel.Sport and social capital[J].Acta sociological,2006,49(2):169-183.
[5]李偉民,梁玉成.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中國人的信任結構與特征[J]. 社會學研究,2002,(3):11-22.
[6]Carr S,Fitzpatrick N.Experiences of dyadic sport friendships as a function of self and partner attachment characteristics[J].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2011,12(4):383-391.
[7]Wallhead T L.Explaining the attraction:Understanding the motivational responses of students to Sport Education[J].Sport education: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2012:133-148.
[8]溫忠麟,劉紅云,侯杰泰.調節效應和中介效應分析[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2:37-48.
[9]Fox K R.Physical self-perception and exercise involvement[D].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Arizona State University.1987.
[10]Mcallister D J.Affect-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1):24-59.
[11]Weiss M R,Smith A L.Quality of youth sport friendships:measurement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Journal of Sport &Exercise Psychology,1999,21(2):145-166.
[12]熊紅星,張璟,葉寶娟,等.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及其統計控制途徑的模型分析[J].心理科學進展,2012,20(5):757-769.
[13]劉衛,齊國張,孫志毅.體育參與的價值認同與社會流動研究——以山東4城市各社會階層為例[J].山東體育科技,2012,34(6):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