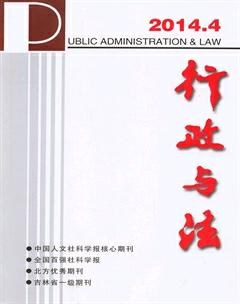南海漁業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研究
劉強 杜學道
摘 要:南海漁業知識產權保護中存在著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強、缺乏漁業地理標志、商標保護、立法不夠完善、行政保護制度及司法保護欠缺等一系列問題。應當從加強漁業知識產權相關法律法規的普及宣傳、實行地理標志知識產權保護、完善漁業知識產權立法及魚種新品種權的保護、加強行政與司法保護及二者銜接等方面完善南海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以求促進南海現代漁業經濟的發展、漁民民生的改善及維護國家的利益。
關 鍵 詞:南海漁業;知識產權;地理標志保護
中圖分類號:D9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207(2014)04-0103-05
收稿日期:2013-09-06
作者簡介:劉強(1978—),男,湖南長沙人,中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南大學知識產權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知識產權;杜學道(1989—),男,安徽亳州人,中南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知識產權。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71173191;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YBA311;湖南省創新平臺開放基金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3K009;中南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一、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對象
⒈漁業知識產權特點。漁業又稱水產業,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漁業是指從事水產生物資源利用的產業。凡是經營或管理水產生物的事業,不論是捕撈、養殖、制造或行銷,包括狹義的漁業和漁產品的銷售、休閑等。[1]而我們通常所說的漁業是指狹義的漁業,即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及漁業署對“漁業”所下之定義,指人們從水中采取動植物,并加以運用的一種經濟活動,按照生產方法之不同可分為捕撈業、養殖業、水產制造業等三大類。根據國內學者對漁業知識產權概念的界定,漁業知識產權是指漁業領域的知識產權,即民事主體對人們腦力勞動創造的發生在漁業領域的智力成果、特定標記和其他非物質信息等依法享有的專門權利的統稱。參照我國知識產權法的有關規定可以認為漁業知識產權的權利人既可以是原始取得漁業知識產權的漁業知識產權的創造者,又可以是因繼受而取得漁業知識產權的權利人。漁業知識產權作為知識產權的一種,具有知識產權的一般性屬性和特點:一是無形性,即知識產權的客體不具有物質形態。二是專有性,即知識產權為權利人所獨占使用,他人不得侵犯。權利人壟斷這種專有權利并受到嚴格保護,沒有法律規定或未經權利人許可,任何人不得使用權利人的知識產品。三是地域性,即知識產權作為一種專有權在空間上的效力并不是無限的,而要受到地域的限制,即具有嚴格的領土性,其效力只限于本國境內。四是時間性,即知識產權僅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受到保護,一旦超過法律規定的有效期限,該權利就自行消滅,相關知識產品即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財富,為全人類所共同使用。同時,作為漁業與知識產權的交叉,漁業知識產權也具有區別其他知識產權的特性,包括農業性、水域性、困難性、復雜性等。所謂農業性,是指漁業知識產權具有農業知識產權的基本特點,如包括育種、養殖、貯存等環節的知識產權。因此,漁業知識產權屬于農業知識產權的子概念。水域性,是指漁業知識產權密切聯系水域,與水產品的特性有關。困難性,是指漁業知識產權無論在創造、保護還是在應用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困難和風險,這是源于水產品的鮮活易腐性、生產季節性、水域立體性等特性。復雜性,是指漁業知識產權涉及的專業領域復雜而廣泛,從水域質量治理、苗種品質、飼料質量安全,到養殖技術及機械、捕撈技術及機械、加工技術及機械、包裝技術及設備、貯存與流通技術及裝備等,涉及環境學、生態學、生物學、工學、理學等各大學科。
⒉漁業知識產權的分類。結合《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協議(草案)》與我國有關知識產權方面的立法,知識產權主要包括版權與鄰接權、商標權、地理標志權、工業品外觀設計權、發明專利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和未披露的信息權(即商業秘密)等。具體到漁業領域,可以將漁業知識產權的主要內容概括為水產品新品種權、漁業技術專利權、水產品及其加工品的商標權(包括地理標志)、漁業商業秘密權(包括水產品育種方法、產品配方、生產工藝、技術資料、數據、管理技巧、價格信息等技術秘密和經營秘密)、漁業著作權(含計算機軟件)等。[2]按照權利屬性的不同進行劃分,漁業知識產權又可以分為經濟權利和精神權利。按照對象不同分,漁業知識產權又可分為物化于有形物質載體上的技術產品(如水產品新品種、飼料、藥劑、漁業機械等)的知識產權,與物化于知識載體上的技術文字、圖形、圖紙等新技術成果(如養殖技術、捕撈技術、漁業機械制造與修理技術、水產品JC存技術等)的知識產權。
二、南海漁業資源知識產權保護的必要性分析
⒈南海漁業資源及漁業發展概況。南海總面積350萬平方公里,90%以上被陸地包圍,是一個半封閉的陸緣海域。海域范圍內不規則的分布著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南海縱跨24個緯度,形成兼具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特征的海洋生態系統。其中歸我國管轄的約200多萬平方公里。本海區海洋捕撈漁獲量80%來自南海北部沿岸近海水域。據專家估算,南海區的漁業資源潛在漁獲量大體分布如下:⑴南海北部大陸架漁場(47.76萬平方公里)約121萬噸;⑵北部灣漁場(16.4萬平方公里)60-70萬噸;⑶西、中沙漁場(21萬平方公里)23-34萬噸;⑷南沙漁場(71萬平方公里)42-56萬噸。全區漁業資源潛在漁獲量約為246-281萬噸。南海海洋魚類品種多樣化,生物種類格外豐富。南海北部大陸架已有記錄的魚類1064種,蝦類135種,頭足類73種。[3](p335)其中主要經濟魚類80多種,品種有馬鮫、金線魚、帶魚、鯧魚、紫紅笛鯛、黃鰭金槍魚、藍園、鯊魚、石斑魚、海鰻等;主要經濟蝦類17種,品種有斑節對蝦、短溝對蝦、日本對蝦、紅斑對蝦、龍蝦等;貝類700多種,主要經濟貝類150多種,品種有鮑魚、文蛤、泥蚶、大珠母貝、珠母貝、馬氏珠母貝、企鵝珠母貝等;主要經濟藻類162種,品種有江蘺、麒麟菜等。
基于海南省水產研究所科研人員2010年至2012年數次出海調查以及赴海南、廣西、廣東三省漁港調查走訪結果,南海諸島海域漁業生產的基本情況是:⑴在南海諸島海域從事漁業生產的我國漁船絕大部分來自海南省、廣西省、廣東省,少量來自福建、浙江等省份;[4]⑵在中、西沙海域,海南省三亞市的漁船比例較多,采用燈光圍網捕撈藍圓鲹、扁舵鰹等種類,作業季節主要集中在上半年,產量波動較大;⑶在南沙海域,廣西北海漁船占大多數,主要采用燈光罩網捕撈鳶烏賊、扁舵鰹、黃鰭金槍魚、藍圓鰺等產量較高。[5]
南海海洋漁業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捕撈能力過剩、漁業資源嚴重衰退、漁船單位產量下滑、低值魚和幼魚的漁獲比例不斷增加,而優質魚類的比例則在減少,漁獲質量下降,漁業生產的虧損面不斷擴大等問題。因此,總體上來說,南海現代漁業經濟的發展面臨十分嚴峻的局面。
⒉南海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意義。在當今世界經濟、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知識產權保護已成為推動各國科學技術進步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國內國外也有越來越多涉及知識產權的爭議和糾紛,隨著對外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對我國的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就顯的格外重要。同時,在我國的漁業經濟發展中,知識產權保護下的漁業科學技術和漁業資源等在漁業科技創新中也越來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從長遠看,對南海漁業進行知識產權保護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第一,有利于支持和保障南海漁業科技的持續創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現代漁業的發展對漁業科技有著更高的要求。漁業科技的發展不僅是突破資源和環境對漁業雙重束縛的出路,同時也關系到我國南海漁業生態安全、水產品質量安全、漁業生產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因此,要想促進南海現代漁業經濟的發展,需要對漁業科學技術進行有效的知識產權方面的保護,從而激勵權利主體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以促進漁業科技能夠持續創新,保持旺盛的發展活力。第二,有利于提高南海漁業生產的綜合競爭力。加強漁業知識產權保護是提高南海漁業綜合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在世界知識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訴訟和糾紛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呈現擴大趨勢。要想提升南海漁業生產的競爭力,不僅在技術創新上國家應予以強有力的支持,而且需要加強漁業的知識經濟發展,對漁業科技創新過程中的優良成果進行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才能促使南海漁業生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第三,有利于南海漁業生產規模效益和品牌效益的產生,有利于南海漁業經濟增長,漁民增收。在南海的漁業知識產權保護中,漁業技術專利權、漁業商標權、漁業著作權、漁業商業秘密權、漁業生產地理標志權等不僅是現代漁業發展的象征,而且通過對漁業的知識產權“包裝”能更好地促進漁業知識產權轉化為漁業經濟,從而促進漁業產品價格的增加,使漁業經濟的效益規模化。
三、南海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⒈南海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現狀。我國南海海洋生物資源的利用歷史悠久,漁業發達。近年來,我國南海地區漁業經濟始終保持著良好的發展態勢。根據農業部漁政局《2011年中國漁業統計年鑒》,2010年我國全國漁業經濟總產值、增加值分別為12929.47億元和5904.11億元,其中漁業產值6751.79億元。[6]以南海漁業經濟的主力軍海南省為例,2010年,全國海洋生產總值38439億元,海南省為523億元,僅占全國的1.36%;全國漁業經濟總產值1.29萬億元,海南省為235億元,僅占全國的1.8%;全國漁業增加值3790億元,海南省為133.18億,僅占全國的3.51%;全國水產出口量333.88萬噸,海南為12.9萬噸,僅占全國的3.8%;全國水產品出口額138億美元,海南為4.76億美元,僅占全國3.4%。我國是世界水產養殖第一大國,養殖業占世界的70%。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之后,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雖然我國漁業出口量較大,但占我國漁業總產量比重很小。有資料統計,2009年我國水產品出口僅占我國水產品總量的5%,出口額在世界水產品貿易中也僅占其總量的8%。[7]南海地區的廣東、廣西、海南三省在我國漁業對外貿易中更是占有極其微小的比重。與東南亞及漁業發達國家相比,南海地區三省雖是水產品生產大省,卻算不上是水產品出口貿易大省。同時與這些漁業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相比,南海三省在水產品貿易方面,缺乏水產品知名品牌、知名商標,缺乏足夠的生產技術及商業保護,綜合競爭力遠遠不及一些發達國家或地區。
在水產品中,我國漁業方面的專利數量與其他一些漁業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相比遠遠不足。有學者曾對我國漁業專利和我國臺灣地區漁業專利進行過比較總結。在2009年公布的一項研究成果表明,中國大陸漁業技術已公告專利合計有6145件。2002年突破每年100筆的公告專利,隨后呈現大幅度的成長態勢。其中捕撈技術在2004年達到最高峰,有245筆專利,而后發展趨緩;養殖技術在2007年到達最高峰,有383筆專利,水產制造則有324筆專利申請。相比之下,臺灣地區漁業技術已公告專利合計有2230件。[8]在數量絕對值上,我國大陸漁業專利是臺灣地區漁業專利的近三倍,但是鑒于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在漁業總產量、地域大小等方面的巨大差異,相對來說,我國大陸的漁業專利數量遠遠不夠。同時有不少的報道指出,臺灣地區的一些漁業知識產權主體,擁有我國內陸地區不少數量的漁業專利。從我國目前漁業專利的實際發展情況來看,我國漁業專利數量很少,同時漁業專利的質量也不高,而在實際上真正屬于內陸漁民的漁業技術專利也不多。南海漁業專利相比之下更是少之又少,能夠有記錄的漁業專利數量屈指可數。
⒉南海漁業知識產權保護中存在的問題。第一,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強。目前,南海漁業行業大都是中小企業,從事漁業科技推廣工作的人員中,職稱達到正副高職稱的人員少之又少,大量的是初級技術人員和其他人員,人員結構不合理,對提高漁民的科技素質有很大的影響,漁民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有關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同時,長期以來,有關漁業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研究和論文幾乎為零,真正從事漁業知識產權研究工作的專家學者極為鮮見。漁業科技工作人員、科研機構和科研工作人員很輕易地便將漁業知識產權方面的技術、成果公之于眾,由于沒有申請相關知識產權,其成果容易被國內外的企業或是研究機構無償使用,導致知識產權的無形流失。政府有關部門對漁業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也缺乏足夠的認識。第二,缺乏對漁業的地理標志保護、漁業品牌商標的創新創建。地理標志是一個地區象征性的“名片”,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有著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南海漁業資源異常豐富,其中的海南省、廣東省、廣西自治區更是我國水產資源與水產品生產大省,具有豐富的水產品地理標志資源。截止2010年12月31日,海南已注冊的地理標志農產品僅有12種,主要是瓊中蜂蜜、文昌雞、臨高乳豬、澄邁福橙等,其中與漁業有關的地理標志為零。[9]廣東省地理標志保護工作做的相對較好,在2008年因有31個國家地理標志產品,地理標志產品數量躍居全國第一。如:河源米粉、郁南無核黃皮、廉江紅橙、馬壩油粘米、增城絲苗米、端硯、流沙南珠、惠來荔枝等共31個產品獲國家地理標志產品保護,全省共有21家企業獲準使用地理標志產品專用標志。而與漁業有關的地理標志卻為零。截止目前有中山脆肉鯇、南澳魚露、南澳牡蠣地理標志產品等極為少量的與漁業有關的地理標志產品。廣西與漁業有關的地理標志產品也為數極少。在北京市法院2012年知識產權訴訟十大案例中,“舟山帶魚”證明商標案被列為其一,主要涉及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保護問題。案件起因如何暫且不說,但足以看出“舟山帶魚”這一漁業方面的地理標志品牌的廣大知名度。第三,相關法律法規的立法不足影響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如前文所述,南海海洋魚類品種格外豐富多樣,據資料記載南海北部大陸架已有記錄的魚類就多達1064種,有諸多魚類資源已屬極為珍貴的漁業稀有品種。然而關于海洋魚類種質資源保護等方面立法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漁業新品種權的保護。例如,我國現行《專利法》第25條就明確規定對新品種不授予專利權。我國目前僅對人工培育的動物生產方法授予專利權,而對動物品種本身不授予專利權。然而在現代化的溫控技術和基因誘導調控技術手段下,重復生產出穩定的同一魚類品種已經成為現實,如不對此類魚種本身進行保護,不僅會挫傷中國漁業科研人員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也使得我國的生物技術保護水平與世貿組織規則中所規定的保護水平相差甚遠。第四,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不夠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力度嚴重不足。政府漁業行政及漁業知識產權保護有關部門缺乏對漁業相關制度的制定,在行政執法過程中,對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這一模式也存在認識上的不足,不能有效地保護漁業知識產權主體及漁民的合法權益。在涉及漁業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訴訟中,多數情況下存在即使法院作出了對侵權人相應處罰的判決,然而在實際執行工作中,執法力度嚴重不足,很難保護漁業知識產權主體的利益。與此同時,行政保護與司法保護兩種模式在適用過程中也經常發生相互沖突的狀況,行政機關和法院之間互相推諉,導致最終出現漁業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蒙受重大損失的結果。
四、南海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建議
⒈強化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漁業科研單位要加強學習與漁業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律法規、保護措施,逐步增強知識產權意識。由于對漁業知識產權缺乏較多的研究和關注,人們對漁業知識產權了解也不多,因此對漁業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進行宣傳、普及顯得尤為重要。首先,有關部門可以考慮將知識產權納入科技管理的范疇,引導人們逐步形成尊重他人知識產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習慣;其次,漁業科技管理人員要加深對國際規則的了解,彌補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參與市場競爭經驗;最后,在現代化通訊、媒體迅猛發展的情況下,有關部門要積極利用多種形式,多渠道、多層次地在全社會廣泛開展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宣傳。相關職能部門要積極利用報紙、廣播、電視等容易接觸到的大眾傳媒進行漁業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宣傳和教育,努力提高國民的法律意識和尊重知識產權的自覺性,減少越權違法事件的發生。
⒉加強對南海漁業資源的地理標志知識產權的保護。地理標志,又稱原產地標志(或名稱),TRIPS協議第22條第1款將其定義為:“其標志出某商品來源于某成員地域內,或來源于該地域中的地區或某地方,該商品的特定質量、信譽或其他特征主要與該地理來源有關。”我國2001年修訂后的《商標法》也增設了地理標志方面的規定,其第16條第2款規定:“前款所稱地理標志是指標示某商品來源于某地區,該商品的特定質量、信譽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該地區的自然因素或人為因素所決定的標志。”申請地理標志證明商標,是目前國際上保護特色產品的一種通行做法。通過申請地理標志證明商標,可以合理、充分地利用與保存自然資源、人文資源和地理遺產,有效地保護優質特色產品和促進特色行業的發展。
地理標志對南海漁業資源的保護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⑴發揮南海漁業資源的比較優勢;⑵能夠發揮市場引導與企業組織效應,推進和提升漁業產品的產業化、規模化;⑶通過技術監控、嚴格的質量技術審核能夠提升漁業產品的質量標準;⑷有力促進市場對南海漁業產品的認知,南海漁業產品品牌的形成,提升漁業產品的核心競爭力;⑸能夠提升南海漁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漁業產品與國際接軌,提升南海漁業產品的對外貿易能力;⑹品牌效益會促進漁業產品附加值的提升,增加漁民收入,促進漁民生活的改善。鑒于此,加強對南海漁業資源的地理標志保護勢在必行。
⒊建立健全漁業知識產權立法,加強魚種新品種權保護。南海不僅漁業資源極為豐富,周邊各省還有眾多高等院校,可謂自然資源和科教資源得天獨厚,具備產生和形成漁業種類資源新品種的條件,因此在立法層面要建立健全漁業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體系,完善《專利法》第25條關于動植物新品種授予專利權的規定,并能根據我國漁業資源及南海漁業資源的特定情況,出臺針對漁業新品種保護和生物技術的專利保護的法律法規。同時加強對南海漁業資源的新品種權的知識產權戰略規劃,提高魚種新品種權的保護意識,將南海豐富的漁業種類資源優勢轉化為知識產權優勢。為南海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南海現代漁業經濟的長足發展。
⒋從司法與行政執法層面加強南海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目前,我國對知識產權保護實行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與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并行的“雙軌制”保護模式。其中,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是行政機關對知識產權的全面保護,指行政機關依據法定職權和程序,依據權利人的申請或其他法定方式,履行職責,授予或確認權利人特有權利,管理知識產權使用、變更、撤銷等事項,糾正侵權違法行為,保護各方合法權益,維護知識產權秩序的活動。[10]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指對知識產權通過司法途徑進行保護,即由享有知識產權的權利人或國家公訴人向法院對知識產權侵權人提起刑事、民事的訴訟,以追究侵權人的刑事、民事責任。
從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角度來說,應當強化漁業知識產權保護中行政部門的職責。漁業行政部門應指導、監督、保護、管理好漁業知識產權。鑒于漁業知識產權保護并非為廣大漁業科研機構、漁民、企業等與漁業知識產權密切相關的單位或個人所熟知,因此應做好宣傳、普及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知識等。同時,充分發揮行政保護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行為主動性、手段多樣性、成本低、高效快捷的特點,為漁業知識產權保護服務。
從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角度看,司法保護具有穩定性,專屬性,效力的終級性,公平優先性及規范性,注重對權利人的賠償等優點,但司法保護一般是被動的保護。所以在實際中,應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優點,讓司法保護在南海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中起到積極有效的促進作用。
在漁業知識產權保護中,既要發揮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功能又要充分利用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來保護南海漁業知識產權保護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同時更要做好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與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之間的協調、銜接工作,以更好的做好南海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
【參考文獻】
[1]陳新軍.漁業資源與漁場學[M].海洋出版社,2004.
[2]吳漢東.知識產權法(第四版)[M].法律出版社,2011.
[3]唐啟生.中國區域海洋學—漁業海洋學[M].海軍出版社,2012.
[4]麥日利.南海諸島海域漁業捕撈現狀及發展建議[J].福建水產,2012,(04):346.
[5]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中國水產科學發展報告(2005-2007)[M].海洋出版社,2008.
[6]農業部漁政局.2010年全國漁業統計情況綜述[J].2011中國漁業統計年鑒,2012.
[7]劉博濤,丁衛國.中國水產品出口主要市場的比較分析[J].世界農業,2008,(04):46.
[8]季任天.我國漁業知識產權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J].中國漁業經濟,2010,(05):7.
[9]王紅衛.“三亞芒果”成三亞首個地理標志商標[N].海南日報,2013-04-14(A7).
[10]曲三強,張洪波.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問題研究[J].政法論叢,2011,(03):57.
(責任編輯:徐 虹)
Abstract:A number of problems can still be found in the IPR Protection of the fishing indust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lack of IPR protection awareness,geographical indication; the legislation is yet to be improved;the protection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judicial departments is badly in need.To tackle these problems,we shall improve the IPR protection of the fishing industry by making more effort to publicize and populariz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evant to the IPR protection of the fishing industry,implementing the IPR protec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improving the legislation related to the IPR protec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new fish species,intensifying the combined protection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the IPR protection of the fishing indust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rough these efforts,we can expect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fishing indust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improving the state of living of the fishermen and secure the interests of China.
Key words:South China Sea;Fishery;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