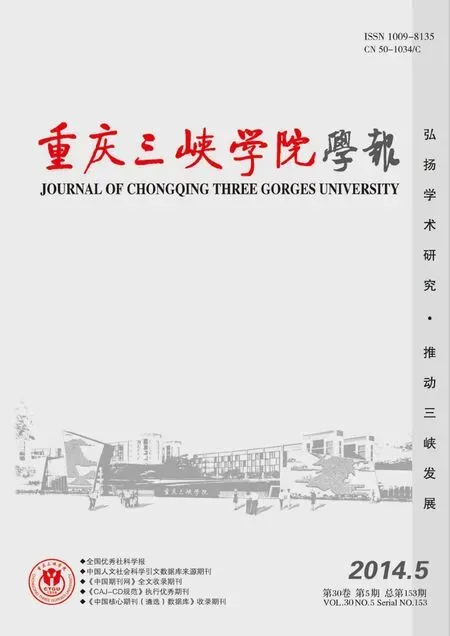胸中山水奇天下,刪去臨摹手一雙——石濤與汪野亭山水畫比較
林文賢
?
胸中山水奇天下,刪去臨摹手一雙——石濤與汪野亭山水畫比較
林文賢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華中師范大學汪野亭研究所;湖北武漢 430079)
以汪野亭的山水瓷畫為對象,結合石濤的繪畫作品及繪畫理論,從汪野亭山水瓷畫的構圖、造型、筆墨三方面入手,探求石濤的山水創作對汪野亭的山水瓷畫的影響,尤其是汪野亭作品中堅持石濤“搜盡奇峰打草稿”的創作理念和堅守“我為我法”的藝術追求。
石濤;汪野亭;構圖;繪畫技巧
中國山水畫最早出現在東晉顧愷之的傳世摹本《洛神賦圖卷》的背景中,隋唐時期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畫科,五代至北宋達到高峰,理法大備,名家輩出。與此同時,山水題材也慢慢進入了同樣具有繪畫成分的陶瓷業。早在唐代長沙窯中就已現身“以瓷代紙,將畫入瓷”的山水瓷畫。之后歷經宋、元、明,到了雍正時期出現了粉彩山水瓷畫,山水瓷畫發展達到了高峰。清末粉彩山水瓷畫日益衰退,到了咸豐、同治年間,文人畫師程門、御長畫師金品卿、王少維等開創了淺絳彩文人山水瓷畫,為死氣沉沉的山水瓷畫業吹入了一股清風。可惜淺絳彩文人瓷畫只風行了半個多世紀便呈現衰退之勢,真正將文人瓷畫完善并使其完成由工藝到藝術的質變的是以汪野亭為代表的新粉彩山水瓷畫家們。
汪野亭是汪派山水瓷畫的創始人,也是“珠山八友”中最重要的山水畫家之一。他私塾教學出生,22歲離開樂平老家,前往江西波陽“陶業學堂”學藝。起初師承彩瓷名家張曉耕、潘匋宇學繪花鳥,后赴景德鎮學習專業繪瓷,此期他主要沿襲以程門為代表的淺絳彩文人瓷畫家對文人風格的追求,并師法王翚、沈周偏重于技法形式,以青綠工筆山水設色技法繪瓷,用筆工細嚴謹,線條細長,很少皴擦,體現了他“皴擦不可多,厚在神氣”的繪畫主張。如其作于1920年的《南屏晚鐘圖》瓷板畫,用筆精到,工麗嚴謹,法度整飭,體現出他一絲不茍的創作態度。后來,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收藏界掀起了一股“石濤熱”并很快蔓延到了中國畫畫壇。國畫畫家們都爭先學石濤、仿石濤。當時被稱為“石濤再生”的張大千就因此而一舉成名。汪野亭后期受石濤的影響也頗深,他“主攻山水,初習清初‘四王’,繼而崇石濤。”[1]35本文便試著從構圖、造型、筆墨三個方面,談談石濤對汪野亭山水瓷畫創作影響。
一、構圖——“具無俗跡”
南齊謝赫在《古畫品錄》的“六法”中把構圖稱為“經營位置”而列為第五法。[2]現在人們一般稱它為“構圖”或“布局”。中國山水畫構圖大多遵循兩種傳統章法,也就是石濤在《畫語錄·境界章》中所說的“三疊兩段”,“三疊”,“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兩段”,“景在下,山在上,俗似云在中,分明隔做兩段。”[3]269但石濤在創作中并不滿足于對這兩種模式的機械套用,而講求繼承與創新,所以他的山水畫構圖新穎獨特,角度豐富多樣,或全 語錄》中也有段對造型的經典論述,首先他將藝術景呈現,或局部特寫,變幻無窮。“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就是他的《畫語錄》中所傳遞的繪畫美學思想。鄭板橋曾評述他說:“石濤畫法,千變萬化,離奇蒼古而又能細秀妥帖,比之八大山人殆有過之無不及。”[4]160
汪野亭在其山水瓷畫的構圖上服膺石濤這種“具無俗跡”的創作理念,他一方面總結并吸收了石濤很多獨創性的構圖方法,另一方面還結合瓷器的外形特點推陳出新,匠心獨運地使用了“通景山水”的構圖方法。前者,如其作于1931年的《蘇堤春曉》及其《半潭秋水一房山》瓷板畫與石濤的《古樹垂陰圖》極為相似。兩者皆意象繁復、層次分明,采用凹狀三段法,近坡坨、老樹(高),中小橋流水(低),遠為峰巒白云(高),洋溢著一種清新靜謐的書卷氣。再如其《湖山秋色》粉彩瓶與石濤的《清湘小來》都采用了近景高山遮眼,遠景采用平遠法一覽無余的布局。此外,其《野航恰》瓷板畫在構圖上也沿用了石濤的《黃山圖冊21開之十三》的構圖方法。石濤在該作中拋開傳統,特寫崖壁上一伸展著的“平頭”古松,其它地方留白,而汪野亭則重點特寫了陡崖上一株海棠。還有他的《梅花通曉夢》、《春江曉渡》等瓷板畫,構圖多用平遠法和高遠法,令觀者隨江流游走,景意相連,明顯帶有石濤從北京回到揚州沿運河南下所作的《石濤江行畫冊》的影子。后者,在汪野亭之前“景德鎮傳統山水瓶類,大多采用錦地開光畫法,即瓷瓶通身或上下畫圖案錦地,留出幾個部位小面積開光(亦稱“開框”),在開光部分作山水畫。還有一種就是半畫半字,即一面作山水畫,另一面題跋。”[1]36而汪野亭的“通景山水”構圖法,則如其所作《林泉到處皆名勝》墨彩瓶,結合了瓷瓶的立體外形,別具匠心地繞瓷瓶作一幅具有完整構圖的山水畫,使瓷瓶在各個角度看都是一個完整的畫面,而且,還可以將瓷瓶旋著觀賞,首尾相連、循環往復、意境無窮。這種“通景山水”構圖法獨特新穎,開20世紀初景德鎮粉彩山水裝飾章法的新風,至今仍是陶瓷界評定陶瓷裝飾水平的重要標準。
二、造型——“不似似之”
繪畫反映生活離不開具體的形,古人早已有“應物象形”、“以形寫形”[2]之說。石濤在其《畫創作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山川脫胎于予也”,二是“予脫胎于山川也。”[5]79然后,他進一步指出了通往藝術世界唯一的途徑是感受和理解自然山川的內在生命,即“搜盡奇峰打草稿”,才能達到“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于大滌也”[5]79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正是這種對主體意識滲入的強調,促使其能擺脫客觀束縛任意揮灑馳騁于“江花隨我開,江水隨我起”[5]175的無疆境界中的奧秘。此外,石濤還進一步在其《畫語論》中闡明如何實踐“不似之似”的造型方法。首先在于“黃山是我師,我是黃山友”的廣泛體驗,接著進入“心期萬類中,黃峰無不有”的典型化過程;然后,發揮主體主觀能動性進行“對景不對山,對山不對景,倒景,借景,截斷,險峻”[3]的選擇、加工、創造;最后達到“夫畫,從于心也”的人景合一至高境界。這也就是石濤所提倡的“一畫”繪畫美學觀點,所謂“一畫”,即“一根造型的線,畫家憑借這根造型的線為天地萬物傳神寫照。”[6]211
石濤 瞎尊者原濟 汪野亭 孤蓬萬里征
汪野亭十分心儀石濤的藝術理念,他“樂山樂水,師山師水,足跡遍及景德鎮周邊名山大川,力求像石濤那樣‘搜盡奇峰打草稿’,反映在瓷畫上筆墨雄健縱恣,深得丘壑意趣。”[7]205熊中富先生編的《汪派山水瓷畫》中也說他:“深刻體會石濤山水之精髓,石濤‘搜盡奇峰打草稿’的創作精神,始終激勵著他潛心默會,發奮揮毫。汪野亭別開生面地將國畫山水的神韻融入陶瓷創作之中,體現石濤風格的‘南國水鄉’、‘江春風雨’、‘柳岸清秋’、‘枯樹寒鴉’等題材,汪野亭一次又一次以瓷畫形式展現在世人面前,使瓷畫山水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汪野亭也因此而享譽瓷壇。”[1]35他“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所繪景物皆融合了其精神情感的表達,而絕非某處景物的簡單再現。他自己還作過“深深落葉迷行徑,莫知何峰與路橋”的詩句來闡明其在創作中對主觀能動性的追求。
此外,汪野亭還借鑒了石濤作品中很多人物、小橋、瀑布水口、松樹等具體造型的處理方法。人物方面,如其作品中古樸的寬衣高士,或觀景、研讀、閑談,或拐杖訪友、舟中垂釣,衣紋線條流暢,面部筆簡神足;而且也同樣常用粗筆揮灑出淋漓蒼茫的背景,或古松、或枯柳、或桐蔭,用以襯托高士的偉岸、超邁。其次,石濤善于畫松,在黃山奇松的影響下,其松絕少古代那種挺立的長松,大多枝干伸展,松針茂盛,似乎圍蓋在枝干上。汪野亭的很多松樹也有石濤的面目。

人物:左石作,右汪作 松樹左石作,右汪作
再如,他們都喜歡在畫中設置茅舍和各種小橋。石濤曾解釋到:“高人讀書處,取徑非人寰。尤愛茅檐際,梅花雪裹山。”[5]也許是因為他們都愛與“高人”相關的題材,所以,“徑”和“茅檐”也都成了他們畫中的一個標志。汪野亭畫中的很多小橋和茅舍也都是參考石濤畫作而來。此外,古人言“遠山難置,遠水難安”,汪野亭在安置畫中的瀑布水口時也受到石濤的很多啟發。

小橋:上汪作,下石作 水口:左石作,右汪作
三、筆墨——“蒙養生活”
北宋韓拙《論用筆墨格法氣韻病》中提出:“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8]322,指筆墨不僅能造形,還能傳神,它構成了中國畫形式美感和審美要求的基本特征。石濤也曾說過:“夫畫者,形天地萬物者也。舍筆墨何以形哉?”[3]他還認為在山水畫的創作中“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3],指“蒙養”與運墨關系密切,“生活”與操筆關系密切。因為墨氣的干濕濃淡能充分體現大自然的渾然一體,即“蒙養之靈”;筆的勾勒皴擦能充分體現大自然的千姿百態,即“生活之神”。同時,筆、墨又是圓融一體的,墨氣依筆之揮灑方能使萬物渾成一體,顯示出和諧美;筆依墨氣之暈染方能使天地包羅萬象,顯示出氣象萬千之妙。因此,他為表現“山川萬物之具體”[3]采用了很多獨創性的筆墨之法。
如前所述,汪野亭在1927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開始將重心從“師古”轉向“師造化”,他“搜盡奇峰打草稿”學習的不僅是大自然無奇不有的造型,還有石濤所提倡的在“生活”中領悟山水的內蘊和生命力,尋找更能表現“生活”的筆墨畫法,從而做到“胸中脫去沉濁,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鄄鄂,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矣”。[9]999所以,他吸收運用了石濤來源于“生活”的很多筆墨用法。如石濤畫山石,常先用流暢凝重的中鋒線條,或干毛松柔的側縫勾勒山體的輪廓脈絡,然后用不同的皴法皴染來表現山巒的凹凸和體積感。他常用的“大披麻皴”和“牛毛皴”,就是在繼承董源、黃公望的披麻皴和王蒙的解索皴的基礎上,結合自己實際的繪畫經驗創造出來的。而汪野亭的山水瓷畫,“早期畫風摹古,淺絳彩風格兼粉彩乾隆細路,畫品嚴謹,中期效法四王,筆墨洗練,蒼勁整潔,設色滋潤,晚期追慕石濤,用筆潑辣,墨氣淋漓,氣勢高遠。”[1]35他的彩繪江山春色圖提梁壺[10]及其落款為“烏目山下人法”的瓷板畫就都用了石濤獨創的牛毛皴。石濤的點法亦隨性而變豐富多樣,耐人尋味,“點:有雨雪風晴四時得宜點,有反正陰陽襯貼點,有夾水夾墨一氣混雜點,有含苞藻絲纓絡連牽點,有空空闊闊干燥沒味點,有有墨無墨飛白如煙點,有焦似漆,邋遢透明點。更有兩個點,未肯向學人道破:有沒天沒地當頭劈面點,有千巖萬壑明凈無一點”。[6]260汪野亭的《松林策杖》、《孤蓬萬里征》等瓷板畫的點法也都與石濤的點法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汪野亭謹記石濤“我為我法”的教誨,在學習石濤的筆墨畫法時,既不拘泥于前人技法的桎梏,又能緊貼“生活”,不以立異為標榜。他的畫作在纖毫微墨間都融入了濃厚的主體精神,“所畫雨景潑墨淋漓,極有氣勢,無論是朦朧煙雨,或是大雨滂沱,均能發揮墨氣暈染、流動酣暢的特點”[1]38,使山川水木動靜有致、生機盎然,畫面意境開闊,氣韻動人,從而真正達到了“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9]586的境界,“顯示出對墨色處理的造詣,從而構成了他瓷畫藝術的特點”[1]38。
四、結 語
汪野亭以其卓絕的藝術成就享譽當今的國內外畫壇,即使是同為民國景德鎮繪瓷名家的汪大滄還常常師法他的畫法。作為一位悟性很高的畫家,在掌握了石濤的一些畫理、畫論、畫法之后,不管是師古人還是師造化,他的很多創作理念都或多或少的受其影響。而他自己也十分感謝先賢對他瓷畫事業的啟發,為此他將自己的“畫齋命名為‘平山草堂’,緣于石濤辭世后葬于‘平山堂’之‘萬松嶺’。為仰慕先賢,汪野亭將長子汪小亭又名‘汪松’;次子汪少平又名‘汪柏’;三子取名‘汪青’,寓意‘松柏常青伴野亭’。”[1]38但汪野亭仿石濤、學石濤絕不僅僅滿足于技法上的機械模仿,更在于“搜盡奇峰打草稿”和“我為我法”的藝術創作精神的追求[11]。正是這份師古卻不拘泥于古的藝術精神鞭策著他在藝術上越走越遠,為二十世紀的中國陶瓷繪畫增添了獨特的一筆。二十世紀已經走遠,但汪野亭用其一生對藝術的鉆研與追求的學習精神,仍然是我們每一個當代人學習的榜樣。
[1]熊中富.汪派山水瓷畫[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2]張紅.石濤對張大千山水畫創作的影響[D].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3]楊成寅.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石濤[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4][清]鄭燮.鄭板橋全集[M].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
[5][清]石濤.周遠斌點校.苦瓜和尚畫語錄[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
[6]翰林德.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石濤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7]劉渤,高士國.一世朗潤——民國瓷器特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8][宋]韓拙.山水純全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卷八[M].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9]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10]徐明岐.提梁壺鑒賞[J].收藏,2006(1).
[11]夏斯翔.淺析汪野亭瓷板畫藝術的風格特征[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3(6):66-70.
[12]邱巧.意象與中國山水畫[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
(責任編輯:鄭宗榮)
Painting from Nature and Innovation: a Comparison of Realm of Landscape Painting between Shi Tao and Wang Yeting
LIN Wenxian
This paper, taking three aspects of composition, painting technique and painting from nature and innovation spirit as point of departure,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Shi Tao’s painting theory on Wang Yeting’s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s of landscape. The artistic pursuit of Wang Yeting’s use of Shi Tao’s theories “Make a draft with all unique peaks exhausted” and “No way is better than mine” is specifically investigated.
Shi Tao; Wang Yeting; composition; painting technique
J211
A
1009-8135(2014)05-0069-04
2014-04-27
林文賢(1988-),女,廣東汕頭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文藝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