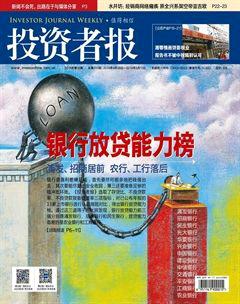新聞不會死,出路在于與媒體分家
傳統媒體正經歷著最艱難的時刻。身處這個行業中的人們一段時間以來頻繁地聚會,在憂心忡忡的情緒中,人們流露出更多的卻是對新聞業前景的擔心。人們可以接受媒體轉型、甚至消亡,但人們無法接受“新聞”這個東西邊緣化,此時,我所看到的完全出于公益而非私心,人們知道社會一旦失去“新聞”,那將多么悲劇。
人們為什么發自心底熱愛“新聞”,“新聞”到底之于我們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到底在哪兒?
我們都知道,一般意義上新聞是指有關最近發生的事情的報道,但這并不是新聞的全部。實際上,新聞包含著對事實的陳述和對事情的看法(評論)。人們之所以認定新聞機構對事實的陳述和對事情的看法更加權威,在最基礎的意義上并不是因為新聞機構可以更加準確地陳述事實,或者新聞機構發表了最無可辯駁的言論,而僅僅因為新聞機構所處的立場——它獨立于任何當事方。
舉個例子,在最近大陸游客與港人就小孩子當街大小便出現的“罵戰”事件中,孩子的父母與港人都各自陳述了“事實”,各方還都有視頻、物證和證人來幫助陳述,各方觀點也都聽起來振振有辭。
那么對于旁觀者來說,到底應該聽誰的就成了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這時,來自新聞機構的對“事實”的陳述和對事件所做出的評論往往會起到讓公眾達成一定程度的妥協和共識的作用。盡管這種作用是有限度的,但顯然要比無限度的爭吵好得多。
類似這樣的事情天天發生,大到政府活動、小到鄰里糾紛。資本市場里股東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官員與群眾之間,明星與粉絲之間都無時無刻不發生著各種各樣的事情,當這些事情被新聞機構報道出來時,人們通過這些“新聞”來了解周圍的世界。
我正是因為這樣看待“新聞”,所以就無法接受一些新潮人士提出的“新聞已死”的說法。在我眼中,這些新潮人士把自媒體的迅猛發展定義成了人人都可以做新聞,這實在嘩眾取寵了。
我無意神圣“新聞業”,好像這份職業只有新聞人才可以做,一般人做不了。相反,從技能意義上,新聞從業比起律師、會計師或者服裝設計師要容易得多,它真正難的地方在于你要從別人那里獨立出來,你要成為一群與當事方分離的人。這一立場成就了新聞業,也為新聞人贏得尊重。
當對我身處的行業做出這樣的思考后,我相信新聞業的未來不但沒有迷茫,反而更清晰了。我相信社會公眾大多數各有生計而更加需要一群專業的獨立的人群,來保守社會平衡的底線。對于新聞業,它最大的價值不止于維持公平、公正、公開,它更是對社會少數意見的保護,從而讓他們不被多數力量壓倒甚至消滅。
對新聞業的信心不足以解決當下傳統媒體的困難,人們更希望看到解決之道。只可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成功,所以,一個確定的答案是無法給出的。我只能把我一段時間以來的感悟總結于此,看看能否對有意投身于這個行業的,以及行業中的人有所幫助。
在我看來,傳統媒體轉型意味著兩種功能的分離。一個是新聞功能,一個是傳播功能。以報紙為例,報社一直既負責報道新聞,又負責傳播新聞。在互聯網時代,報紙的傳播能力已經完全被互聯網替代了,這時,你只剩下報道新聞這一項工作。有的人可能把少一件工作看作是新聞作用的減小,但在我看來,反而是新聞責任的擴大和機會的到來。
報紙期刊業的凋敝還有一個顯著的特征,那就是廣告作為主要收入的大幅下降。當收入沒有了,新聞業又如何得以維持呢?持這看法的人可能沒有注意到,報紙損失廣告收入并不是因為它們新聞做得不好,而是因為它們的讀者流失了。也就是如前所說,負責傳播的工作已經失效,那么你這一部分工作帶來的收入流失不是再合理不過的事情嗎?
我的結論可以簡單地這樣說,對于傳統媒體,要么放棄傳播、專心做新聞,要么就融入互聯網。至于能否活好,那就不是面包有沒有的問題,而是會不會做面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