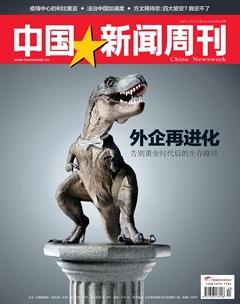中共“依法治國”展示習(xí)式風(fēng)格
蔡如鵬

剛剛閉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份在中共中央總書記習(xí)近平主導(dǎo)下形成的文件,展示出鮮明的習(xí)式風(fēng)格。
通過對比不難看出,《決定》中很多觀點,在習(xí)近平最近的一系列講話中都已有所體現(xiàn)。自2012年11月的十八屆一中全會以來,習(xí)近平先后十余次就法治建設(shè)發(fā)表論述,從立法到執(zhí)法、司法均有表述。其中,“把權(quán)力關(guān)進制度的籠子里”“任何人都沒有法律之外的絕對權(quán)力”等表述已廣為人知。
本屆四中全會將中共近二十年來對依法治國的探索作為主題,并通過會議《決定》把它上升為全黨的意志,在中共執(zhí)政65年歷史上尚屬首次。
很多時政觀察人士都注意到,全會發(fā)布的公報首度將“深入貫徹習(xí)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與已經(jīng)載入黨章作為中共指導(dǎo)思想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xué)發(fā)展觀相并列,釋放出現(xiàn)任最高領(lǐng)導(dǎo)人的思想體系已經(jīng)納入到最高意識形態(tài)理論體系之中的信號。
輿論認為,習(xí)近平“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與歷代領(lǐng)導(dǎo)人并列,是中共黨內(nèi)對習(xí)近平最高領(lǐng)導(dǎo)人地位的一種尊崇。而仔細研讀習(xí)近平的相關(guān)論述,不難發(fā)現(xiàn),他依法治國的思想是從地方到中央,局部到全局,逐步形成的。
憲法至上
2002年到2007年,習(xí)近平主政浙江,先后任省委副書記、代省長,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在浙江工作三年后,2005年初,習(xí)近平在省委提出了“法治浙江”的理念。他親自主持“法治浙江”重點課題,先后深入基層40多個鄉(xiāng)村、社區(qū)和單位開展專題調(diào)研。
2006年浙江省委作出了建設(shè)“法治浙江”的重大決策,通過了《中共浙江省委關(guān)于建設(shè)“法治浙江”的決定》,“法治中國”在省域?qū)用骈_始大膽實踐與探索創(chuàng)新。
習(xí)近平主政浙江期間,曾以筆名“哲欣”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fā)表了232篇短論,其中有很多文章就是專門談法制的。如今,這些文章都收錄在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之江新語》中。
2012年12月4日,剛當選總書記20天的習(xí)近平,就在紀念現(xiàn)行憲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會上高調(diào)宣示“憲法高于一切”。
“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zhí)政,關(guān)鍵是依憲執(zhí)政。新形勢下,我們黨要履行好執(zhí)政興國的重大職責(zé),必須依據(jù)黨章從嚴治黨、依據(jù)憲法治國理政。黨領(lǐng)導(dǎo)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lǐng)導(dǎo)人民執(zhí)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nèi)活動,真正做到黨領(lǐng)導(dǎo)立法、保證執(zhí)法、帶頭守法。”習(xí)近平說。
2014年9月初,習(xí)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重申依憲治國、依憲執(zhí)政。
在剛剛過去的紀念政協(xié)成立65周年大會上,他更是七次提到憲法,一再強調(diào)要忠于憲法,依憲治國,依法治國。
此次四中全會《決定》,將加強憲法實施放在推進依法治國任務(wù)放在重要位置,提法也與習(xí)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表述相近。
不過,四中全會沒有僅僅停留在對依憲治國、依憲執(zhí)政的重申上,公報進一步明確,“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jiān)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
去年11月召開的三中全會,曾提出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jiān)督機制和程序。輿論認為,四中全會明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為主體,而且具體指出要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可以說是在依憲治國的方向上又推進了一步。
國家行政學(xué)院教授汪玉凱認為,四中全會特別強調(diào)依憲執(zhí)政,依憲執(zhí)政又主要強調(diào)中共執(zhí)政和領(lǐng)導(dǎo)法律建設(shè),這樣一來,中共本身也必然在法律范圍內(nèi)活動。
2.0版依法治國
汪玉凱還認為,此次公報提及“實現(xiàn)科學(xué)立法、嚴格執(zhí)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具體目標,涵蓋了執(zhí)政黨進一步加強司法獨立的邏輯思路。
他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是依法治國的1.0版。剛剛發(fā)布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科學(xué)立法”等新十六字方針已是升級版的2.0版。
而“科學(xué)立法”等十六字方針在習(xí)近平此前的講話中也早有提及。
2013年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第四次集體學(xué)習(xí)。習(xí)近平在講話中談到,要全面推進科學(xué)立法、嚴格執(zhí)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zhí)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shè),不斷開創(chuàng)依法治國新局面。
在2014年1月7日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xí)近平曾說,“經(jīng)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jīng)形成,總體上解決了有法可依問題。現(xiàn)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應(yīng)該是保證法律實施,做到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有了法律不能有效實施,那再多法律也是一紙空文,依法治國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幾個月后,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他再次強調(diào),“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違法不究現(xiàn)象,堅決整治以權(quán)謀私、以權(quán)壓法、徇私枉法問題,嚴禁侵犯群眾合法權(quán)益。”
此次全會《決定》在執(zhí)法方面重申各級政府必須“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這與習(xí)近平多次強調(diào)的“把權(quán)力關(guān)進制度的籠子里”可謂一脈相承。
2013年1月22日,習(xí)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要加強對權(quán)力運行的制約和監(jiān)督,把權(quán)力關(guān)進制度的籠子里”,并告誡各級領(lǐng)導(dǎo)干部“任何人都沒有法律之外的絕對權(quán)力”。
之后一個多月,習(xí)近平兩次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論述。
一次是在2013年2月23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xué)習(xí)時,他強調(diào)“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nèi)活動,”“各級領(lǐng)導(dǎo)干部要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各級組織部門要把能不能依法辦事、遵守法律作為考察識別干部的重要條件。”
另一次是幾天后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典禮上,他進一步說,“學(xué)習(x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guī),這是領(lǐng)導(dǎo)干部開展工作要做的基本準備,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養(yǎng)。不掌握這些,你根據(jù)什么制定決策、解決問題呀?就很可能會在工作中出這樣那樣的毛病。”
四中全會的另一個亮點,被認為是提出“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zé)任追究制度及責(zé)任倒查機制”,并“把法治建設(shè)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lǐng)導(dǎo)班子和領(lǐng)導(dǎo)干部工作實績重要內(nèi)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
分析人士指出,這可謂是將習(xí)近平之前提出的“把能不能依法辦事、遵守法律作為考察識別干部的重要條件”落到了實處。
禮法合治
在司法方面,習(xí)近平此前很多論述在《決定》中也得以體現(xiàn)。
比如,《決定》中提到的“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就曾出現(xiàn)在習(xí)近平在紀念現(xiàn)行憲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
他當時說,“要依法公正對待人民群眾的訴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決不能讓不公正的審判傷害人民群眾感情,損害人民群眾權(quán)益。”
事實上,早在2013年初的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xué)習(xí)時,習(xí)近平就有過類似的論述。
當時,他還要求“所有司法機關(guān)都要緊緊圍繞這個目標來改進工作”,“確保審判機關(guān)、檢察機關(guān)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quán)、檢察權(quán)”。
從已發(fā)布的《決定》看,此次全會在司法改革方面的舉措主要分兩大方面,一是司法體制的改革,如最高人民法院設(shè)立巡回法庭,探索設(shè)立跨行政區(qū)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另一方面則提出如何加強權(quán)力監(jiān)督,預(yù)防“一把手”干預(yù)司法,這包括建立領(lǐng)導(dǎo)干部干預(yù)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zé)任追究制度等。
四中全會提出設(shè)立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跨行政區(qū)劃的法院和檢察院、公益訴訟制度等,被認為是解決司法地方化的治本做法。
中國政法大學(xué)副校長馬懷德認為,中國目前的司法轄區(qū)與行政轄區(qū)相對應(yīng),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地方保護主義對司法公正形成干擾。“比如,一起涉及兩個省份的糾紛,無論在哪個省份的法院審理,當事人都可能感覺得不到公正處理,但如果設(shè)立諸如華東法院、華北法院等,一些跨域區(qū)案件就能得到比較公正的審理。”
而對于全會提出防止領(lǐng)導(dǎo)干部干預(yù)司法的多項機制,中國人民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朱景文分析,這是明顯的信號,表示執(zhí)政黨要求官員要把法律當回事。

事實上,習(xí)近平對此也有過不止一次的論述。
尤其是在2014年1月7日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他明確提出“要正確處理堅持黨的領(lǐng)導(dǎo)和確保司法機關(guān)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quán)的關(guān)系”。
也正是在那次會上,習(xí)近平對領(lǐng)導(dǎo)干部干預(yù)司法的現(xiàn)象,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一些黨政領(lǐng)導(dǎo)干部出于個人利益,打招呼、批條子、遞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預(yù)個案,甚至讓執(zhí)法司法機關(guān)做違反法定職責(zé)的事。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另外,公報還提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jié)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fā)。”在構(gòu)建法治的同時,也不忘德治傳統(tǒng)。這與習(xí)近平重視發(fā)揮傳統(tǒng)文化的積極作用也非常吻合。
在不久前的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xué)習(xí)時,習(xí)近平強調(diào)了“禮法合治,德主刑輔”這一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精髓要旨,提出法治和德治的統(tǒng)一。
他說,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fā)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中國的今天是從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發(fā)展而來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tǒng)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jié)。
有學(xué)者指出,在傳統(tǒng)社會,儒家的道德教化為國家的秩序良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構(gòu)建法治社會,離不開人們的道德自我約束,一個道德敗壞的國家,也不可能是一個良好的法治國家。
《決定》提出,“發(fā)揮市民公約、鄉(xiāng)規(guī)民約、行業(yè)規(guī)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guī)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就是從傳統(tǒng)的德治角度出發(fā),倡導(dǎo)自我約束的道德自律。
黨的領(lǐng)導(dǎo)
在《決定》中,“黨的領(lǐng)導(dǎo)”是出現(xiàn)頻次最高的詞語之一。
《決定》明確“黨的領(lǐng)導(dǎo)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zhì)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的同時,也用了很大的篇幅,指向?qū)?zhí)政黨的自我約束,強調(diào)“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工作的領(lǐng)導(dǎo)”。
關(guān)于黨的領(lǐng)導(dǎo)與法治的關(guān)系,習(xí)近平之前也有過很多表述,尤其是今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他作了大段論述。
他說,“我們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黨的政策是國家法律的先導(dǎo)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據(jù)和執(zhí)法司法的重要指導(dǎo)”,“要正確處理堅持黨的領(lǐng)導(dǎo)和確保司法機關(guān)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quán)的關(guān)系”。
《決定》中,“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lǐng)導(dǎo)”被放在推進依法治國任務(wù)的最后一條。中國政法大學(xué)憲法學(xué)教授焦宏昌認為,將黨的領(lǐng)導(dǎo)放在最后意味著一切需要有黨的保障,沒有黨的保障不能實現(xiàn)前面所有目標。
眾所周知,此次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作為主要議題,在中共全會歷史上盡管尚屬首次,但距離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國已經(jīng)過去了17年。在此期間,歷次黨代會都會重申“依法治國,建設(sh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那么,十八屆四中全會的特殊意義究竟何在?
有評論指出,之前中共提出依法治國盡管有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如何把依法治國與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有機統(tǒng)一起來,一直缺乏明確的表述。多年來,中共也一直在探索如何把黨的領(lǐng)導(dǎo)與依憲治國、依法治國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建立起新的現(xiàn)代執(zhí)政方式。
而這次會議明確地把中共對國家的領(lǐng)導(dǎo)、治理與社會主義法治表述為同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堅持中共的領(lǐng)導(dǎo)“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法治是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具體體現(xiàn),堅持社會主義法治也是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
《決定》把中國共產(chǎn)黨界定為中國法治建設(shè)最重要的領(lǐng)導(dǎo)力量和最根本的保證,說明中共的領(lǐng)導(dǎo)力量是內(nèi)在地體現(xiàn)在中國的法治建設(shè)的進程之中,而不是跟法治建設(shè)平行并立的另一種力量。
有輿論認為,這次全會關(guān)于黨的領(lǐng)導(dǎo)與社會主義法治關(guān)系的表述,完成了中共過去三十多年甚至六十多年一脈相承的探索與創(chuàng)新,也標志著中共的執(zhí)政方式將進入一個實質(zhì)性和更加成熟的轉(zhuǎn)變階段。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十八屆四中全會具有里程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