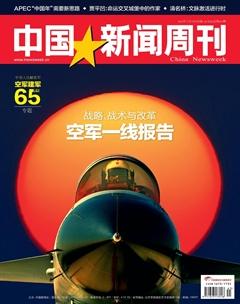中國空軍的藍天大考
張力 江菲

一張戰場態勢圖清晰記錄著對抗的全過程。
交戰從一開始就呈現“一邊倒”。“紅軍”將作戰力量偏重于右路部署,左路只留了4架戰機,在前沿的兩個空域巡邏待戰。
“藍軍”恰好把進攻方向放在左翼,數架遠程作戰飛機直撲而來,從畫面上看,“紅軍”一側已是大兵壓境。
然而,對抗結果公布,“藍軍”瞠目結舌:“紅軍”依靠早期預警信息,早已占據有利位置,作戰要素密切協同,將進攻的“敵”機悉數擊落。
“紅軍”獲勝!
在這場被命名為“體系對抗”的中國空軍最高規格的演習中,兩支空軍部隊全方位地感受著一場現代化的實兵對抗。
然而,倒退10年,中國空軍的演習卻完全是另一副面孔:對抗不宣布名次,攻防按預先套路進行,打得效果如何,雙方知之不深,有時也不太深究。
“當時演練的主要目的是驗證戰法。”空軍司令部軍訓部原副部長徐敏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就是研究出一套作戰方法,用演習來驗證一下。一方怎么打,另一方怎么防,事前已有限定,對抗的主要目的是驗證和完善。”
“改變一個循序漸進、逐步發展的過程。”徐敏杰說,“而且這種改變遠未結束。”
“和平積習”的反思
普通人很難想象空中戰斗的真實狀態。
轟鳴,超音速,一閃即過的“敵”機。不斷拉桿,壓桿,連續翻滾。承受幾倍的身體重力,天旋地轉中,抓住偶然閃現的四分之一秒,按下導彈發射按鈕。
“沒法描述它。”一位航空兵團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要相信電影中的空戰場面,那基本都是唬人的。”
“空戰的魅力只有你真的參與了,聞到那種氣味兒,處于那種氛圍,才能感受到它。”空軍航空兵某團副團長顏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是一種刺激,一種挑戰,你會不由自主地興奮起來,迫不及待想要把自己的思想與戰機合為一體。如果非要去形容,我只能想出一個字:爽。”
然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空軍飛行員對這種感覺是陌生的。
中國空軍規模一直位于世界前列,上世紀90年代初,中央軍委確立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后,更是開啟了中國空軍逐步換裝新型戰斗機、升級武器裝備的質變時代,逐步引進了蘇-27等第三代戰機。但是,戰斗力呢?
“沒有辦法檢驗。”徐敏杰坦率地說,“中國空軍幾十年沒打過仗,除了對抗演習和考核,缺少一個可以檢驗戰斗力的平臺。”
多年前,他曾到某航空兵團檢查對地突防突擊訓練。“就是四平八穩地起飛,到目標機場,轉兩圈,打個地靶,回來。我當時就說,這是打地靶訓練,不是突防突擊,不是戰術訓練。”
在另一個部隊檢查突擊地空導彈基地訓練時,他隨口問了一句:具體是什么型號的地空導彈?沒想到,現場的人幾乎答不出。“他們天天飛,都不知道突擊的是什么導彈,說明敵情研究不夠。”徐敏杰有些激動,“并不是說我們飛行員們技術不好。但要將技術轉化為戰斗力,還有漫長的過程。”
這種情況,被描述為:“一條航線兩個彈,天天圍著靶場轉。”遠離戰火淬煉的軍隊,有時會不自覺地會沾染上這種“和平積習”。
但是,越來越多的飛行員開始感到壓力。“沒有戰爭,我們一丁點經驗都沒有……沒有比拼,就沒有枕戈待旦的壓力,也就缺乏前進的動力,猶如井底之蛙看不到外面的世界。”60后飛行員孫洪喜回憶說,“某些戰術課題一飛就是好幾年,方法不變,套路不變,保姆式、家長式的指揮保障,讓本該具有很強自主性和創造性的空戰飛行,漸漸失去了活力和狼性。”
“作戰靠的是戰術素養,是飛行員感知和應對戰斗態勢的能力。”顏鋒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戰斗是一個復雜的、持續不斷的動態過程,在嫻熟的飛行技術基礎上,還要求飛行員有敏銳的洞察力、快速的判斷力、高水平的執行力、強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極好的協同配合能力。“想一想,那么快的速度,要盯著對方,自己要機動,要瞄準,要調雷達,要發射武器,身體還要承受很大壓力,這么復雜的狀況,反應時間也就幾秒鐘,平時訓練不夠,上去只會手忙腳亂。”
如何達到人機合一,在未來空戰中勝券在握?別無他法,只有在日常訓練中盡一切努力貼近實戰。
“未來戰場可能發生的,在演練場上都不算違規”
實戰化訓練轉型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持久性地激發部隊“想打贏、謀打贏”的斗志。
“其實沒有軍隊不想打贏。”空軍某基地團長于昌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但是,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一個平臺去證明自己。實力到底如何,自己心里也沒數。”
最現成的辦法,是將原本的驗證戰法演習,改造成近乎未來戰場的對抗平臺。
為了能夠逼近戰場實況,“紅藍體系對抗”的改革方案一改再改。最初,是將一個軍區空軍部隊一分為二,作為紅藍軍對抗演習。試驗一段時間后,發現了問題:同一個軍區,再怎樣對抗,感覺都有點“左手打右手”。演習雙方于是調整為一個軍區空軍部隊與一支空軍專業部隊對抗。這個方案有進步,但仍有差距。軍區空軍部隊“官兒大”,對手“放不開手腳”。左右權衡,最后的方案是,兩個軍區空軍對抗,“級別一般高”,公平競技,誰也不用有顧慮。
解決了部隊間對抗的心態問題后,下一步是如何讓“對抗”變為“真打”。
“用我們的話說,就是放開,放開突防高度,放開氣象條件,放開網絡攻防。”負責組織這一演練的某基地司令員李世福解釋說,對抗開始前,只通報雙方的駐地范圍和基本武器裝備,至于更具體的內容,比如對方的指揮部在哪里,使用什么樣的雷達,部署什么樣的導彈,都只能靠自己的本事去發現。
這個決心并不容易下。對于沾染過“和平積習”的部隊來說,從“套路”一下跨越到如此“自由”的實戰演習,需要強大的心理和戰術準備;對于空軍訓練部門來說,則需要有承擔風險的心理準備和責任感。此外,還需要加強空軍裝備體系建設,以便從硬件上確保演練取得實效。這一切的完成,經歷了四五個年頭。
為了解決對抗強度不夠的問題,軍訓部認為:還需要再加上一條,評成績、比輸贏、排名次、獎能手。
2009年,這一頗具實戰味的體系對抗規則一經推出,就讓基層部隊“炸了窩”。
“部隊指揮員感受到了特別大的壓力,誰都不愿意輸。”顏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所在的部隊剛好參加了這一年的體系對抗,為了能贏,白天黑夜地研究對手、完善方案,全部隊都進入了臨戰狀態。
但在李世福的印象中,這種變化只是表面的。更深層次的變化在于,由于限制了紅藍雙方的信息通報,雙方部隊開始了戰前情報偵察,以及互相保密的作戰規劃,由此帶來的作戰理念和精神狀態的變化,“意義深遠”。
不少部隊一時無法適應。一次,藍軍部隊通過技術手段,攻破了紅軍的指揮系統,搞到了對方的作戰計劃。紅軍連忙舉報說:“他們違規!”另一次,紅軍部隊超低空突防時,被藍軍舉報:“違規!他們的突防高度低于演習規定的最低突防高度!”還有一次,一方部隊偵察到對手的地面防空導彈位置,派機轟炸,到達時導彈卻已被機動走了。偷襲沒成功,他們不解地到處問:這樣算不算違規啊?
“只要是未來戰場可能發生的,在演練場上都不算違規。”徐敏杰回答。
幾年下來,空軍參演部隊終于明白:得玩兒真的。不玩兒真的,就真的會輸。
突防突擊:“仿真”考核
一架蘇-30戰機,以接近每小時1000公里的速度,貼著大漠疾行。它不時變換姿態,左彎右繞,波浪般隨著地勢上下漂移,但高度始終保持在“敵人”雷達探測的盲區。
機上雷達顯示,目標就在前方。甫一沖進目標區,它瞬間仰頭向上直躥2000米,之后倒轉機頭,蒼鷹捕食般俯沖下來。一枚炸彈從腹下沖出,直奔地面標靶。
這是中國空軍另一個實戰化訓練品牌——突防突擊考核。
很長一段時間,突防突擊是公眾關注的盲區,也是中國空軍需要提升的重要能力。
中國空軍僅有過兩次對地作戰的經驗。一次是抗美援朝時期轟炸大和島,另一次是1955年海陸空協同作戰攻占一江山島。
空軍指揮學院軍事專家王明志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奪取大和島戰斗雖然最終取勝了,但中國空軍派出9架戰斗機,被擊落5架,擊傷3架,十幾名飛行員犧牲,“總體上是不成功的”。
這次不成功的對地作戰經歷,以及后來國家整體戰略的調整,使中國空軍開始更多地關注防御。但一架戰斗機的用武之地,并不只在空中。空中作戰的本來目的,是“以空制地”————轟炸地面目標。“制空永遠要服務于制地。”徐敏杰總結,“因為人生活在地上,而不是在空中。”
在中國空軍戰略轉型的過程中,全面提升其戰略打擊能力,成為一個緊迫問題。突防突擊實競賽性考核,應運而生。
2009年,第一次施行,考核規則幾近苛刻。
第一,考核地點一律在陌生靶場——徐敏杰戲稱為“敵占區”,參加考核的部隊必須全建制參加。部隊接到命令后,從所在機場遠距離奔襲執行任務。
第二,沿途將布防雷達組網探測,如果戰機被地面雷達截獲,便視為“突防失敗”而淘汰。
第三,沿途將布設地空導彈模擬攻擊,不間斷進行電子干擾,最終只允許有一次進攻機會。
第四,每種彈型評出一名“突防突擊能手”,分高者得。
飛行員所能夠利用的,只有三樣工具:目標坐標、大比例尺航空地圖一張以及目標所在地衛星照片。
“的確很難。一邊要隱蔽,一邊要尋找目標,還要一次性完成攻擊。”但徐敏杰最擔心的,不是完成一次性進攻的成功率,而是發現不了目標。在不允許使用衛星導航設備以及地面布設強電子干擾的情況下,找不到目標是很有可能的。
或許正是嚴苛的考核條件,逼出了部隊的潛能。第一年考核下來,突防成功率和首次突擊成功率,都超過了50%。
“對地突防突擊考核看起來對抗性不強,但難度很大,對部隊的影響也不小。”多次參加這項考核的空軍司令部軍訓部副部長于和杰說,“部隊整建制參加考核,戰友之間、部隊之間都有比較,尤其是還沒到靶場就被發現的,零分。誰愿意得零分呢?下了飛機都不敢和別人說話,覺得丟人。”


為了“不丟人”,有部隊與友鄰地導、雷達部隊合成訓練,在實兵對抗中,專項研究突防技術;還有部隊為了研究突擊目標,把航空偵察照片貼在墻上,在地圖上一毫米一毫米地測量計算;還有的部隊為增強自主發現目標的能力,專門向環境構設部隊學習抗干擾戰法。
“金頭盔”比武,空軍訓練史上的里程碑
在中國空軍向實戰化訓練轉型的改革中,關鍵的一步,來自2011年開始的“自由空戰”比武。由于它的最高獎品是一頂金色頭盔,也被稱為“金頭盔”比武。
“這其中的邏輯是一環扣一環的。”徐敏杰說,“研究未來信息化空戰,我們發現必須提升體系作戰能力,又必須以提高對地打擊能力和制空能力為基礎,于是開始了突防突擊考核,和自由空戰考核。”
也有人提出,現代空戰中,貼身“肉搏”已經過時,時髦的是超視距空戰。雙方在肉眼看不到時已經“干掉”對方或被“干掉了”。近距離空戰的訓練,意義不大。
作為“自由空戰”考核的早期發起人之一,徐敏杰不這樣認為。“超視距空戰面臨很多難題。第一,你能攻擊我,我也能攻擊你,為了不被攻擊,雙方都會實施規避;第二,雙方都會實施電子干擾,很可能誰也看不見誰;第三,相距幾十公里,識別對方是敵軍是友軍,非常困難,因此不能貿然開戰。”
勢均力敵時,超視距空戰的成功率不高,勢必會越打越近,最終轉化為近距離空戰。
加強自由空戰訓練的更直接觸動,來自感性體驗。
“在聯合軍演或對外交流中,看到外軍一些尖子飛行員的表現,嫻熟的動作、面對風險的從容,以及飛行過程中表現出的自信,令人敬佩。”多次參與國際交流的飛行員王樂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而最能反映一個飛行員個人實力的,就是自由空戰。”
但當要在空戰訓練中給予飛行員更大“自由”時,遇到了難題——安全。
戰斗機在空中速度極快,為避免相撞,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空軍沿用相對保守的訓練方式:甲機和乙機在空戰對抗中,強調保持一定的高度差。
如何既能有“自由”又不失安全,2010年,空軍軍訓部選擇一個單位先行試點。
事情發生了奇妙的變化。原來怕相撞,認為取消高度差將極為危險,可一旦下定決心研究解決,發現辦法其實很多。比如:近距離接近時保持高度差,一旦有一方報告目視發現,便可立即取消高度差,由飛行員自行決定戰術;沒有高度差的迎頭飛行,到了必須各自轉彎規避的時機,可自行實施規避……
大半年后,基本規則確立。空軍各部隊派出至少4名代表,參加骨干培訓,之后回到本部隊傳幫帶。
之后,徐敏杰主持,成立一個研討小組,更具體地研究嚴密的交戰規則、協同規則和安全規則。四個月后,一套系統的對抗空戰考核方案出臺。
徐敏杰帶著方案到每一個部隊去征求意見。“是征求意見,也是溝通和推廣。”他說,“取消高度差的空戰對抗是個質變,這樣做就是告訴大家,我們下定了決心。”
為了更好地激勵先進、鞭策后進,在時任空軍司令部軍訓部部長亢衛民的提議下,“金頭盔”成為“自由空戰”考核的最高獎項。
2011年10月,第一屆“金頭盔”比武開戰,12支部隊的108名殲擊機飛行員,成為空中“自由搏擊”的第一批先行者。
沒人想到,戰況是顛覆性的。一支曾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創造過輝煌戰績、最早裝備新型戰機的部隊,輸給了一支名不見經傳的部隊,而且是大比分落后。
對抗一打響,評委們就發現,該部隊的戰斗機“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該部隊飛行員許利強回憶,一上天,耳機便不斷傳來“敵跟蹤”“敵告警”的雷達警告,自己奮力采取機動措施,仍然無法扭轉被動態勢。
原來,比武前的準備階段,對手部隊就請來電子對抗專家,對如何使用電子干擾做了專項研究。“電子干擾的使用有許多技巧。”空軍電抗專家劉璘解釋說,干擾對方的同時,自己也會受到對手的干擾,因此需要非常細致地控制干擾的時間,并學會與武器使用相互配合。
“被電子干擾的飛行員,在雷達屏顯上看到的只是一片雪花,不只發射不了導彈,連目標也看不到,和瞎子沒兩樣。”他說,“但也不是一點兒辦法沒有。比如立刻機動,采取臺階式、曲線式飛行,就可能突破干擾。這些都需要下功夫訓練。”
顯然,“王牌”部隊沒有下夠他們的功夫。第一個比武日結束,他們以59:166的大比分敗北,所有選手首輪被淘汰。許利強后來回憶,那一天晚上,大家難過得連飯都不想吃,被首長硬逼著去吃了飯,有人在飯桌上就哭了起來。“現在回想當時的場景,真是又悲又傷。”他說,“那一刻,真正體會到了戰敗是軍人的最大恥辱。”
更深刻的顛覆,發生在飛行員的內心。
一位飛行員用“后怕之后的竊喜”形容他的感受,“后怕的是我們曾那樣自我感覺良好;竊喜的是終于看到了差距,找到了實實在在提高部隊戰斗力的敲門磚……”
另一位飛行員則認為:“沒有打過‘金頭盔,你的戰術思想只是你們單位的戰術思想,打過后,就成為自己與對手戰術思想的融合。”
飛行員們的反饋震動了空軍司令部。一位空軍領導指出:這次空戰考核,在空軍訓練史上有著里程碑意義。
自我否定中,探求制勝之道
時間到了2014年6月。顏鋒率領所在部隊再次參加“突防突擊”考核。為了便于普及推廣,這項考核在今年被正式將命名為“金飛鏢”比武。
顏鋒充滿信心。盡管這是近年來最富挑戰的一次突防突擊考核。
放開突防高度、導彈全程攔截等,這些都還在他意料之中。最讓他撓頭的是靶標本身。他需要擊中的,是一輛吉普車——不是空曠場地中孤零零的一輛吉普車,而是在一個靶場內的眾多吉普車模型中指定的那一輛。“從兩三千米的高空看,就是個小黑點兒。”
事實上,這最初就是他的主意。“大目標,大家都能打中,有什么意思?要比試就打最難的。”他極力建議,最后竟然被采納了。
他渴望這次挑戰,帶著部隊,仔細準備了一個多月,對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都做了研究。比如,為了鍛煉陌生環境的目標搜索能力,專門在野外放置小型靶標,出機搜索;為了練習小靶標的瞄準射擊能力,制作了許多同樣大小的靶標,反復練習;為了對考核靶場的自然環境有所適應,他們還專門長距離奔襲,到靶場附近的機場轉場訓練。
但他沒想到,考核那天,靶場刮起了一陣大側風。若是大一點兒的目標,風對實彈飛行曲線的影響還可忽略不計,偏偏目標是輛吉普車。
“我沒打中。”顏鋒紅著臉笑,勉強說出了他的分數:3分。“我帶隊,第一個就沒打好。幸虧我們團長收尾的一彈打中了,不然可就全軍覆沒了。”
但他很快趕走了遺憾的情緒。“我還是覺得這樣是對的。每個靶都能打中,容易自我感覺良好,反倒不能保持清醒。”
這恰好是空軍打造三大演訓品牌——體系對抗、突防突擊、自由空戰——的目標:不是為了顯示肌肉,而是為了找到與未來戰爭的差距,激發部隊刻苦訓練的動力。
率先找到這種動力的,是那支鎩羽而歸的王牌勁旅。
第一屆“金頭盔”比武失利后,該部隊開展了幾個月的反思檢討,嚴抓實戰化訓練,即使輪訓期間也不忘搞空戰對抗。許利強回憶說,他和戰友們沒有休過一個完整的雙休日,高強度大過載的飛行,讓飛行員們的腿上留下許多“血點”。落地后,大家對著飛參,一個個摳細節找問題,再帶著問題去飛行驗證,“連做夢都在背數據”。
2012年“金頭盔”再戰,該部隊奪取第一個團體冠軍;2013年,該部隊三個團全部參加,獲得三個團體冠軍。迄今為止,這支部隊成為“金頭盔”比武的最大贏家之一。
考核比武還激起了二代機部隊的斗志。
三代機列裝中國空軍后,不少人認為,二代機終將淘汰,不需要再刻苦訓練了。老機團和新機團同時參加會議,老機飛行員都會“自覺地”坐在后面,完全沒有新機飛行員的昂揚氣場。在最初的考核比武中,二代機部隊也往往只能墊底。
但沈陽軍區空軍有一支二代機部隊,卻為此展開了全團討論:老舊戰機在現代戰場真的沒有作為嗎?
“戰爭隨時可能打響,對手可不會等我們有了新裝備才發起進攻。”“打敗對手的辦法有很多,只要找對敵人的破綻,同樣能打勝仗……”討論結果是:一支部隊無法選擇裝備,但應盡一切努力,將裝備性能發揮到極致。
就在今年的“突擊吉普車”考核中,這支部隊派出8架飛機,長途奔襲,全部突防成功;地面攻擊,首枚即中,彈無虛發,一舉奪魁。
大家的確都開始“動真格”了。新的戰術打法,更有針對性的武器使用技巧,以及此前沒有被發現的戰術技術,頻頻出現。
最有趣的“動真格的”,出現在體系對抗的情報偵察階段。為了搞到對方的情報,照相偵察,電子偵察,網絡偵察,能用的招兒幾乎都用上了。
當然也必須有反偵察。“部隊入駐前,先派人全面檢查駐地房間,看有沒有攝像頭竊聽器,檢查各種線路是否被破壞,能想多細就做多細。”顏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只要召開作戰會議,門口必派人站崗,閑雜人等,一律不得進入。”
他需要擊中的,是一輛吉普車。“從兩三千米的高空看,就是個小黑點兒。”
一次,他們無意間發現了兩個形跡可疑的人,穿著同樣的演習服裝,總是打聽東打聽西,感到蹊蹺。各兵種之間互相詢問:這是你們部隊的嗎?問了一圈,沒人認識。
“嘿,抓起來!”他們恍然大悟,“是間諜。”
“戰爭使人變得聰明,貼近實戰的訓練同樣使人變得智慧,而且能孕育一種軍人特有的尚武精神。”徐敏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沒人能夠預測未來戰爭的具體模樣,但我們可以在‘科學求實練為戰的理念下,通過常態化、實戰化的訓練和考核,不斷發現和彌補自身在理念、組訓、指揮、保障以及裝備上的不足,從而找到一條立足現有條件的勝戰之道。”
對中國空軍來說,這個危機與希望并存的時代,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