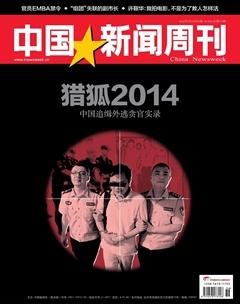官員EMBA禁令
韓永

中國的反腐,在“打虎”捷報頻傳的同時,正在指向一些腐敗易發的平臺。多年來在中國高舉高打的EMBA,成為整治的新目標。
7月31日,中共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中組部、教育部聯合下發通知,嚴禁領導干部參加高收費的培訓項目,和各類名為學習提高、實為交友聯誼的培訓項目,已參加的要立即退出。
在另一份配套的文件里,這些被要求與領導干部“隔離”的培訓項目,又被明確列舉如下:EMBA、后EMBA以及各種打著政商聯誼、交友、游學等名義的總裁培訓班、高級領導人員研討會、研修班等。“EMBA、后EMBA、總裁班、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長江商學院等,明確屬于高收費社會化培訓項目。”
官員的比例
在上述通知中,與EMBA有關的評價有兩個:一個是“高收費”,另一個是“名為學習提高、實為交友聯誼”。后者雖沒有直接用來形容EMBA,但用在了與其基因相似的總裁班身上,等量齊觀的意味甚濃。分析人士認為,正是這兩個特點,讓EMBA與官員的身份格格不入。
按說,無論從其課程的設置還是收費標準,EMBA都很難與官員扯上關系。EMBA的全稱是“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翻譯成中文是“高級管理人員”,其中的“business”已經設定了其服務對象,即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而從課程設置看,EMBA講的也主要是一個企業的事情,即如何更好地管理和經營企業。對官員來說,即便從宏觀經濟管理的角度考慮,這些課程也很少能派上實際用場。
另外,EMBA的高昂收費,對官員也是一筆難以承受的負擔。目前,在國內排名靠前的EMBA的學費,都在50萬元以上。按一個北京處級官員的收入標準,這筆學費需要耗費其5年左右的全部收入。
但官員在各個學校EMBA中的存在,又是一個現實。要了解這一點并不難,因為基于招生的考慮,各個學校都傾向于選擇將這一信息廣而告之。據《中國新聞周刊》統計,官員在EMBA學員中所占的比例,平均約為5%~10%,但各校之間相差很大。其中,以官員資源見長的中國人民大學,有一年公布的比例竟然高達26.3%。另外,北大光華為12%,長江商學院11%,上海交大安泰學院為4%。而在廈門大學公布的20位EMBA優秀校友中,政府官員占了4位,占比20%。
若將官員的這一比例,與EMBA之中的國有企業高管所占的比例相加,就是一個更為可觀的數字。公開的材料顯示,國有企業高管在EMBA學員中所占的比例,比官員在其中的比例高很多,通常在30%左右。其中中歐商學院為三分之一,北大光華為30%,人大為34%,上海交大為29%。在上述中組部等三部門下達的通知中,國有企業也在EMBA禁讀之列。
上述兩個比例加起來,“國字號”學員在有的學校已占據EMBA學員的50%左右。清華大學一位EMBA研究者認為,雖然很多學校竭力淡化上述通知對招生的影響,但一半左右的學員在禁讀之列,其對招生的影響已不言自明。
“圈子文化”
這些以自身收入難敷學費的官員,學費的問題如何解決?一位曾在國內排名靠前的EMBA項目從事過招生工作的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官員的學費支付主要有三個渠道:一是官員所在的單位報銷;二是有人代付;三是學校減免。“這三者中,前兩者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學校為其減免學費。”
學校此舉的目的何在?這位前EMBA招生人員說,官員,尤其是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員,對于EMBA來說猶如至寶,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可以介紹生源;二是可以吸引生源。這兩者,都是基于官員對企業家的巨大影響力,只不過前者是基于過去的關系,后者則是基于未來的關系。
官員在EMBA中的巨大作用,與在其中廣泛存在的“圈子文化”有關。
自1995年進入中國以來,這個在國外旨在培養商科思維的培訓體系,在繼承重“商”傳統的同時,也在不斷適應中國的人文環境。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中國的每個EMBA項目,都無一例外地表現出對學員之間資源共享的重視。上文提到的清華大學EMBA研究者說,每個學校都會在宣傳中提及自己遍布全國的校友會,并重點提及其中的重量級人物,除了昭示自己的吸引力外,也是對資源共享的某種暗示。
上述前EMBA招生人員說,這些在各行各業事業有成的學員,他們對EMBA的覬覦,除了專業上的指導外,還有這個平臺上的大量優質資源。這些資源包括能提供上下游合作的生意伙伴,也包括手握資源分配權的官員。
浙江省一位私企老板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EMBA平臺上積累下來的資源,由于有兩年的情感積累,又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在共享資源時信任感更強,成本更低,風險也更小。“對商商之間的合作是這樣,對官商之間的合作也是這樣。”
北京市一位處級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相對黨校等體制內的培訓,比如EMBA對于官員的好處,除了在專業上更能開闊視野外,也有利于其選擇一個商業上的合作對象。
這樣,官員的參與,就有可能形成一種“三贏”的格局:商人收獲官場資源,官員收獲合作對象,而EMBA主辦方則坐收生源充盈的漁利。
“更少數的一群人”
在這次事件之前,EMBA在中國經歷了“黃金十二年”。
2002年,中國30所院校正式獲得EMBA辦學資質。此后,EMBA在中國的行情年年見漲:2002年秋季班,國內幾大排名靠前的EMBA的收費,基本上都在20萬元左右,收費最高的長江商學院和清華經管學院,也只有25萬元,中歐和北大光華都在20萬元以下。到了2012年秋季班,這幾個EMBA項目的收費,全都超過了50萬元。其中長江商學院漲幅最大,達到了65.8萬元,是十年前的2.6倍。
有人根據其收費標準和上課時間,算出了EMBA每分鐘的含金量:EMBA學制兩年,通常每月上課4天,去除節假日,兩年上課80天左右,按每天上課8小時計算,長江商學院2012級EMBA每分鐘收費17元左右,每小時1000多元,每天8000多元。
但中國EMBA報名人數與學費增長之間的關系,呈現出與很多國家不太一樣的趨勢:在EMBA市場相對成熟的西方國家,學費的高低與報名的需求之間,通常會呈現一種反向的關系:學費的上漲,通常會抑制報名的需求;而在中國,EMBA報名的需求與學費之間,卻呈現出一種同步上揚的趨勢——在過去的十年里,EMBA的學費上漲了兩至三倍,而其報名人數的增加,也不少于這個幅度。
這一趨勢,在2009年體現得最為充分:這一年,金融危機陰云密布,EMBA學費卻逆勢上揚,長江商學院的上漲比例高達35%,而報名的需求竟然不降反升,一些排名靠前的EMBA項目,報名的增長率均超過了50%。
浙江省上述私企老板在報名EMBA之前,曾經研究過各個學校EMBA學員的構成。他發現收費30萬元和收費50萬元的EMBA,在學員的構成上有明顯的區別:除了經濟實力外,后一類學員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上的共同性,都比前一類更多,相互之間的認同度也更高,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更大。
上文提到的前EMBA招生人員,還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了一個秘密:這些“不差錢”的學員,有時甚至希望通過提高學費的辦法,提高這一項目準入的門檻,從而讓自己成為“更少數的一群人”。這在業內有個說法,叫做“用高價購買純度”。
如今,EMBA出現在一個具有反腐性質的中央文件里,讓業內人士多少感覺到一些“負面評價”的意味。前述EMBA項目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對EMBA項目來說,這一舉措至少會產生兩個后果:一是來自官員和國有企業的生源會大幅減少,二是前幾年讓人目不暇接的漲價行為,在今后幾年可能風光難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