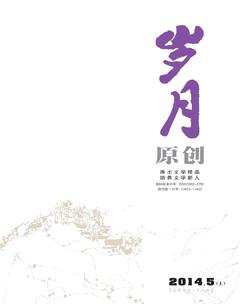遠離喧囂浮華
星芽
縱觀中國詩壇幾十年的詩歌進程,由20世紀初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寫作,并創作新詩為誕生標志和起步階段,隨后出現的“七月詩群”、“新月派”、“朦朧派”、“學院派”、“民間派”和“新生代”等詩歌創作群體,以及科技進步和網絡開發,都加大了詩歌傳播的力度和廣度,促成它的多元化發展趨向。這也是中國詩歌的群體性喧囂。盡管這場文化盛宴從表象上看是熱鬧紛呈的,和西方幾千年的根基相比,中國短短幾十年的詩歌歷程往往存在泥沙俱下的現象。而詩歌的邊緣化已成定局,不少詩人因此提倡詩歌回歸大眾,打著口語的詩歌理念,力圖展現人們的生活狀態,異于“學院派”精雕細琢,關注生存狀態的詩風。因此,詩人的“圈子化”,自我炒作,自我娛樂等與詩學精神相背離的現象一一萌發。在當下這個科技網絡和娛樂媒體興盛的時代,詩歌理應要有最起碼的社會良知,獨立的思想,避免盲從跟風以限制自我思維的開敞。因此,我總將詩歌看做一種遠離喧囂的個體存在方式,過度地“圈子化”,不僅會養成片面的眼光,局限寫作的自由,還容易引發因流派觀念不同卻同樣是詩歌擁護者的紛爭,造成詩壇的喧嘩(例如1999年的“盤峰詩會”)。遠離喧囂,不僅指外界環境的喧囂,也指人類個體思維和心境的喧囂。梭羅幽居瓦爾登湖畔,是為了追求“人的完整性”,荷爾德林將不可知的神作為詩人的尺度,而海德格爾則認為“做詩乃是原始的讓棲居”,這些都是他們選擇的存在方式以及具有原創性的獨立思考。每次寫詩時,我都將思維看作身體里一種愛好旅行的生物,借助它們的眼睛,便可以橫渡我雙腿無法抵達的地域。這是處于群體喧囂中不可抵達的藝術體驗,而詩歌,作為人類生命表達的形式之一,盡管它沒有必然的使命要求,而它自身的美學和知識力量,總能在社會各個階層達到熏陶和潛移默化的引領作用。它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用以解構主義等先鋒性創造思想,改變現有的思維模式和閱讀習慣。它是激發生命的力量,是一種存在方式,遠離了浮華喧囂,也能使“孤獨在意志中閃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