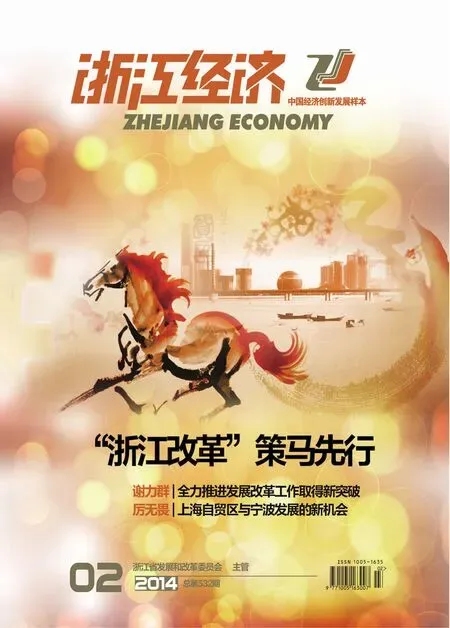從“基礎性”到“決定性”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蘭建平
作者為浙江省經信委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一)
當前國家之間的競爭,已經不僅僅體現在技術競爭、產品競爭、企業競爭等領域的經濟競爭,更是體現在政黨治理國家的模式和能力上的競爭。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采用什么樣的經濟管理方式來促進國家和地區經濟的持續發展,是這種競爭的重要體現。
回顧我國經濟發展的管理方式,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計劃經濟、轉軌經濟、市場經濟。
第一階段:新中國成立以來到1978年,是典型的計劃經濟管理方式,是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在中國的典型復制。這一體制對于生產力水平較低、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的新中國重構國家經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階段:1978年到2013年,順應經濟全球化、一體化浪潮,開始走改革開放發展之路,開始從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并逐步由計劃經濟配置資源為主導向市場經濟配置資源轉變的國家經濟管理方式。在1992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我國第一次提出了“市場經濟對社會資源起基礎性配置作用”,可以說是我黨和我國執政理念的一次重大理論創新,標志著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可以運用市場機制來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沒有這一理論創新,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
第三階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充分發揮市場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這是我們黨和國家在新時期執政理念的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體現了我們黨和國家在新的時期,認識市場經濟規律、尊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把握并順應客觀規律的科學執政理念和做法。要素資源配置的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意味著我國將借鑒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崛起、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崛起的經驗,在制度創新上,更加注重發揮“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解決發展型政府的“有形之手”的“越位”問題。
從近些年的發展來看,我國一些本應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領域,如股市、房市、債市等,其管理方式體現為直接的政府計劃管控,沿用了計劃經濟做法。盡管階段性地看,這樣的管控,對刺激經濟發展、實現穩增長、保增長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客觀上也較大地扭曲了市場的價格信號,改變了供求關系,掩蓋了市場的真實情況。表現在調控結果上,價格失真,偏離價值規律,政府調控成為“空調”,社會資源錯配而造成浪費。如房地產,越調價格越高;光伏產業,越補助,產業發展越非理性。市場“決定性”作用的提出將極大地促進資源錯配問題的解決,提高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分析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世界各國圍繞市場配置資源與政府配置資源問題上,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市場主導的自由經濟階段,如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政府與市場并舉經濟階段,如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新自由經濟階段,如歐元區經濟體的誕生,WTO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強勢政府干預經濟發展階段,如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日本、韓國等經濟體的刺激政策,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等。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歷史看,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發展水平,政府干預的程度有所差異,但透過現象看本質,以及根據發展趨勢判斷,市場的力量都是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配置資源的主導力量,這是由于市場經濟的本質所決定的,也是一個被實踐證明了的客觀規律。但是,市場經濟也會偶有失靈,如在提供公共產品和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等方面,這就為實行政府干預提供了“切入口”。正如一個硬幣具有兩面,適度的干預是需要的,但干預往往容易過度,特別是在經濟出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以政府配置資源為主的各種宏觀調控,會成為經濟發展方式政治化趨勢追求的重要表現。
從最近5-10年來看,最為典型的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應對危機采用了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政策,通過大量投放貨幣啟動經濟,直接導致全球性資產泡沫,以美元為世界貨幣的全球經濟,也因此埋下了經濟理性復蘇隱患。日本經濟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安倍經濟學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超發貨幣。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也存在較為嚴重的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貨幣超發的問題也是比較突出的,2012年,公開媒體報道我國M2/GDP的比值已達到2倍。這些通過開動印鈔機來刺激經濟的做法,已經成為被打開的“潘多拉魔盒”。市場“決定性”作用的提出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將極大地促進我國各級政府過度干預問題的解決,促使政府更好地發揮規范和服務職能。
總結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發展的路徑,雖然在市場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從一個面臨生存壓力的國家到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風景這邊獨好,成就令人矚目,但客觀上講,我國目前只是一種“半市場、半計劃;半封閉、半開放”的經濟體制,按照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認為我國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是有一定道理的。借鑒國外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要實現十八大提出的“中國夢”,解決“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只有讓市場來配置資源,讓市場來起決定性作用,才能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加快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才能為實現中國百年崛起奠定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制度基礎。
所謂的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在路徑和方式表現為經濟發展各種要素的配置,要實現“全覆蓋”和“全過程”地由市場來配置,讓產品或勞務的價格由市場來定價,讓經濟社會各項事務由市場來決策。這種配置權、定價權、決策權,讓市場說了算,而不是行政命令、行政長官說了算。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應該是一種消費者和生產者綜合定價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是市場起決定作用最根本的表現。當然,必須指出,在推進的時序上,作為轉軌經濟,不可能一兩年、一兩個文件,市場的這種決定性作用就體現出來了,至少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真正實現這種市場的決定性資源配置作用。在區域的發展上,由于發展環境、發展基礎、發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異,市場的這種決定性發揮的程度,也是不一樣,不可能是全國“一刀切”、一個調、大家一起走,都讓市場來起決定作用。在行業上,由于要素本身特性的差異性,有的市場配置作用很容易實現,有的需要先做些調整,才能適合由讓市場來配置。
(二)
三中全會關于市場機制起決定性配置作用的理論創新,在實踐上也將起到十分明顯的作用。從當前來看,至少在這五個方面會起到十分明顯的政策效用:
一是大大提高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預期,提振市場的信心。實際上,對一個已經進入中等發達階段的國家、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既無必要、也無可能由政府為主導來實現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
二是有效地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讓有限的要素資源得到最有效的使用。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在工業化進程中,資源的有限性、稀缺性會成為制約經濟翻番的主要因素。資源市場經濟的動力機制,就在于資本本身具有逐利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過十分精辟的論述。如何通過市場機制,讓社會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讓資本流得更快、更暢,是經濟活力釋放的重要途徑。浙江之所以能夠從資源小省邁向經濟大省、基本溫飽走向總體小康,和當年改革開放的制度創新有很大的關系,關鍵是從“計劃”到“市場”的改革,市場化讓浙江“一遇陽光就燦爛、一遇雨露就發芽”,到處是“希望的田野”。

圖/金川
三是促進企業提高自身競爭力,實現市場主體的轉型升級。企業雖然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但如果政府掌握大量的高端資源,企業為獲得超額利潤甚至合理利潤需要去積極爭取這些資源的話,企業不會有動力去創新,去自我革命。這樣的制度安排,造成企業家將主要的精力轉向去努力“找市長(司長)”,而不是“找市場”。所謂“商海橫流方現英雄本色”,只有通過市場的充分競爭,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才能促進企業練就出色的“硬功夫”,才能打造“百年老店”。
四是有利于消除腐敗、減少權利尋租,改善經濟發展的社會生態環境。權利尋租、甚至是過度尋租,是政府配置資源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腐敗不僅僅是要教育干部“不要貪”,更要制度上讓干部“不能貪”,這才是最根本的。當前,部分干部犯錯誤,相當程度上是權利尋租太容易所致。
五是倒逼政府更好地提高宏觀調控的能力,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政府不直接配置社會資源,政府的權利就會“減少”。但是,新時期、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出來,該如何解決?迫切要求黨委、政府提高自身宏觀調控能力,否則,由于“本領恐慌”而會不被社會所認同,這對執政黨來說是一種倒逼機制。
浙江是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也是市場對資源能夠起決定性配置作用條件最成熟的省份,浙江要緊緊抓住全面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有利機會,謀劃各種能夠讓市場起決定性配置資源作用的領域和方式。如爭取浙江成為“國家市場化配置資源改革試點省”,成為浙江新的地方國家戰略;按照“一級宏觀調控、二級宏觀管理”的思路,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推動國家產業政策轉變,由中央政府的“事前審批”轉為“事后監管”,發揮地方政府更了解、更接近、更掌握地方企業實際情況的優勢,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最佳的服務;借鑒上海設立自貿區(實體試驗區)的改革路徑,爭取浙江成為“國家電子商務自由貿易區(虛擬試驗區)”改革路徑,為浙江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努力通過體制、機制上的不斷創新,為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更加強勁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