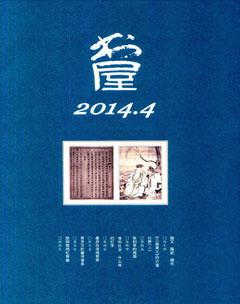張伯苓的周圍
張曉唯
天津南開系列學(xué)校(大、中、小學(xué))的創(chuàng)辦,主要得益于嚴(yán)修(字范孫)的聲望、人脈和實力,校長張伯苓起到了重要的輔助作用。南開元老黃鈺生直言:嚴(yán)、張二人的關(guān)系“一為東家,一為西席”,即是說,張最初乃嚴(yán)氏聘請的家庭教師。當(dāng)南開的事業(yè)越做越大,嚴(yán)、張間的合作共事就具有了不可分離的伙伴效應(yīng)。及至南開學(xué)校校慶四十年時,重慶《大公報》社評稱:南開乃張校長所一手締造,距史實已遠(yuǎn)。實則,張伯苓本人早在1931年校慶二十七周年之際,即就此作過十分恰切的表述:本校創(chuàng)辦人是嚴(yán)范孫先生,承辦人是我。他強(qiáng)調(diào)說,南開前期靠嚴(yán)先生,“他的偉大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所謂前期,應(yīng)是嚴(yán)修在世的1929年以前。后期呢?1948年張伯苓在浙江大學(xué)介紹南開辦學(xué)經(jīng)驗,稱南開“后期靠基督教”。聽者不免感覺突兀,不明所以,然究其所言,似指美國教會勢力的資助。美國“洛克菲洛基金會”曾一再提供資金贊助南開,張本人早年加入教籍,其榮獲的兩個名譽(yù)博士學(xué)位均得自有美國圣公會背景的上海圣約翰大學(xué)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xué)。不過張氏這一說辭,似在謙遜回避他個人的辦學(xué)業(yè)績,事實上,嚴(yán)修故去后的二十年間,承辦人張伯苓將南開推向了事業(yè)的峰巔。
一
嚴(yán)修在世的最后幾年,張伯苓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很強(qiáng)的辦事能力,贏得社會的認(rèn)可和尊重:大總統(tǒng)黎元洪曾以教育總長一職相許;少帥張學(xué)良則視其為良師益友,在東北大學(xué)草創(chuàng)階段更是多有借重。極具實力的管理美國退還庚款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中方董事不僅有張伯苓,在董事長范源廉病逝后,進(jìn)而接替此職。不過,這些榮耀的取得,均來自民國前期的北洋政府。隨著1928年夏季國民革命軍二次北伐,京津一帶再次迎來“改朝換代”。6月12日,南開中學(xué)期末考試最后一天,天津城西馬路一帶槍聲大作,革命軍進(jìn)城,奉系督軍褚玉璞退兵。作為社會賢達(dá)的南開校長張伯苓,面對南方革命政府,或多或少有那么一點“前朝舊人”色彩。畢竟他跟隨嚴(yán)修“化緣”興學(xué),與北洋軍政勢力結(jié)緣不淺,屬革命黨秉政之初須排斥之列。
南京國民政府在教育界實施的大動作,首先是改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其美方董事基本留任,而原中方董事大部分被撤換。南京方面認(rèn)為,該機(jī)構(gòu)由賄選總統(tǒng)曹錕任命,“現(xiàn)國民政府統(tǒng)一全國,此種賄選亂命自當(dāng)根本取消。且所任命之董事中,有為國民政府所通緝者,有為擁護(hù)賄選之官僚與學(xué)閥者,皆不當(dāng)任其主持國民政府之教育文化事業(yè)”。頗有些書生氣的胡適對此舉持異議,致函主持其事的蔡元培,希望將享有“清譽(yù)”的周詒春(前清華校長)、張伯苓留任,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辭職換取張的留下。蔡元培回函予以“峻拒”。顯然,國民黨政權(quán)此時對所謂北洋舊人尚不肯包容……
不過,張伯苓不同于書生氣十足的胡適,他處世顯然更加現(xiàn)實和靈活。南開學(xué)校每年幾十萬支出的費用等待著他設(shè)法籌措,而這倘離開了當(dāng)權(quán)者幾乎不可想象。好在蔣介石委派秘書錢昌照遍訪京津各校,對南開印象頗佳,而張伯苓也不失時機(jī)地表露對新當(dāng)政者的擁戴,這些歸結(jié)為一個尚好的回報:蔣命令已經(jīng)“易幟”的張學(xué)良給予南開一定力度的常年資助。無疑,此舉大大拉近了張伯苓與新政權(quán)之間的距離。事實上,當(dāng)南方二次北伐大局已定,張伯苓就通過故交孔祥熙的關(guān)系,在上海拜訪了主管財政的宋子文,為進(jìn)一步結(jié)納最高當(dāng)局埋下了伏筆。
1929年的前九個月,張伯苓在美歐旅行,其目的在考察教育和募集經(jīng)費。這期間,年屆古稀的嚴(yán)修于3月中旬辭世,數(shù)月后,南開大學(xué)五位重要教授紛紛離校他往。面對校內(nèi)多事之秋,張伯苓并未中斷行程。他在海外屢屢發(fā)表高論,向國民政府示好。在斯坦福大學(xué)演講,談及國內(nèi)形勢,他說:“今革命幸告成功,不啻去云翳而見天日,全國氣象煥然一新。”在另一次演講中,他稱“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由軍政而訓(xùn)政,再次為憲政,步驟井然,如能行之不誤,定能進(jìn)入承平之世”。在倫敦的一個歡迎會上,有人質(zhì)問:南京大興土木修中山陵,是否虛糜金錢?張伯苓應(yīng)聲答道:“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至少可說是最近四百年來第一人,無論用多少金錢,以紀(jì)念孫先生,十分正當(dāng),十分應(yīng)該。”在政治歸屬上,伯苓先生可謂做足了姿態(tài)。
少帥張學(xué)良應(yīng)允資助南開二十萬元,分十年付清,可是首年撥付二萬元后,第二年僅交付四千元,其余便遲遲無下文。張伯苓歸國后,迭函東北要員王維宙等人催促續(xù)撥,看來并不順利。他又聯(lián)系當(dāng)年與嚴(yán)修有些交誼而今已成黨國“新貴”的李石曾,希圖得到其主持的俄國退還庚款的補(bǔ)助。晉系將領(lǐng)傅作義時任天津警備司令,對于張伯苓辦學(xué)之艱難有所體認(rèn),主動提議將所轄南郊小站營田交由南開大學(xué)經(jīng)營,以其所得用于辦學(xué)。傅、張之間的交情由此開啟,后來傅將軍在長城一線抗戰(zhàn),收復(fù)百靈廟,張伯苓贊為民族英雄,發(fā)動民間捐款捐物,支援前線將士。廈門大學(xué)的有關(guān)捐助即是經(jīng)由南開張伯苓之手轉(zhuǎn)交。全面抗戰(zhàn)開始后,傅作義的家眷被安置于重慶南開中學(xué)校內(nèi),由張校長特別關(guān)照。當(dāng)然,這已是后話。
二
上世紀(jì)三十年代初,時局動蕩,南開各校經(jīng)費拮據(jù),僅南開中學(xué)即負(fù)債達(dá)三十萬元,可謂靠赤字維持運作。四川民生公司老板盧作孚由丁文江介紹,造訪南開,張伯苓向其大吐苦水。1930年12月,蔣、馮、閻的“中原大戰(zhàn)”因張學(xué)良的介入援蔣而終見分曉,東北軍再度入關(guān),接管平津地區(qū)。作為老朋友,少帥堅請張伯苓出任天津市長一職,顯然也順乎情理。可是,張校長“在茲念茲”的重心在南開,緩解辦學(xué)難局乃首要急務(wù),哪有心思“更上層樓”?他極其熱情地接待來校視察的張副總司令夫婦,卻以校務(wù)羈絆、“不愿放棄二十六年教育生涯而卷入政治漩渦”為由婉拒了其盛情相邀。
此時,張伯苓真正心儀的領(lǐng)袖人物是南京的蔣介石。就在接待少帥夫婦一周之后,張伯苓偕心腹秘書伉乃如來到南京,于12月24日首次拜見蔣介石。蔣對張三十年如一日專心辦學(xué)大表欽佩,對于南開校風(fēng)稱譽(yù)不已,了解并同情南開的經(jīng)濟(jì)狀況,允諾設(shè)法予以補(bǔ)助。張伯苓對于最高當(dāng)局重視教育的表態(tài)印象極深,在其后寫給宋子文的信函中特別提及。顯然,宋應(yīng)是此次會面的牽線人。此后,張伯苓又幾次致電致函蔣介石,陳述學(xué)校經(jīng)費困難各節(jié),進(jìn)而提出由英國退還庚款委員會每月指配二萬元補(bǔ)助南開的請求。也就是在此前后,張校長罕見地對已經(jīng)從政的校友田炯錦表示:自己雖以專心辦理教育為職志,但南開造就的學(xué)生應(yīng)在政治上有所貢獻(xiàn),因為政治實一切事業(yè)之重心。他期望南開人在政治領(lǐng)域能形成自己的影響力。此一變化未可小視,潛心辦學(xué)者開始萌發(fā)政治進(jìn)取心。endprint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在北平組建華北政務(wù)委員會,張伯苓被任命為委員之一。兩年后又組成由黃郛領(lǐng)銜的政務(wù)整理委員會,張仍任委員之職。這期間,已決意棄學(xué)從政的翁文灝在廬山向蔣介石進(jìn)言:國家危難之際,急應(yīng)延攬人才,不宜過分拘泥于黨派,而應(yīng)擴(kuò)大用人范圍,并舉薦了胡適、張嘉璈、吳鼎昌、張伯苓等多位非國民黨人士,蔣表示愿意延攬借重。從后來的事態(tài)觀察,蔣基本采納了翁的建議。張伯苓雖然時常向外界表示,自己對政治完全是外行,但對于華北事務(wù)亦曾熱心參與和建言。他以社會賢達(dá)身份赴山東,盡力調(diào)解韓復(fù)榘與劉珍年部的戰(zhàn)事,效果尚佳;當(dāng)華北形勢日益危殆時,他大膽向南京當(dāng)局直言:為了防止日本使華北特殊化的預(yù)謀,中央應(yīng)盡力支持宋哲元等華北將領(lǐng),以增加他們對國民政府的向心力。蔣介石聞言,頗為重視。
面對三十年代前期華北錯綜復(fù)雜的局勢,蔣介石對于像張伯苓這樣在地方上深具影響的人士特別倚重,不但發(fā)函征詢方策,還附來密電本,囑可直接向其建言。張復(fù)函稱:“承頒給電本,謹(jǐn)當(dāng)密藏待用”,“苓遇事勉竭愚蒙用供采擇,但不愿一知半解動擾聰聽。”可知,此時二人關(guān)系已非泛泛。1933年7月,具有南開背景的青島市長沈鴻烈因權(quán)力摩擦提出辭職,張伯苓為此一再函電蔣氏,力言“不宜聽其高蹈遠(yuǎn)行以去”,“甚盼中央處置此事加以審慎”。不久,蔣復(fù)電:“沈市長由威(海)返青復(fù)任,乃中央懇切慰留之結(jié)果,報載易人之說不足據(jù)也。”對于張伯苓涉及人事安排的意見,蔣予以最大程度的關(guān)照。
這個時期,羅隆基任教于南開大學(xué)政治學(xué)系,并主筆天津《益世報》,該報對南京當(dāng)局若干外交舉措多有抨擊。蔣介石最初對這位自由知識分子施以籠絡(luò),請張校長告知羅,蔣邀其南下并將親自接見云云。可是,其后《益世報》的言論并未“收斂”,南京方面即勒令其停刊。為此,蔣委托黃郛電告張伯苓:平、津各報年來頗多持論偏激,行營認(rèn)為莠言亂政,主以切實制裁。《益世報》未知審慎,因而獲咎,據(jù)聞尚系最寬大之處分,只須該報能了解國家立場,認(rèn)識地方環(huán)境,持平立論,不難力謀恢復(fù)。顯然,蔣希望張起到配合和緩沖作用。張伯苓深得最高當(dāng)局倚重,昔日友人不免有所請托,而張卻回應(yīng):“最近雖于國務(wù)時有參與,但俱屬虛名,與政界并無切實聯(lián)絡(luò)。”可謂虛實之間,應(yīng)付裕如。
三
張伯苓政治地位的上升,有力緩解了南開辦學(xué)經(jīng)費困局,來自國民政府的資助,也使學(xué)校的私立性質(zhì)越來越名不副實。一個難以抗拒的現(xiàn)實壓力愈加明顯,即日軍步步緊逼,華北已危若累卵。張伯苓眼光超前,很早便做出在西部建立分校的決策,而到了1935年初,南開董事會正式討論將大學(xué)部改為國立的議案,此前,張已向行政院長汪精衛(wèi)、教育部長王世杰通報此事。隨后,他又派何廉教授赴寧向教育部交涉改轉(zhuǎn)國立具體事宜。6月間在南開大學(xué)畢業(yè)典禮上,張伯苓宣布,將學(xué)校獻(xiàn)給政府,稱“現(xiàn)在政府領(lǐng)袖真能埋頭苦干,我們應(yīng)當(dāng)改變從來懷疑政府的心理,依賴他們,所以愿把畢生心血結(jié)晶的最高教育事業(yè)奉之政府,化私為公”。其后,張伯苓當(dāng)面向蔣介石表明了此一心愿。幾乎同時,私立廈門大學(xué)改為國立,陳嘉庚先生終于卸下沉重負(fù)擔(dān)。張伯苓有否同樣心理,尚不得而知,他對國民政府高度信賴確乎無可置疑。政府方面對于南開的國立訴求雖未即刻接受,但并入西南聯(lián)大之后的南開,實際上已屬國立性質(zhì),盡管正式賦予國立名義延后到1946年復(fù)員返津時。
在西部設(shè)立南開分校的設(shè)想,得到蔣介石鼎力贊助,他允撥五萬元作建校經(jīng)費,這筆款項很快到賬。張伯苓遣人速購重慶杜家坪地段建筑校舍,此處“無城市之喧囂,有山水之清幽”,靠近重慶大學(xué),具有地利之便。這便是后來的重慶南開中學(xué)。蔣贊助南開渝校之舉,產(chǎn)生帶動效應(yīng),四川省主席劉湘亦捐款相助。不久,王世杰秉承蔣介石之意,任命張伯苓擔(dān)任四川大學(xué)校長。張以與嚴(yán)修有誓約終身辦理南開為由,予以婉拒。
就在此時,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fā)生,張伯苓驚愕之余,拍發(fā)私人電報給張學(xué)良,痛陳利弊,呼吁放蔣!后來美國《亞洲與美洲》雜志刊文稱:“當(dāng)委員長在西安被綁架的時候,張博士給少帥的私人電報在后來的釋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孔祥熙急電張伯苓:“吾兄與漢卿相知甚久,此時一言九鼎,當(dāng)有旋轉(zhuǎn)之效”,請兄飛赴南京或西安,斡旋“陜變”。張隨即赴寧候命。南開大學(xué)全體教職員和學(xué)生會在得知事變消息后,或通電全國,或發(fā)表時局宣言,痛責(zé)兵變,維護(hù)領(lǐng)袖,重申法紀(jì),敦促放蔣。在西安各方談判過程中,曾醞釀改組“內(nèi)閣”,張伯苓被列為教育部長人選。蔣介石獲釋返寧,南開師生致電慶賀,學(xué)校為此特放假三天,其喜慶氣氛猶如節(jié)日。張伯苓稱此次事件為“逢大兇化大吉”。蔣氏隨后復(fù)電張校長:“陜變發(fā)生后貴校師生備極關(guān)念,甚為感慰,特謝!”事變和平解決,各地欣喜之狀,不獨南開為然,然該校與事件當(dāng)事者關(guān)系之特殊,引人關(guān)注。張校長與蔣的互信更加牢固,而與少帥的交誼則戛然而止。
1937年夏,張伯苓參加廬山談話會,在南方逗留期間,平、津淪陷,南開大學(xué)被日軍炸毀。張臨大難而不驚,他向報界表示:毀掉的是校園,不死的是精神。《中央日報》刊發(fā)社評盛贊“南開精神”。作為最高當(dāng)局的蔣介石為此作出“有中國就有南開”的明確表態(tài),既是豪言,也是承諾。這似乎也預(yù)示著張伯苓將跟隨蔣氏在政治上走得更遠(yuǎn)。此后,南開大學(xué)與另兩所國立名校組成西南聯(lián)合大學(xué),在春城昆明度過艱難的抗戰(zhàn)歲月;而重慶南開中學(xué)則成為戰(zhàn)時陪都文化教育的一個亮點。張伯苓常駐渝校,辦學(xué)一如往昔的井井有條,聲譽(yù)卓著。校內(nèi)聚集了不少社會名流或其家屬,如翁文灝、馬寅初、譚熙鴻、段茂瀾、郝更生、張平群等均借住校內(nèi)宿舍。為數(shù)不少的各界要人的子弟進(jìn)入該校就學(xué),如盧作孚、曽養(yǎng)甫(戰(zhàn)時交通部長)、陳調(diào)元等人的子女。知名的南開校友周恩來、吳國楨、梅貽琦等不時造訪,而蔣介石亦多次來校,看望張校長。此時,南開的經(jīng)濟(jì)狀況已有保障。據(jù)喻傳鑒、黃鈺生等南開元老憶述:南開被炸后,尚有資金百萬元之譜,匯至重慶,作為基金,投入在渝各實業(yè)部門,諸如水、電、水泥、民生、華西等公司,“莫不有南開肥本”。只可惜,抗戰(zhàn)中期以后,大后方經(jīng)濟(jì)陷入困境,南開資金所剩無幾。endprint
四
抗戰(zhàn)期間在重慶,張伯苓的一項新的重要工作,是擔(dān)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議長一職始由汪精衛(wèi)、繼由蔣介石出任。其職責(zé)之重大,地位之高,不言而喻。這是全民抗戰(zhàn)為國效力的使命,按胡適等人的說法,是應(yīng)國家戰(zhàn)時征召,張伯苓沒有推辭。國民政府選中張氏,自然是看重他的社會賢達(dá)身份,當(dāng)然與政府乃至最高當(dāng)局的密切關(guān)系也是重要考量。他的態(tài)度是:中國今日之局勢,非全國共同一致奮斗,不足以挽救危亡,非服從一個領(lǐng)袖之主張,不能挽狂瀾于既倒。在多個不同場合,他更明確表示:“擁戴蔣委員長為唯一最高領(lǐng)袖”。張、蔣之間的互信,在歷史緊要時期,外露到社會政治層面的最高點。
張伯苓履新,在參政會近百名各界精英面前亮相,各方感受不一。與張資歷相當(dāng)?shù)狞S炎培在日記中記述:伯苓在參政會發(fā)言“頗多失禮,聞?wù)卟粷M”;“伯苓主持(會議)慌亂,致會場大嘩”;“副議長張伯苓致詞,甚失當(dāng)。此君總是如此,真無如之何”。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中共方面參政員周恩來評論自己的老師則出言謹(jǐn)慎:伯苓先生是教育家,從事政治非其所長。《新民報》記者寫道:“主席張伯苓,老態(tài)龍鐘,有如導(dǎo)演無聲電影。”但官方的《中央日報》每每報道張在參政會的表現(xiàn)就大不相同:張先生的講演,“足以提高國人抗戰(zhàn)信念,詞畢,全場興奮”。蔣介石更是以細(xì)微的關(guān)懷,不斷的探訪,鼓勵和支持張伯苓的工作,還邀請他到中央訓(xùn)練團(tuán)講演《學(xué)校訓(xùn)育問題》。就是在這一講演中,張伯苓首次談及“入黨”問題:“……更要與黨發(fā)生密切的關(guān)系,須知從前入黨的使命是在推翻專制,而今后入黨的任務(wù)是抗戰(zhàn)建國,較前更為重大,每個國民都要為黨而努力奮斗,使黨的基礎(chǔ)日趨穩(wěn)固,建國事業(yè)才能成功。”此后不久,張伯苓加入了國民黨。此舉雖有當(dāng)年大學(xué)校長被要求必須入黨的背景,但同虛與委蛇者相比,似尚有區(qū)別……
蔣介石每次到訪重慶南開中學(xué)看望張伯苓,對其辦學(xué)成績總是贊不絕口。1943年12月,重慶教育當(dāng)局以“辦理成績甚佳”傳令嘉獎南開中學(xué),同獲嘉獎的還有清華所辦中學(xué)和市女中兩校,清華之中學(xué)以注意學(xué)生營養(yǎng),渝市女中以師生精神振奮而獲嘉獎。此前,蔣介石著《中國之命運》出版,重慶南開鄭重部署本校師生展開研讀,并由校長辦公室通告,有關(guān)研究報告須在規(guī)定時日內(nèi)繕交,顯得頗為重視。為此,張伯苓還特別撰寫了《中國之命運與南開之教育——由“公能教育”進(jìn)為“建國教育”》一文,文中提出:“今后南開教育方針,實有由‘公能教育更進(jìn)為‘建國教育之必要。以‘建國為教育之最后目標(biāo),以‘公能為訓(xùn)練之具體方針。彼此配合,相輔相成。”南開特有的公能校訓(xùn)及教育,此時已然被涂抹上“黨化”色彩。不過,對于國民黨官場的貪腐現(xiàn)象,張伯苓私下也多有抱怨,尤其對于1944年冬桂林失守,致使日軍進(jìn)占獨山,形成直逼貴陽,震動重慶的態(tài)勢大為不滿。蔣介石聞知,親自登門勸慰,解釋說:“我們與美國合作,確有攻擊日本的力量,請張先生安心。”意在消除其憤懣和疑慮。
八年抗戰(zhàn)終于迎來勝利,對于天津市長人選,蔣介石聽從張伯苓的建議,任命了張廷鍔。此人戰(zhàn)前擔(dān)任過該職,對南開有所助益,與伯苓先生私交甚好,但抗戰(zhàn)期間無作為,且有通敵嫌疑。陳果夫等強(qiáng)烈反對,國民黨內(nèi)吵翻了天,要求蔣收回成命。蔣解釋道:“有關(guān)天津的事要尊重張伯苓先生意見,馬上不能改變,以后我再想法調(diào)整。”蔣隨即任命南開畢業(yè)的國民黨人杜建時為副市長,其后不久接替了張廷鍔。據(jù)《竺可楨日記》披露:國民黨內(nèi)派系爭權(quán)激烈,一些小團(tuán)體抱怨(蔣)主席對政學(xué)系言聽計從,使其把持權(quán)柄。“并謂最無恥者為張伯苓、蔣廷黻等,如張等不知斂跡,不惜以對付楊永泰者對付之……”楊永泰者,昔日湖北省主席,因內(nèi)部權(quán)斗遭暗殺。可知,蔣對張伯苓之倚重,曾引發(fā)國民黨內(nèi)暗流涌動。
五
戰(zhàn)后,張伯苓一度赴美治療舊疾,蔣介石贈送一萬美金供其使用。這是張生平最末一次訪美,美國文教界盛情接待。美國人認(rèn)為,張伯苓深得蔣先生信任與尊敬,卻不是國民黨的政治衛(wèi)士,長期從事教育,實際上也是中國年長的政治家。敏感的美國觀察家特別注意到張在戰(zhàn)后中國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1946年12月,張伯苓回到上海,旋即赴南京,蔣介石設(shè)宴為其接風(fēng),主動提議在長春設(shè)立南開第三分校。翌年3月張返津,一個“喜訊”在等待他,天津市長杜建時報告,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漢奸中沒有一個戰(zhàn)前南開畢業(yè)生!張校長聞之甚感欣然,稱:“這比接受任何勛章都讓我高興。”
當(dāng)年平、津官場知情人士有如下“推想”:鑒于參政會時期的經(jīng)驗,蔣主席會讓伯苓先生在未來政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倘不得已建立各黨派聯(lián)合政府,伯苓先生出面組織國會,可為各方接受。如恢復(fù)先前林森做主席的架構(gòu),伯苓先生可謂最理想人選。如此推想,是因為看得出“蔣主席尊敬張先生,是另有用意的”。對此,張伯苓應(yīng)能感覺到。1947年冬,在蔣介石安排下,張伯苓參選國大代表,南開校友組成“公能學(xué)會”幫助校長競選,外加三青團(tuán)力量配合,終以十三萬余票當(dāng)選,據(jù)說個人得票數(shù)居全國之冠。到1948年初,南京便盛傳張伯苓將競選副總統(tǒng),張出面否認(rèn)。同時,《大公報》報道,七十二歲的張伯苓“病體康復(fù)后,有時出席會議二、三小時,始終振奮不懈,每天在辦公室工作三小時”云云,似乎也在透露某種信號。3月底,行憲國大在南京開場,張入選主席團(tuán)。其時,國共決戰(zhàn)已拉開大幕,張伯苓認(rèn)定“戡亂在我看來只是個時間問題”,頗為樂觀。6月間,經(jīng)蔣介石提名,張出任考試院長一職。張伯苓走出這一步,南開內(nèi)部有人勸阻,更有人“勸進(jìn)”。“事后諸葛”式的正面記載充斥相關(guān)校史文本,不完全值得取信。張氏長子張希陸就此講過這樣一番話:“我父親一生從年輕時就被人利用,現(xiàn)在家里人(指南開人)利用他更不應(yīng)該。”張大公子雖語焉不詳,意思卻很明白。
問題在于,張伯苓本人對于國內(nèi)局勢嚴(yán)重“誤判”,即使到了這年8月仍表樂觀。可是,多少有些令人不解的是,國民黨退走臺灣前,蔣介石父子幾次三番登門勸張“出走”,可去臺島,也可去美國,并留下專機(jī),隨時可用。此前張的家眷已被接到重慶,應(yīng)該無后顧之憂,張伯苓留在大陸……
有人將張、蔣關(guān)系概括為“互相利用”,未免失之于簡單。張伯苓辦學(xué)求助于當(dāng)政者,非蔣一人而已,何以對蔣情有獨鐘?蔣介石從多個渠道得知南開辦學(xué)聲譽(yù),對張心生敬意,并非矯情作態(tài);二人關(guān)系發(fā)展有一大背景,即中日交惡,危難日亟,御侮求存,相互支持;二人早年均投身軍旅,對于教育與國家的關(guān)系理解,乃至學(xué)校管理方式,具有共識。至于張伯苓晚年“成于蔣亦敗于蔣”的大起大落,人們慨嘆“生于末世運偏消”之余,只能從深邃歷史中尋覓題解了。
張伯苓是否屬于嚴(yán)格意義上的人文知識分子,尚有歧見。張中行《流年碎影》和何兆武《上學(xué)記》等書中,有關(guān)張先生的記述頗有“不敬”。曾在南開任教的蔣廷黻、方顯廷等人回憶錄中,只恭維老校長的辦事能力,甚少提及其學(xué)養(yǎng)。南開元老黃鈺生稱伯苓先生“善辯而不文”,乃“教育實行家”,而非理論家,表述婉轉(zhuǎn)而接近實情。據(jù)南開另一元老喻傳鑒回憶:校長出門,必帶三部書,《四書》、《圣經(jīng)》和《三民主義》。嚴(yán)修先生出身舊學(xué),尋得有些新學(xué)背景的張伯苓一同辦學(xué),亦可謂“中西合璧”。范孫先生早年出仕,晚歲則一心辦學(xué),即使好友袁世凱后來屢屢委以高官,亦心靜如水,不為所動。伯苓先生一生大半精力經(jīng)營南開學(xué)校,聲名鵲起,贊譽(yù)者眾,而晚年卻情不自禁地投入政治激流,終至落得“晚節(jié)不保”。看來,他尚缺乏嚴(yán)先生那種眼光和定力,這與學(xué)養(yǎng)底蘊(yùn)是否有關(guān)呢?值得玩味。
(梁吉生編撰:《張伯苓年譜長編》上、中、下三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