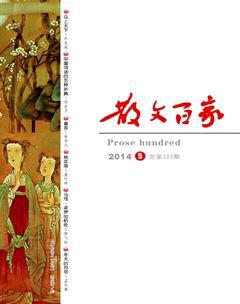別夢依稀祭故園
劉雨虹
我的故鄉在麻南,她的名字很美,叫望花山。
闊別故鄉幾十年了,很少有機會回去看看,即使偶爾來回一兩趟,也總是驅車登古原,來去匆匆,真有些“坐車望花”的意味。今年的秋天,是母親的祭日提醒我必須再次回一趟老家,不過這一次我是特意徒步前往,內心深處當然是想踏實地重溫一下回鄉的路。這世上每個人都是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去,記住來時的路是很好的,不然會容易迷失將要找尋的路。
其實每次回鄉總有一種別夢依稀的感覺,不管是匆匆地來,還是匆匆地去。人到中年,故鄉的情結、尋根的欲望,往往愈來愈深,愈來愈濃,愈來愈難以釋懷,一如“剪不斷、理還亂”般的悵惘。
踏在兒時上學的小路上。兩邊的秋草已漸漸泛黃,極目四望,畈野里那楓葉、烏桕葉都紅成了一片,像醉漢的臉。“小小少年郎,騎馬上學堂,先生嫌我小,肚中有文章”,耳畔不禁泛起童年的歌謠,這是上學路上父親教我唱的第一首兒歌。那時候從家到學校有三四里路,每天上學來去一趟,總要翻兩三個田畈,沿途有幾道溝坎我記得清清楚楚。
當年在我們灣里,父親算是個有學問的人,遠在離家二十里外的一所學校教書。因為他懂得讀書的真正涵義,因此,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們姊妹三人身上,每逢星期天回家,總是教我們念詩識字。幾個兒女中,最疼愛的就是我這個丫頭片子。上學時總是千叮嚀萬囑咐,不是擔心我個子小走路不穩而摔跤,就是怕我不小心掉進了水溝。為此,不少兒童伙伴在上學路上譏笑我是個“膽小鬼”、“黃毛丫頭”。我也不知流下了多少委屈的淚。
記得有一次,學校里要搞什么游行活動,要求所有的小將們都要有紅纓槍。大一點的男孩們有的把學校的門板撬去了,鋸成菱形的槍頭;有的偷老師的紅墨水,把洗白的黃蔴染成紅纓;還有的把家里的薅秧棍弄來做柄,肩扛紅纓槍,雄赳赳氣昂昂地在校園里文進武出,仿佛他們才是潘冬子、是小兵張嘎。班里只剩我一個人沒有槍。老師說,沒有紅纓槍的不準去游行,不準上體育課(我們那時的體育課,一學期就是扛著紅纓槍練隊形)。一回到家我就急哭了,爸爸一邊摸著我的頭,一邊安撫我說,就是不睡覺也要給你做出來,保證你明天去學校能參加游行。那個晚上,半夜醒來,我還看見爸爸在昏暗的煤油燈下,手拿菜刀、木棍,彎腰屈背叮叮咚咚地折騰紅纓槍的情景,他把他的父愛一聲不吭地鑲嵌在那把漂亮的紅纓槍里,幫我找到了“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的感覺,使我有機會與全班同學融合在一起……
不知不覺地來到了故鄉布滿紅薯地的山頭。幾位鄉親邊打招呼,邊吆喝著拉犁的耕牛。溝頭地畔,大大小小的紅薯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一看見滿地的紅薯,眼前就浮現出母親那張黑里透紅的臉龐,想起了當年與她一起挖紅薯的情景。那個秋日的黃昏,我和母親勞累了一整天挖了三塊地的紅苕,苕藤放在田畦中,紅苕扔在地溝里,母親吩咐我,要把苕藤捆好挑回去喂豬,她自己挑紅薯,挑了四五趟后,月亮已在東天升起。最后兩小捆苕藤壓得我氣喘吁吁,一路歇了兩三回肩。母親挑的則是兩大筐紅苕,扁擔在她肩上壓成了一道彎弓,吱吱作響,可她始終一聲不吭地咬牙前行。我問她:“媽,苕么樣這么重,這么壓人?”她說:“伢呀,不重的東西不是好貨,癟殼谷輕飄飄有個么用呀!”我一邊趔趄著,一邊盼望離家的距離近點再近點,并不在乎她的話。母親雖然不識幾個字,但她說的話就跟她自己一樣樸實,現在想來,好像是帶著泥香的山珍 ,管吃管用。“不重的東西不是好貨,癟殼谷輕飄飄的有個么用呀”這句不經意的話在我后來漫長的工作歲月中無時無刻不在耳邊縈繞,它無不警醒我要腳踏實地做人,腳踏實地做事,莫學根淺的墻上蘆葦和中空的山間竹筍。
……
“姑娘,回家行孝來啦!”我的思緒被山腰幾個老伯的聲音打斷。
“是,也不全是……你們要注意身體莫太做苦了!”
“我們才曉得享呢,不像你爸媽那時候……”
……
秋風中,我站在父母墳頭,弓下身來,默默地點燃了紙錢,做一次虔誠的家祭。眼里有一種潮濕的感覺。太多太多的話充塞在心里,雜陳一個五味鋪翻江倒海。夕陽輝映著田間地頭父老鄉親們那一張張古銅色的臉,和爹娘一般慈祥,滿眼凝望,笑容可掬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