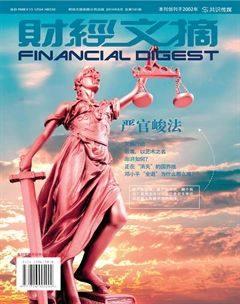如此學術
Heike Holbig


非常廣義地說,哲學關乎的是真理,社會科學關乎的則是社會關系與社會形態。因此,我們應該能夠理解為何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時代以來,哲學和社會科學就在社會主義的展望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的延安時期開始,中共就在科學與黨對智慧和領導權的壟斷之間建立起了有機聯系,這種聯系是蘇式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也成為了毛澤東及其同志的藍圖。
黨辦學術的前世今生
在中共建政后一個月,以蘇聯學術制度為模板的中國科學院便宣告成立,這表明了科學具有相當高的政治地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里,“紅與專”的階級斗爭概念導致了教師、學者和整個學術界頻繁地遭受政治壓迫與動蕩,哲學和社會科學也幾乎蕩然無存。為了重建并激活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研究,中共于1977年5月將部分研究單位從中科院剝離,建立了中國社科院,并在全國建立起了包括中央、地區和地方各級研究院在內的整套體系。中國社科院的政治角色不僅僅體現在它與國務院的附屬關系,更在于迄今為止所有社科院的學術工作都直接受到宣傳系統的監督。
中共十八大進一步確認了這一點。在這次會議的報告中,和新聞與出版、廣播、電視、電影、文學與藝術一道,哲學和社會科學也屬于需要大力發展的領域,以“提高中國文化的總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正如近些年來黨的文件所表明的,當下的哲學和社會科學不僅僅被賦予了列寧主義意義上“經典”的意識形態功能,還扮演著宣傳、推銷“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進步性、創新性和國際競爭力的全新角色。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黨能夠成功地、普遍地令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為己所用。相反,與許多中國同行的對話表明,學術圈的多數人——尤其是社會科學家——都學會了如何規避意識形態限制,并擴展黨教條劃定的邊界。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生大多學會了“說兩套話”的藝術,即在書、文章和會議的標題上避免使用敏感詞,將中國歷史中或是國外討論中的主題作為代理,以此展開對當代中國敏感的國內問題的討論。不過,熟練掌握規避的藝術并不意味著哲學和社會科學承載的意識形態功能一無所獲。相反,中國的社會科學家被視作專業的雜技演員,游走在個人研究偏好與追求學術(也許還包括政治和社會)影響力的欲望之間的縫隙里。
項目·江湖
如今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在申請第三方資助時擁有眾多選擇。首當其沖的是教育部旗下的眾多項目,例如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和人文社科領域的重點研究基地,這些項目由國家人文社科基金在各大學設立。此外還包括2011年推出的一系列創新項目,旨在提升大學的創新能力;以及中國社科院設立的國家出版基金和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另外一系列主要的研究項目由國家社科基金設立,其中包括“重點項目”“年度項目”“青年項目”“后期資助項目”“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西部項目”等等。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包括了23個專家小組,對應的是23個傳統學科: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黨史與黨建、哲學、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管理學、統計學、政治學、社會學、人口學、法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學、民族問題研究、宗教研究、中國文學、外國文學、語言學、新聞與傳播研究、圖書館/信息科學與文獻學,以及體育學。其他三個分列學科(教育學、藝術學和軍事學)的研究則受到單獨監管。每個專家小組的人數平均約為十人,正式任期為五年。在專家小組任職期間,他們要為社科基金的項目規劃和研究日程的設立提供建議,審查對重點項目的申請,評估研究結果,并為國家社科基金頒發的特殊獎項推薦人選。
在實踐中,專家小組成員的聘用因缺乏透明度招致了許多批評。作為不成文的規則,被認為在各自學科的發展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研究機構可以向專家小組推薦自己的代表,這些高級別的學者一般不僅僅具有卓越的學術成就,同時還與黨國的上層人士建立起了密切的聯系。這些學者往往會在專家小組里待上好幾個任期,因此,許多人認為他們實際上成為了學術“寡頭”。在后續的對基金項目申請者的評審過程中,從全國范圍內的專家數據庫中選拔出的同行也會參與其中,然而,最終的選擇結果仍然是由各專家小組成員自己做出的,他們在決定時往往還會考慮到申請者的機構和個人背景。
意識形態改頭換面
考察最近幾年社科基金的重點項目,可以發現當下中國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的動向。觀察自2004年以來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的年度狀況,最為引人關注的趨勢首先是總數量的指數型增長。每年立項的重點項目數量從約20項增加到2009年的約50項,這一數字在2010年躥升到了150項,在2011年達到了228項,2012年更是創下了257項的記錄。
造成這一趨勢的原因部分在于官方政策的變化。立項項目數量急劇上升的背景在于,黨提出了推動哲學和社會科學發展的政策。據中國媒體報道,2011年5月一位主管意識形態的高官親自要求大幅增加國家社科基金的預算,這對于社會科學的整體膨脹發揮了引領作用。
除了官方政策在供給方面起到的擴張作用外,各種需求方面的因素同樣促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預算的急速增長。一方面,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顯然部分是出于物質刺激方面的考慮。在評審過程中勝出的申請人在三至五年間能夠獲得60萬至80萬人民幣的資金。在中國的學術環境中——至少在社會科學領域內——這筆資金是相當可觀的。據說存在著合法與半合法的用這筆資金補貼研究者個人收入的途徑;盡管這類行為近來遭到了禁止,但資金仍能用于聘請助手或是購買材料或其他設備。
國家社科基金近年來的另一重大變化是重點項目研究課題的多樣化,這與2010年以來立項項目的迅速增加是同步的。狹義上的黨的理論課題——如“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在2006年和2007年(即中共十七大前夕)約占課題總數的三分之一;這些課題的比例在2011年至2013年(即中共十八大前后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分別下降到了4%、12%和25%。
具體而言,在三大項目類別中,“應用對策”(指的是社會、經濟、法律等領域實用性更強的課題)和“跨學科研究”明顯體現出了遠離狹義的黨的意識形態的趨勢。然而,對于“基礎理論”(指的是更加理論化的課題)而言,趨勢就截然不同了;這一類別構成了重點項目的主體部分,并且依然承擔著回應黨的文件和理論的任務。該類別中黨的理論課題——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和“中國夢”——的比例在2011年為13%,在中共十八大召開的2012年迅速上升到了25%,而在一年之后又迅速下降到僅僅3%。
另一方面,大部分“基礎理論”類別的項目明顯地呼應著宣傳中國歷史與民族文化這一黨提出的新重點。這些項目的名稱似乎就是在重述中共有關“社會主義文化”的文件中列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和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此外,這些項目仿佛還滿足了官方重寫中國歷史的要求:前幾年是清朝熱,近些年來則是強調中國更早期的歷史。
總之,盡管這些新的研究日程并非是在鸚鵡學舌般地重復狹義的黨的意識形態,但它們仍然是在廣義上將社會科學“重新意識形態化”,即以塑造中國民族文化的方式來呼應近年來的官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