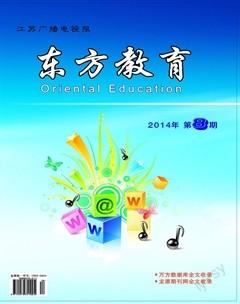職業病診斷的救濟問題
錢于立
【摘要】職業病診斷屬于醫學事實,因此不是具體行政行為,具有不被司法審查的事實性。但是,從權利救濟的角度出發,通過工傷認定及隨后的復議審查,職業病診斷在一定程度上應當獲得被審查與救濟的可能性。
【關鍵詞】職業病診斷;工傷認定;復議審查;救濟
根據立法上的定義①,職業病是指,企業、事業單位和個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在職業活動中,因接觸粉塵、放射性物質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質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可見,職業病并非特指一類專門的疾病,而是指任何因職業活動中的危害因素而可能引發的疾病總稱,因而判斷職業病的關鍵在于勞動者與職業活動之間的危害關系,表現為職業活動與勞動者之間漸進、慢發的疾病過程。同時,職業病具有工傷賠償領域的法律意義,所謂的“工傷”,是指在勞動過程中,因內部漸變的職業病或者外部偶然的突發事故造成的人身傷害,職業病的確證是工傷賠償關系成立的法定情況之一。
一、職業病診斷與工傷認定
(一)職業病診斷屬于醫學事實
職業病診斷是純粹的醫學事實,因此沒有直接的法律效力。盡管從工傷賠償的角度看,職業病診斷與特定的賠償性法律后果有一定聯系。但是,并不能因此認為職業病診斷具有醫學事實與法律事實上的雙重效果,因為職業病診的唯一效果是專家主張的醫學權威性;而法律事實是指在法律適用過程中對事實性內容的總稱,它可能是醫學事實,也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事實,但最主要的是它具有法律上的效果,因而具有法律上的權威性。醫學事實與法律事實的區別在于,醫學事實是法律后果的必要條件,而法律事實是法律后果的充分條件,只有當醫學事實上升為法律事實時,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因為醫學事實的認定來自醫學因果關系,而法律事實的認定來自法律上的因果關系。醫療行政部門誠然可以在行政法上為醫學專家預設某一個鑒定所必須涉及的步驟、方向或類別,但這些法規命令對診斷結果而言僅僅具有形式上的作用,實質上決定鑒定結果的仍然是醫學專家所使用的醫學數據、醫學經驗以及符合醫學標準的臨床判斷等等醫學上的因果關系。
因此,醫學事實與法律事實雖然在具體內容上可能是一致的,但是二者屬于兩個領域的問題。具有積極意義的醫學事實,可能經法律審查而變成否定性的法律事實,從而產生否定性的法律后果;或者,醫療機構或專家委員會在診斷職業病的過程中可能因違反醫療衛生部門制定的相關行政規章而承擔相應法律責任,這種責任只能說明是法律上的責任,而未必是醫學上的錯誤,因為法律所否定的不是醫學事實的權威性,而是醫學事實在法律上的有效性。
所以,職業病診斷屬于權威專家的醫學主張,不論它對勞動者的意義是積極或是消極,也不論它是否受到某些規章制度的約束,都無法直接在法律上產生勞動者有權得到賠償或用人單位依法不予賠償的約束力。
(二)職業病診斷的法律約束
職業病診斷的事實性并不意味著,職業病診斷不受任何形式的法律約束。職業病診斷本身雖然沒有法律效果,但當復議機關收到與職業病有關的、以工傷認定為復議客體的申請時,就必須考慮職業病診斷的合法性。在我國,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接受工傷認定申請,工傷認定的直接法律后果是工傷賠償法律關系,因而它是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政行為。根據復議的“全面審查”原則,如果職業病診斷在程序上存在違法,就可以根據程序瑕疵理論來判斷工傷賠償決定是否合法,因而有可能間接的給予撤銷。
例如:根據法律規定,診斷分析的內容是否有遺漏,鑒定過程是否存在徇私舞弊的行為,診斷工作是否科學公正等。復議機關雖然不可以直接否定醫學專家的權威意見,但是通過否定工傷認定來否定職業病診斷則是可行的,因為職業病診斷是否合法直接關系到工傷認定的合法性或合目的性。我國《職業病防治法》第42條,《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第2條及其第三章“診斷”名下的所有條款,都可以為審查工傷認定過程中對職業病診斷的審查提供法律依據。
因此,從工傷認定的意義上說,勞動者可以間接的請求復議機關對職業病診斷進行法律審查。但是,復議機關無法直接審查職業病診斷行為。因為只有在工傷認定過程中,職業病診斷才是一個上升為具有醫學內容的法律事實,而職業病診斷過程是否合法是工傷決定是否合法或合目的的必要條件。
二、職業病診斷的法律監督
(一)與具體行政行為的區別
具體行政行為的基本特征包括:行政行為的主體性、合法性、權利義務內容上的處理性、形式上的特定性以及行為客體上的具體性。根據我國立法上的認識,一般以“具體行政行為”來特指“行政行為”,目的是將行政主體通過法規、規章的形式作出的“抽象行政行為”從審查具體行政行為一樣的審查程序中排除出去。除此之外,“具體行政行為”與大陸法系的經典概念“行政行為”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的最重要的特定是:“處理性”。處理性是指,行政主體單方面作出的,以設定法律后果為目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命令②。也就是說,具體行政行為與它的法律效果直接有關,如果一個行政活動實際上并沒有任何法律上的約束力,它在形式上就不符合具體行政行為的形勢要求,也就不能稱其為一個具體行政行為或行政行為。
反之,職業病診斷鑒定是這樣一種行為活動,雖然從機構設置上,具有某種程度的排他性,也可以看做由上而下的單方行為,但這種單方性與法律約束力并沒有直接關聯。專家委員會的診斷鑒定并不能直接賦予勞動者請求工傷賠償的權利;工傷認定決定甚至可以反過來,從合法性的角度來否定職業病診斷在法律上的效力,因為醫學權威不等于法律權威。
可見,具體行政行為與職業病診斷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對權利義務內容的處理性上,而不在于二者在具體過程中是否受到法律約束。醫學專家或鑒定委員會在職業病診斷活動中受到有關法律規范的約束,但并不意味著職業病診斷活動的結論也必然具備法律約束力,這是由行政機關的法律義務與相對人主觀公權利的不對稱性決定的。
但問題是,對于職業病診斷這一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上非常重要的活動,怎樣通過外部法律監督而不僅僅是行政主體內部層級監督的方式,督促職業病診斷主體依法履行法律義務,主要是法定的程序性義務,并且受到法律救濟程序的制約。
(二)實在法規定
依據我國《工傷保險條例》(行政法規)第14條、《工傷認定辦法》(勞動保障部門規章)第4條和第5條不難發現,職業病是工傷認定的一種情形,而勞動者要申請職業病工傷認定,必須在形式上提供兩件材料,否則申請無法被受理:一是勞動關系證明;二是職業病診斷證明書或鑒定書。如果專家委員會對申請人作出否定性的鑒定結論,那么勞動保障部門就會拒絕他的工傷認定申請。因為,根據職業病診斷的事實性特征,勞動保障部門作為一般行政部門,在醫學領域上必須尊重專家意見的權威性。
所以,對職業病的救濟,可以通過工傷認定活動予以實現。但前提必須獲得有關職業病診斷的肯定性鑒定結論,以使其工傷認定的申請符合形式要求。但遺憾的是,不僅是勞動保障部門無法否定職業病診斷結論的醫學權威性,復議機關同樣也無法否定它的權威,至于法院則更沒有權力評價醫學事實本身的謬誤。所以,盡管職業病診斷鑒定書對其如此重要,除了有限的層級申訴之外,權利主體很難通過一般的法定救濟途徑來監督專家委員會的工作,職業病診斷活動此時似乎不僅僅是醫學上的權威意見,而是醫學專家的絕對意見了。
因此,職業病診斷的法律監督與相對人基本權利獲得法律救濟上的保障這兩個問題間似乎存在一個矛盾:《職業病防治法》、《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在法律原則上和法律程序上對職業病診斷診斷主體的診斷行為進行了明確的規定,《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雖然不是行政法律淵源,但也在實踐中為診斷主體提供了法律認可的鑒定標準;在這些法律文件的約束下,法律卻不允許勞動者因診斷主體不履行法定義務而提出法
律救濟的權利。職業病診斷活動等于是在法律救濟層面擺脫了審查監督而成為行政部門自我壟斷監督的對象,外部的法律義務似乎成為了內部的行政規則。如果可能的話,當勞動者有足夠的證據表明職業病診斷過程是非法的,例如:徇私舞弊;而從醫療機構到最高級的專家委員會的意見卻一致認為診斷合法,此時復議機關甚至連法院都無法成為裁判診斷程序是否合法的中間人,那么這樣一個職業病診斷行為是否依然能夠成為工傷賠償的事實依據呢。暫且不論職業病診斷是否絕對的不可審查,僅從法治的可接受性角度看,職業病診斷也必須接受一定程度的外部法律監督。
三、復議審查的可能性
(一)救濟空間
實在法規范為這個問題上留下了一定的制度空間:首先,申請工傷認定時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并沒有規定必須是肯定性的結論報告,《工傷認定辦法》第5條第1款第2項只是規定:“(二)醫療機構出具的受傷后診斷證明書或者職業病診斷證明書(或者職業病診斷鑒定書)。”
其次,《工傷認定辦法》第9條的規定更加重要:“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在進行工傷認定時,對申請人提供的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或者職業病診斷鑒定書,不再進行調查核實。職業病診斷證明書或者職業病診斷鑒定書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格式和要求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可以要求出具證據部門重新提供。”
這說明,在受理工傷認定時,法律規定勞保部門必須進行一個類似于審查的判斷過程,即要考慮職業病診斷證明書是否“符合國家有關規定”。這里的國家規定,應該是指《職業病防治法》、《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以及《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等相關法律程序方面的規定。
基于上述理由,實在法制度實際上沒有關閉對職業病診斷的救濟通道,只是勞動保障部門沒有發現它自身在這個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工傷認定辦法》第9-14條明確規定了勞保部門的調查職權,負責工傷認定的勞保部門應充分承擔起法律寄予他的職責。勞保部門不是專家意見在機械意義上的執行機構,而是代表行政權力對醫學權威意見進行第一輪法律適用的“重要的”執法機構。在這個意義上,勞動保障部門有義務受理否定性的診斷鑒定結論,從而利用法定職權針對不合法的診斷活動要求醫療機構重新作出新的判斷,甚至可以追究相關主體的法律責任。相應的,如果像盧先明這樣的申請人有足夠的證據表明醫療機構或專家委員會在鑒定過程中有違法情形的,而勞動保障部門因否定性的鑒定結論又拒絕受理其工傷認定申請,那么申請人可以因勞保部門拒絕受理工傷認定申請為由提出復議申請。
所以,利用復議程序“全面審查”的原則,職業病診斷可以在復議中得到間接的法律審查,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并不違背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形式要求,同時也有利于行政法治可接受性的法律內涵。
(二)復議的受案范圍
我國立法經驗傾向于用受案范圍這個概念,來說明復議申請人的范圍問題。但是受案范圍的核心依然是復議申請權,只不過“受案范圍”在實踐中顯得更加直觀,進而對復議機關正確認識申請人的范圍起到積極的幫助作用。
首先,受案范圍是指哪些案件可以受理。根據救濟的被動性原理,非經法定申請,行政復議機關無法直接審查任何一個屬于受案范圍的行政行為。復議審查是法定救濟程序,因而實體請求權的客觀存在是受理的真正前提,受案范圍起到的只是輔助作用;如果沒有申請權作支撐,僅從受案范圍出發就能決定是否受理案件的話,復議程序實質上就與廣義的行政監督沒有區別了。
因此,行政復議機關受理某一案件的唯一標準是申請人是否適格,只不過,受案范圍將行政行為的類型化特征予以概括,因此對行政復議機關作出正確決定起到了幫助作用。正如我國《行政復議法》第6條第1款前十項的規定中,描述受案范圍的行為特征時頻頻出現“不服”、“合法權益”、“沒有依法”等字樣,以及第十項的兜底條款:“認為行政機關的其他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這都說明,侵犯合法權益所發生的實體請求權才是復議申請應被受理的法律前提。
其次,可以將“職業病診斷”這一類與個體權利密切相關,但在實踐中又很難正確發現受理渠道的重要問題,在不違背相關法律內涵的前提下,用提示性的規范話語將其納入到受案范圍中來。因為立法規定受案范圍的用意,是讓它借助對行政行為的特征化描述,為行政復議機關更好的認識申請人資格提供一種便于操作的方法,進而對復議申請權內涵起到間接的說明和補充效果。因為復議申請權的概括往往比較簡要,尤其當行政法上的權利與其他權利之間的關系需要通過一定的法律解釋得到界定時,與復議申請權相對應的實體權利在具體案件中就無法被直觀的認識到,導致行政復議機關可能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
因此,根據我國實在法有關受案范圍的一般話語形式,似乎可以對職業病診斷一類問題作一個大膽的假設性規定:“……認為主管部門因不當采納證明、鑒定、勘驗等性質的行政事實性結論而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依照本法申請行政復議”。
注釋: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第2條
②[德]漢斯.J.沃爾夫,奧拓.巴霍夫,羅爾夫.施托貝爾:《行政法》(第二卷),高家偉(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