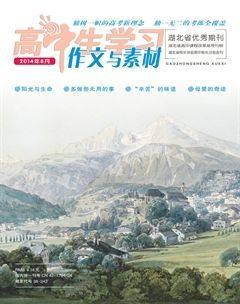劉慈欣:生活在平行宇宙中
吳虹飛
劉慈欣的身體里住著另外一個劉慈欣。
乍一看,他平淡無奇:短發,圓臉,和和氣氣,茶色眼鏡后面的眼神軟軟的,近似于無的淡眉毛像某種行動緩慢的海洋魚類,完全不同于他在寫作中透露出來的冷峻。
就是這樣一個看似普通的男人,被認為“創造了中國科幻文學界的里程碑”,這里指的是他最負盛名的“三體”系列科幻小說。而讓劉慈欣引以為傲的作品當然不止“三體”,《鄉村教師》《流浪地球》《朝聞道》《球狀閃電》《超新星紀元》……許多資深讀者對他短篇作品的喜愛,不亞于規模磅礴的長篇。
“三體”之后,劉慈欣的知名度漸漸擴散至整個華人世界。影視圈的人也開始和劉慈欣密切接觸。據悉,他的小說《鄉村教師》和《球狀閃電》都有望改編成電影劇本,登上大銀幕。而這也正是劉慈欣和無數讀者多年來夢寐以求的事情。
劉慈欣代表的是一種樸素的力量,在俗世中默默浮起。
寫作的秘密花園
如今的劉慈欣仍然只是娘子關發電廠一名毫不起眼的電腦工程師。有一次,他的某個同事對他說:“劉慈欣,我在網上看到有個寫科幻小說的人很火,他的名字竟然也叫劉慈欣。”
劉慈欣老老實實,聲稱自己只是個“科幻迷”,坦白自己不知道誰是巴赫金。中國的科幻作家里,能把科幻小說寫到世界大師級水平的寥寥無幾,他是其中之一,連續拿了八年的銀河獎——中國科幻文學的最高獎,“三體”的銷量超過15萬,是國內近20年來最暢銷的科幻小說。但他在發電廠的領導和同事仍然一無所知。
這些年他一直在默默地深思,默默地看書,默默地寫書,默默地卡殼,默默地寫完,和80年代中后期中國科幻小說低谷時的地下創作沒有太大差別。只是現在寫完之后,可以放心大膽地發表出來,讓越來越多的陌生人讀到,作品也越來越值錢。在網絡上,成千上萬的讀者把他尊稱為“大劉”,儼然自成一派。
許多沒有見過劉慈欣肖像的讀者,會自動在心中勾勒出另外一個劉慈欣的形象:堅硬,剛毅,棱角分明,不卑不亢,富有柔情,甚至可能有點英俊。而他本人看上去只是一個有些木訥,不太和外界打交道的普通中年男人,過著和大多數中年男人雷同的平淡生活。忙的時候連續幾天加班,不忙的時候就在辦公室里閑坐著。寫作的時間也都是零零碎碎拼湊起來的。上班時,手頭的事情忙完,他不愛串辦公室聊天,就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開始不動聲色地寫作。晚上回到家繼續寫,每天都要寫出三四千字。
在這個世界里,他生活簡單,形象模糊,容易被人遺忘。有時候出席大型場合,也會衣著樸素地上臺發言,笑起來有些理工男特有的羞怯。對于生活,他有自己的“奢望”:“錢多到不用工作,時間多到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想在哪兒待多久就待多久。”
娘子關發電廠的工作,對他來說“意味著穩定的收入來源,意味著與社會接觸的窗口”。而科幻,是他在四下無人時縱情游樂的秘密花園,那些數萬光年之外的星塵,是秘密花園里肆意生長的野薔薇。
硬科幻的代表
上世紀60年代,劉慈欣生于北京,在山西陽泉長大。1988年從華北水利水電學院畢業后,進入山西娘子關發電廠任計算機工程師。1999年開始創作科幻小說,被眾多讀者推為硬科幻派小說家。
讓人意外的是,作為一個硬科幻派小說家,他的知識攝入渠道居然主要是靠看書。他不認識什么科學家,離科研圈子也很遠。劉慈欣喜歡去人跡罕至的地方旅行,但機會不多。“幾年前,曾同一群科幻作家一起到過一個神奇的城市——康定,印象最深的就是穿過城市的那條河,我第一次看到那樣湍急而又清澈的河,特別是在夜里,那條河仿佛是穿過城市的夢境。”
最多的旅行機會是去參加各種科幻筆會。他念念不忘1999年參加的科幻筆會,那是他第一次與科幻界接觸。“到了科協招待所已是深夜,看到服務臺前有一對少男少女,男孩兒的英俊和女孩的美麗幾乎是我從未見過的,仿佛是從神話中走出來的人物。直到今天,當年參加筆會的作者都模糊了,但那對深夜中遇到的少男少女還在我的記憶中栩栩如生,幾乎成了科幻的化身。”劉慈欣是愛美的。他對美的感受更多來自于永恒的、漫長的、浩大的事物,比如宇宙和時間,誕生與滅亡。這些是他生命里最大的迷戀。影響他最深的科幻作家,是英國的阿瑟·克拉克,《2001,太空奧德賽》和《與拉瑪相會》,從1980年初次接觸后,成為他心中永遠的科幻圣經。他沉湎于那種跨越數萬光年的美感,而宏大敘事的冷酷和唯美,也由此成為他的科幻作品最大的特質。
孤獨地面對宇宙的神秘
和同輩科幻作家韓松的邪異文風相比,劉慈欣的寫作路數樸實得多。《科幻世界》雜志前主編阿來曾經如此評價劉慈欣的小說:“《鄉村教師》在劉慈欣的作品中,是給予現實強烈關注的一部。它講的是明明白白的故事,說的都是人話。”的確,他的幾乎每一部作品,都以最日常、最普通的凡夫俗子入手,而又多多少少帶有自己生活經歷的影子。對《地火》里的礦工子弟——劉慈欣把小說的主人公命名為劉欣,他如此寫道:“劉欣恍惚著拿起父親的飯盒,走出家門,在1978年冬天的寒風中向礦上走去,向父親的二號井走去,他看到了黑黑的井口,好像有一只眼睛看著他。”劉慈欣的父親以前就在北京的煤炭探討院工作,后來下放去了山西。作為在山西長大的孩子,他小時候常給井下的父親送飯。
劉慈欣雖然被看成是“技術主義者”,每一部作品,不管是長篇還是短篇,都有著極其冷靜的思維和整齊嚴謹的外觀,像一架結構堅固的機器,清楚而精準。但讀下去,又總能讓人感受到一種分外柔軟的東西,像他的外表,柔和而略帶羞怯的微笑。
他的同行,著名科幻作家韓松如此評價他:“劉慈欣的作品中,滲透了一股對宇宙的敬畏。他寫一些技術味道很濃的科幻,但是,后面的東西,骨子里的東西,其實是形而上的。也就是有一種哲學上的意味,宗教上的意味。劉慈欣總是在悲天憫人,而且是一種大悲大憫,像佛陀。”
在劉慈欣看來,他只是勤勤勉勉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他生活簡單,白天上班,晚上寫作。在那個偏遠的小城里,連電影院也沒有,空閑的時候,他就在網上看電影——如果沒有互聯網,他的生活就仿若停留在80年代一般。
科幻小說對于劉慈欣來說,是精神上的一根脊梁,無法從生活中抽去。即使在科幻小說最艱難的80年代中后期,他仍然堅持地下寫作,那是他生命中噩夢一般的時期。而十多年后,時來運行,伴隨著女兒的出生長大,他的小說也開始陸續面世,并連續拿下科幻屆的最高獎項銀河獎,直到如今“三體”三部曲的大紅大紫。生活對他來說一切依舊。頂多是簽售會變多了,可以去更多的地方旅行了,手也會更累些。
“如果有一天你停止寫小說,你會干什么?”劉慈欣說:“哦,不會有那一天的。”
劉慈欣依然清晰記得,1981年的那個冬夜,看完了阿瑟·克拉克的小說《2001,太空奧德賽》,他走出家門,一抬頭就是深邃無垠的星空。“突然感覺周圍的一切都消失了,壯麗的星空下,只有我一個人站著,孤獨地面對這人類頭腦無法把握的巨大神秘……”
(轉載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