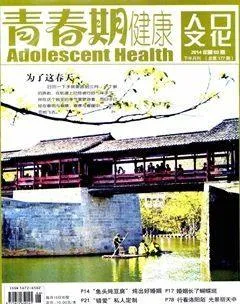青銅時(shí)代,文明的初成
落墨
厚重堅(jiān)實(shí)的金屬質(zhì)地,似在發(fā)出琤琮的鳴響;雄渾古拙的造型設(shè)計(jì),飾以神秘、獰厲、兇狠的抽象紋理,在陰濕的地底沉睡了千年之后,終于有一天,它們連同那個(gè)地底的王朝得以重見(jiàn)天日,一個(gè)個(gè)歷史的謎底也隨之揭開(kāi)。雖然光澤不再,但那由內(nèi)而外散發(fā)的沉著、肅穆,使它們看起來(lái)依然像一個(gè)權(quán)威,獨(dú)領(lǐng)一尊。這或許就是歷史的力量。
許多民族的藝術(shù)品從表面上看,似乎僅僅是在形式上具有裝飾意味,但其實(shí)不然。物質(zhì)文明是一種文化發(fā)展程度的外在體現(xiàn)。從早期華夏民族陶器上的幾何紋飾開(kāi)始,由色彩和線條所打造的這一審美樣式,就成為原始氏族圖騰崇拜或其他崇拜的標(biāo)志。
青銅藝術(shù)品作為民族共同體的物質(zhì)文化的一部分,自然地表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生活及人們的意識(shí)形態(tài),所以,它不單純是具有裝飾性的形式,還是“有意味的形式”。《史記·封禪書》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說(shuō)禹分天下為九個(gè)州,然后集中各地的銅料,鑄成九鼎以象征國(guó)家范圍。三代青銅禮器的功用歸納起來(lái)不外乎祭祀、征戰(zhàn)、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等。祭祀與征戰(zhàn)是當(dāng)時(shí)國(guó)家的要事,所謂:“國(guó)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以鼎為代表的青銅器是祭器、禮器、吉器,亦是國(guó)家權(quán)力的象征。《左傳·宣公三年》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yuǎn)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xié)于上下,以承天休。”更將青銅器的作用說(shuō)得神乎其神。
青銅時(shí)代,是青銅器在社會(huì)生活中處于中心地位的時(shí)期。在中國(guó),青銅器的出現(xiàn)比青銅時(shí)代略早,而這一不同凡響的藝術(shù)品從生活舞臺(tái)的退出,注定會(huì)有一個(gè)長(zhǎng)長(zhǎng)的尾聲。公元前500年前后鐵器出現(xiàn),青銅器逐漸式微,但應(yīng)用依然是極為廣泛的;秦統(tǒng)一六國(guó),建立中國(guó)歷史上第一個(gè)統(tǒng)一的封建王朝,青銅依然作為兵器而被大量使用,秦兵馬俑坑發(fā)掘的銅車馬和大量青銅兵器就是很好的證明。秦以后,青銅器才算是正式退出了歷史舞臺(tái)。這一場(chǎng)華麗現(xiàn)身,不覺(jué)就是一千五百年。
青銅時(shí)代的發(fā)現(xiàn)和歷史意義
夏、商、周是古代文獻(xiàn)中記載的中國(guó)最早的三個(gè)王朝,這是今天的人們普遍了解的一個(gè)基本的歷史常識(shí),但夏朝究竟是否存在,曾是一個(gè)頗有爭(zhēng)議的話題,這一爭(zhēng)論,隨著一項(xiàng)考古大發(fā)現(xiàn)才有了結(jié)論,這就是河南偃師二里頭村遺址的發(fā)現(xiàn)。可以說(shuō),青銅時(shí)代的考證,將我們對(duì)中國(guó)歷史的了解造成了基本性的改變。
1959年夏,現(xiàn)代著名史學(xué)家、中國(guó)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豫西展開(kāi)調(diào)查,不久在河南偃師境內(nèi)洛水南岸的二里頭村南發(fā)現(xiàn)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遺跡。這里有大面積的宮殿建筑基址群和宮城城垣,以及縱橫交錯(cuò)的道路系統(tǒng),并發(fā)掘了大型宮殿建筑基址數(shù)座,大型青銅冶鑄作坊遺址一處,綠松石器制造作坊1處,制陶、制骨有關(guān)的遺跡若干處,宗教祭祀有關(guān)的建筑遺跡若干處,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青銅禮器和玉器的貴族墓葬,以及大量的陶、石、骨、蚌、銅、玉、漆器和鑄銅陶范等遺物。夏墟的發(fā)現(xiàn)是這次調(diào)查中最重要的收獲,引起了中國(guó)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的重視,并先后派出考察隊(duì)赴河南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發(fā)掘。
二里頭遺址被認(rèn)為是具有中國(guó)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wǎng)、最早的宮城、最早的具有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筑基址群和宮城城垣;中國(guó)最早的青銅器冶鑄作坊和綠松石器作坊、最早的青銅禮器群、最早的青銅兵器;是公元前二千年前半葉中國(guó)最大的聚落,同時(shí)也是中國(guó)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guī)劃的大型都邑遺址,等等。
另外,青銅器的存在,為我們了解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階層分化提供了一定的線索。二里頭遺址區(qū)還有大量的石器和石質(zhì)農(nóng)具,說(shuō)明我國(guó)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標(biāo)志,在整個(gè)青銅時(shí)代,金屬始終不是制造生產(chǎn)工具的主要原料,而石、木、角、骨才是。再者,生鐵適于大量制造且比較便宜,所以,隨著手工業(yè)的發(fā)展,鐵器逐漸取代了青銅器的地位,在社會(huì)生活中被廣泛應(yīng)用。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lái)看,由于生產(chǎn)成本較大,青銅器的使用主要是貴族和王室,普通家庭是不允許使用的,這使得青銅器在當(dāng)時(shí)必然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征,用青銅器做器皿、儲(chǔ)物、照明等日常生活用具應(yīng)該是貴族才享有的權(quán)利,一般百姓用的多為粗制的陶器。
青銅器與三代文明的傳承
關(guān)于三代政權(quán)形成的歷史,首先值得關(guān)注的一個(gè)現(xiàn)象便是都城的選址問(wèn)題。夏墟與殷墟的城邑遺址,都具備以下要素:夯土城墻、戰(zhàn)車、兵器;宮殿、宗廟與陵寢;祭祀法器與祭祀遺跡;手工業(yè)作坊;聚落布局在定向與規(guī)劃上的規(guī)則性,等等。從這些考古遺存中可以推斷,城邑在當(dāng)時(shí)是維護(hù)政治統(tǒng)治和社會(huì)管理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尤其中國(guó)初期的城市,并不是經(jīng)濟(jì)起飛的產(chǎn)物,而是政治領(lǐng)域的工具。城邑同時(shí)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一堵城墻,不僅僅劃分出人們的行動(dòng)范圍,城里城外,更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生活方式,權(quán)利和義務(wù)的分離。所以,城邑的出現(xiàn)表明了早期文明的階級(jí)屬性,也是國(guó)家出現(xiàn)的標(biāo)志。
如果說(shuō)一般的城邑是文明社會(huì)的一個(gè)符號(hào),那么都城就是權(quán)力的象征,它的確立必然關(guān)乎一個(gè)王朝的百年基業(yè)。考古發(fā)現(xiàn),三代都城在歷史上屢有遷徙,夏朝歷470年,共傳十四代,十七個(gè)帝王,累計(jì)遷都十多次。商族以湯居亳(今豫西偃師)為界,前八后五,立國(guó)后五遷六都,止于盤庚遷殷(今豫北安陽(yáng))。西周自太王至平王,遷都五次。三代國(guó)號(hào)皆本于地名,雖屢次遷都,但最早的都城卻一直保持著祭儀上的崇高地位。
在生產(chǎn)工具、交通運(yùn)輸不發(fā)達(dá)的古代,遷都所耗費(fèi)的人力、物力、財(cái)力甚至要大于重建一座都城。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們頻繁遷都?又是什么因素影響著新都的選址?
古代帝王不惜血本,頻繁遷都,實(shí)際上是出于一種戰(zhàn)略眼光,在內(nèi)憂外患之際,開(kāi)辟一番新天地以圖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以平王東遷為例,宣王末年,西北關(guān)中一帶連年干旱,洛、涇、渭三川都干涸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受到了嚴(yán)重的影響;同時(shí),岐山一帶又發(fā)生了地震和地崩災(zāi)害,鎬京在地震中受損;再者,鎬京接近戎、狄等外患。有趣的是,夏代崛起于晉南,商代自東向西,周代自西向東,最終也都落腳在豫西和晉南一帶。經(jīng)考證,三代選址的依據(jù)很可能是青銅礦源,因?yàn)殂~礦和錫礦是三代鞏固其實(shí)力的政治資本。沒(méi)有銅錫礦,三代就沒(méi)有青銅器;沒(méi)有青銅兵器,就打不到天下;沒(méi)有青銅禮器,就無(wú)法治理天下……夏代都城的分布區(qū)與銅錫礦的分布幾乎完全吻合,商代的遷徙路徑也便于采礦,而山西境內(nèi)銅錫礦較少,這應(yīng)該也是迫使周代向東遷徙的一個(gè)原因。三代銅、錫礦點(diǎn)集中于華北平原邊緣山地,以晉南、豫北為中心,這些礦產(chǎn)都較稀薄,以三代采礦量之大,每個(gè)礦產(chǎn)地維持的出礦時(shí)間是非常有限的,需隨時(shí)尋求新礦。
青銅器的較廣泛應(yīng)用始于夏,盛于商周。三代都屬于城邑式的宗族統(tǒng)治機(jī)構(gòu),以姓族治天下,夏代為姒姓王朝,商代子姓,周代姬姓,繼統(tǒng)相似,都建立了城郭,貴族分封制邑。總之,三代在文化上一脈相承,而以青銅器為文明的特征。
青銅器動(dòng)物紋樣的時(shí)代內(nèi)涵
青銅器上的不同動(dòng)物紋應(yīng)是以之為崇拜物的不同部族的象征,其在青銅器上的裝飾位置反映了相應(yīng)部族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地位。隨著部族的地位不斷變化,青銅紋飾也隨之變遷。商周青銅紋飾大致可分為三大類,即獸面紋、夔龍紋、神鳥(niǎo)紋。
獸面紋
獸面紋,一般是以動(dòng)物頭部的正面形象為主體,輔以軀干、羽翼、足爪等部位的一種紋飾。其中,頭部在獸面紋中占據(jù)著十分突出的地位,不僅頭部的比例遠(yuǎn)大于軀干、羽翼和足爪,而且有的獸面紋或難以分辨輔助部位,或軀干“有首無(wú)身”。
一個(gè)完整的獸面紋,應(yīng)包括鼻、額、眼、眉、角、耳、口、牙、身、尾、羽、翼、足、爪等部位。獸面紋的核心要素是其眼、角(或代替角的耳)、口。眼和口的形式比較固定(眼分為回字目和臣字目,口分為嘴角內(nèi)勾和外撇),唯有角(或耳)變化十分豐富,因此角(或耳)就成為區(qū)分獸面紋最重要的標(biāo)志。根據(jù)角(或耳)的形狀,可分為牛角類、羊角類、豕角類、變形類等。
獸面紋是商、周青銅器紋飾中地位最顯赫、含義最神秘、結(jié)構(gòu)最成熟的紋飾。主要出現(xiàn)在鼎、簋、尊、方彝、罍、爵、壺、觥等主要青銅器類別的顯著部位,其中與鼎關(guān)系最為密切。雙目炯炯,睥睨天下;雙角凜凜,唯我獨(dú)尊。與之同時(shí)代的其他紋飾幾乎總是作為它的陪襯和附屬。
“獸面紋”的原型是牛、羊、豬等祭祀牲畜。它作為一種祭品的象征,雄踞在青銅禮器上,同時(shí)也作為盛放牲畜祭品的禮器,享受著人們的祭拜——既是奉獻(xiàn)的牲犧,又是受祭的對(duì)象。祭祀在古代是一件很嚴(yán)肅的事,尤其三代時(shí)期,制定了嚴(yán)格的規(guī)制。受到祭祀的天帝或祖先不但在人間有他們的“辦事處”,即帝廷,也就是后來(lái)說(shuō)的“太廟”,還有一個(gè)人間的“代理人”,也就是人王,他們代替神靈和祖先享受人間的祭祀,傾聽(tīng)人們的祈愿,再轉(zhuǎn)達(dá)給天帝。由于對(duì)神靈懷有敬畏之心,人王對(duì)天帝有所請(qǐng)求時(shí),絕不直接祭祀于上帝,而以廷正為祭祀的媒介,以故世的先王為“中間人”,再由先祖轉(zhuǎn)達(dá)。這些在今天看來(lái)有些不可思議,但當(dāng)時(shí)的人們是很認(rèn)真履行的。
商代是獸面紋最發(fā)達(dá)的時(shí)期,數(shù)量眾多,型式繁雜,分布地域廣,且流行于整個(gè)商代;西周早期仍可見(jiàn)大量獸面紋,但至中期其地位被鳳鳥(niǎo)紋取代。因此,獸面紋所代表的信仰和崇拜體系與商代具有最密切的聯(lián)系。
夔龍紋
夔龍紋在商、周青銅器紋飾中,群體數(shù)量最龐大、型式演變最復(fù)雜、流行時(shí)間最長(zhǎng)久,自宋代王黼《宣和博古圖》以來(lái)一直被冠以“夔紋”之名。這一命名源于“夔一足”的傳述,由于《莊子·秋水》《莊子·達(dá)生》《國(guó)語(yǔ)·魯語(yǔ)下》《山海經(jīng)·大荒東經(jīng)》《山海經(jīng)·中山經(jīng)》和《說(shuō)文解字·文部》對(duì)夔的描述都是有“一足”,因此宋代學(xué)者據(jù)此將青銅器上廣泛存在的側(cè)視一足的動(dòng)物紋及相似紋飾統(tǒng)稱為“夔紋”。即使《呂氏春秋·慎行論·察傳》和《韓非子·外儲(chǔ)說(shuō)左》辨“夔一足”為“得一夔而足”之意,即有一夔就足夠了,非“夔有一只足”,這種動(dòng)物紋飾畢竟有了一個(gè)名字,那它何嘗不是一個(gè)“美麗的誤解”?
夔紋往往混有少量其他紋飾,而大多數(shù)“真正的夔紋”則與甲骨文和金文中保留了的各形“龍”字十分相似。這部分“夔紋”及數(shù)量較少、型式單一的公認(rèn)“龍紋”,是由遠(yuǎn)古時(shí)代龍的雛形到秦漢以后“三停九似”的標(biāo)準(zhǔn)龍形的過(guò)渡。鑒于以上因素,就將這一時(shí)期青銅器上的“夔紋”和龍紋統(tǒng)稱為“夔龍紋”。
作為“四靈”之一的“龍”的起源,可追溯至距今八千年前今遼寧西部的某些遺存,隨后的三千年間,許多地方又陸續(xù)出現(xiàn)了龍的蹤跡,雖然它們大小懸殊,形態(tài)各異,但普遍具有后世龍形一脈相承的特征(如蛇身、有角、有鱗等),因此被視為龍的雛形。龍的造型為動(dòng)物體的集合,曾為許多原始部落的圖騰,這與原始氏族合并成為部落聯(lián)盟有關(guān)。各氏族原有的圖騰各取一部分整合為新的復(fù)合體,充當(dāng)帶有圖騰性質(zhì)的象征物。這種移植而成、現(xiàn)實(shí)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形象,更能使人產(chǎn)生恐懼和敬畏。《管子·水地》:“龍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欲大則藏于天下,欲上則凌于云氣,欲下則入于深泉,變化無(wú)日,上下無(wú)時(shí)。”《說(shuō)文解字》有釋:“龍,鱗蟲之長(zhǎng),能幽能明,能細(xì)能巨,能短能長(zhǎng)。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青銅時(shí)代,龍文化進(jìn)入一個(gè)爆發(fā)時(shí)期,在數(shù)量和類型上都急劇增長(zhǎng),成為當(dāng)時(shí)最活躍的形象,因而歷代青銅器上的龍紋樣式都不統(tǒng)一,且與熟悉的秦漢以后定型的龍的形象有較大差距,以至于后世人們?cè)俅我?jiàn)到時(shí)已經(jīng)認(rèn)不出了。宋代王黼《宣和博古圖》中根據(jù)部分紋飾從側(cè)面看有一足而將其統(tǒng)統(tǒng)稱為“夔紋”,實(shí)際上它們就是“龍紋”。
在二里頭遺址的陶片上發(fā)現(xiàn)了兩種比較成熟的龍紋,而有關(guān)文獻(xiàn)也提到“夏人崇龍”。《列子·黃帝》:“夏后氏蛇身人面。”《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以龍勺。”可以肯定龍與夏族的關(guān)系,但龍與商族的聯(lián)系沒(méi)有那么密切,因?yàn)樵谏坛y(tǒng)治的核心區(qū)域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很少的龍紋型,且這種紋飾在商代早期青銅器上普遍居于從屬和陪襯地位,很少作為主體紋飾裝飾于器物的顯著部位,一般都出現(xiàn)在鼎、壺、罍等禮器的口沿下、圈足上。所以龍紋可能并不是商文化固有的紋飾,龍也可能并不是商族傳統(tǒng)的主神靈。周代龍的地位略有提高,作為主體紋飾裝飾于器蓋和器腹的夔龍紋型式與數(shù)量均明顯增加,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周族與夏族關(guān)系較為密切。文獻(xiàn)記載,周人常以夏的繼承者自居,如《詩(shī)經(jīng)·魯頌·閟宮》“赫赫姜……是生后稷……奄有下土,纘禹之緒。”但西周早期青銅器上的夔龍紋的地位仍不及獸面紋;而西周中期獸面紋衰落后,夔龍紋的地位又不如大量新興的鳳鳥(niǎo)紋突出。
神鳥(niǎo)紋
神鳥(niǎo)紋是一種流行于商至西周早期的、鳥(niǎo)首獸身的變形鳥(niǎo)紋。商代及西周早期,青銅器上流行一種鳥(niǎo)首獸身的變形鳥(niǎo)紋,到西周中期以后,一種鳥(niǎo)首鳥(niǎo)身的“寫實(shí)”鳥(niǎo)紋開(kāi)始流行。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勾喙和羽翼,其中勾喙為第一特征,部分神鳥(niǎo)紋并無(wú)明顯的羽翼。”它或許是與商族關(guān)系密切的“玄鳥(niǎo)”形象。《詩(shī)經(jīng)·商頌·玄鳥(niǎo)》:“天命玄鳥(niǎo),降而生商。”
但玄鳥(niǎo)紋作為商族的象征,在商代青銅器飾紋中并未占據(jù)最突出的地位,商代青銅器上最發(fā)達(dá)、最引人注目的紋飾是獸面紋,它始終占據(jù)著商代重要青銅禮器的顯著部位,而玄鳥(niǎo)紋大多處于從屬地位,只是一個(gè)陪襯。
玄鳥(niǎo)紋在入周后被鳳鳥(niǎo)紋代替,鳳鳥(niǎo)紋廣泛飾于鼎、簋、尊等青銅類別的較顯著位置,應(yīng)為周人崇拜的神靈,所謂“鳳鳴岐山”,《國(guó)語(yǔ)·周語(yǔ)上》也說(shuō),“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鸑鷟,鳳屬的神鳥(niǎo)。早期鳳的形象與現(xiàn)在不同,而是與龍類似的飛禽走獸的復(fù)合體。中國(guó)古代典籍《天老》中記載:“鳳之象也,麟前鹿后,蛇頭魚尾,龍文龜背,燕頜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guó),翱翔四海之外,過(guò)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fēng)穴,見(jiàn)則天下大安寧。”其性格高潔,非晨露不飲,非嫩竹不食,非千年梧桐不棲。相傳鳳集香木自焚,然后從火焰中重生,美艷非常,所以,人們又稱鳳為不死鳥(niǎo)。自從傳說(shuō)中周始祖后稷被棄寒冰之上,鳥(niǎo)用翅膀?yàn)槠涓采w供暖后,鳥(niǎo)就與周人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加之有這樣神異的傳說(shuō),鳳自然而然成為了部落集團(tuán)的圖騰性質(zhì)的象征物。
青銅器動(dòng)物紋樣是三代政治、宗教、藝術(shù)的重要結(jié)合點(diǎn)。有了青銅器,三代帝王在占據(jù)豐富的自然資源之外,又掌握了可以匯通天帝的祭祀工具,上可以通神靈,下可以御萬(wàn)物。
夏商周作為部落聯(lián)盟,都有各自的文化,然而“三十年河?xùn)|,三十年河西”,隨著歷史的變遷,三者的政治勢(shì)力此消彼長(zhǎng),才呈現(xiàn)出一種政權(quán)更迭、文明承繼的狀態(tài)。從發(fā)現(xiàn)的三代遺存來(lái)看,在商朝時(shí)期,周族的文化發(fā)展程度不亞于商族。青銅時(shí)代,是夏、商、周王朝形成的時(shí)代,是中國(guó)許多文物制度的奠基時(shí)代。
作為三代文化集中表現(xiàn)的青銅器,還有待我們進(jìn)一步深入了解。由于歷史的機(jī)緣,在特定的年代里,青銅器只屬于特定人群,并且與祭祀、戰(zhàn)爭(zhēng)相遇,它注定是那么高高在上、富有權(quán)威、讓人顫栗和難以接近,而作為單純的藝術(shù)品來(lái)說(shuō),誰(shuí)能肯定,隨著時(shí)代的流變,新元素的出現(xiàn),以及人們對(duì)美的訴求的改變,青銅器不會(huì)再以另一種面貌出現(xiàn)在我們的生活中,帶給我們美的享受呢?
(編輯 劉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