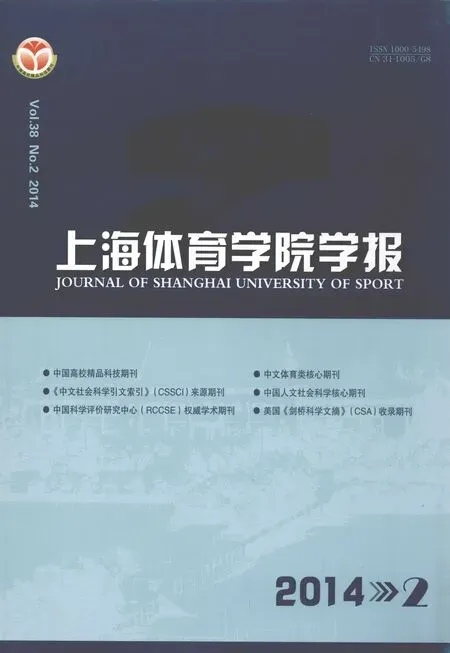想象的共同體:跨境族群儀式性民俗體育的人類學(xué)闡釋
---基于傣族村寨“馬鹿舞”的田野調(diào)查
楊海晨, 王 斌, 胡小明, 沈柳紅, 趙 芳
(1.華中師范大學(xué)體育學(xué)院,湖北武漢430079;2.華南師范大學(xué)體育科學(xué)學(xué)院,廣東廣州510631;3.玉林師范學(xué)院體育學(xué)院,廣西玉林537000;4.廣西師范大學(xué)體育學(xué)院,廣西桂林541004)
想象的共同體:跨境族群儀式性民俗體育的人類學(xué)闡釋
---基于傣族村寨“馬鹿舞”的田野調(diào)查
楊海晨1, 王 斌1, 胡小明2, 沈柳紅3, 趙 芳4
(1.華中師范大學(xué)體育學(xué)院,湖北武漢430079;2.華南師范大學(xué)體育科學(xué)學(xué)院,廣東廣州510631;3.玉林師范學(xué)院體育學(xué)院,廣西玉林537000;4.廣西師范大學(xué)體育學(xué)院,廣西桂林541004)
采用田野調(diào)查法,從文化人類學(xué)的視野出發(fā),對云南省孟連縣傣族村寨的儀式性民俗體育活動“馬鹿舞”進(jìn)行研究。通過對馬鹿舞的儀式過程及其文化生態(tài)的參與感知、深度訪談后認(rèn)為:關(guān)于馬鹿舞起源的民間傳說,“原型”或“母題”應(yīng)來自傣族社會的生活環(huán)境和宗教信仰;馬鹿舞的跨境傳承、傳播與傣族社會歷史變遷中重大事件相對應(yīng);擁有想象的共同體是儀式性民俗體育活動得以傳承與傳播的重要原因。
想象的共同體;跨境族群;儀式性民俗體育;馬鹿舞;傣族村寨
Author's address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2.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Guangdong,China;3.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Yulin Normal University,Yulin 537000,Guangxi,China;4.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Guangxi,China
在中國漫長的邊境沿線及其毗鄰的周邊國家之間,世代居住著眾多跨境族群,其中僅云南就有傣、哈尼、壯、拉祜等16個(gè)民族跨境而居。盡管這些族群生活于不同的政治語境中,但他們在親緣、地緣、業(yè)緣、物緣、神緣、語緣[1]影響下,激發(fā)了多邊文化交流和互動的內(nèi)在動力。因其憑借這諸多的文化紐帶進(jìn)行的跨國流動和信息交換較為便利,由此在族群文化演進(jìn)中形成了區(qū)別于其他世居族群的特有文化模式。鑒于跨境族群文化的特殊性,在著力構(gòu)筑中國-東盟自由貿(mào)易區(qū)的國際環(huán)境中,人類學(xué)者有必要深入研究這些跨境族群的文化生態(tài)所蘊(yùn)含的豐富意義,這對促進(jìn)東南亞不同地域間族群理解同源及異源文化,促成和諧共生的周邊文化生態(tài),在現(xiàn)實(shí)與學(xué)術(shù)層面均具有積極意義。
前人對跨境族群的研究或側(cè)重于對某一族群歷史淵源和遷徙等方面的考證,或在宏觀視野下關(guān)注跨境族群的族群認(rèn)同、國家認(rèn)同等。在體育領(lǐng)域,基于人類學(xué)的宏觀視野,從某一具體的跨境族群所參與的身體運(yùn)動入手,探討身體運(yùn)動文化在傳承與傳播上的共時(shí)狀態(tài)、歷時(shí)過程等,并且以此提升對東南亞文化圈相互理解的微觀個(gè)案研究鮮見。為此,筆者借助參加“2012年云南大學(xué)民族學(xué)和人類學(xué)研究生暑期研修與田野調(diào)查學(xué)校”學(xué)習(xí)的機(jī)會,與學(xué)習(xí)班的部分人員一起,對云南省孟連縣勐梭寨的傣族社會文化及傣族特有的跨境族群儀式性民俗體育活動---馬鹿舞(圖1)進(jìn)行專項(xiàng)性田野調(diào)查,期望借助對“馬鹿舞”這一“地方性知識”的闡釋,推論出關(guān)于跨境族群體育在傳播與傳承等問題上的一般性觀點(diǎn)。

圖1 馬鹿舞表演Figure 1. Performance of Malu Dance
1 中緬邊境的勐梭寨
“田野”是“人類學(xué)家以及人類學(xué)知識體系的基本構(gòu)成部分”[2],也是人類學(xué)研究任何人類問題的基礎(chǔ),優(yōu)秀的田野工作者應(yīng)力爭做到“成為當(dāng)?shù)厝松畹墓餐謸?dān)者和分享者”[3]42。由于運(yùn)用人類學(xué)理論對身體運(yùn)動的專項(xiàng)性研究與對傳統(tǒng)的初民社會(primitive society)的全景式研究在選取對象、關(guān)注內(nèi)容上等均不相同,因此當(dāng)前體育人類學(xué)較為流行的是采用“多次、短期、深度訪談式”的田野調(diào)查。其中,筆者及參加學(xué)習(xí)的人員于2012年7月18-26日主要就馬鹿舞的儀式展演過程、起源、傳承與傳播等進(jìn)行田野調(diào)查。隨后,筆者自2012年9月28日-10月7日對勐梭寨再次進(jìn)行田野調(diào)查,此次主要是在人類學(xué)整體觀理論下,采用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相結(jié)合的方法,從勐梭寨及傣族的地理環(huán)境、歷史傳統(tǒng)、生活方式、宗教民俗等方面進(jìn)行考察,并對上一次調(diào)查中存在的疑問進(jìn)行重復(fù)求證。在2次田野調(diào)查中,主要探訪了孟連縣文化館相關(guān)負(fù)責(zé)人、民間文學(xué)傳承人、多位勐梭寨馬鹿舞傳承人以及普通寨民,共計(jì)訪談50余人次,拍攝訪談及參與式觀察視頻約600 min。此外,為了彌補(bǔ)參與觀察不夠深入的缺陷,筆者還采用了文獻(xiàn)資料調(diào)研與深度訪談相結(jié)合的方法。
勐梭寨地處橫斷山脈南麓的瀾滄江流域,位于云南省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是該縣娜允鎮(zhèn)芒弄村下屬的一個(gè)傣族村寨。孟連縣地處中國西南邊陲,與緬甸第二特區(qū)撣邦接壤。勐梭寨位于孟連縣城郊東南,距縣城約2.5 km,距昆明市約660 km,距中緬邊界約40 km(圖2)。據(jù)該村已故老會計(jì)巖(音ái)依罕們(亦被稱為波葉嫩)用傣艮文撰寫的村史大事文本可知,現(xiàn)今的勐梭寨人是因害怕佤人獵頭,而在1938年從當(dāng)時(shí)西盟的“大勐梭”搬遷過來的。

圖2 孟連縣勐梭寨區(qū)位圖Figure 2. Map of Mengsuo Village of Menglian County
云南大部分傣族信奉南傳上座部佛教,筆者調(diào)查的孟連縣及勐梭寨傣族亦如此。為了日常佛事需要,當(dāng)?shù)馗鞣N佛寺隨處可見,幾乎每個(gè)下屬鄉(xiāng)鎮(zhèn)、村寨等均有小型佛寺,傣族社會稱之為“緬寺”。寨子里年齡較大的傣族人大都使用傣語,并能聽懂緬語及泰語,而對于漢語較為陌生。年齡較小者由于接受了漢語教育,大都能同時(shí)熟練運(yùn)用傣語和漢語進(jìn)行交流,并能聽懂部分緬語及泰語。勐梭寨傣族盡管與緬甸的撣族、泰國的泰族分別屬于不同的國家,族稱不同,但他們的居住地相連,有共同的民族特征,在語言使用、宗教信仰、族群認(rèn)同等方面與緬甸、泰國的相同族群能夠產(chǎn)生較強(qiáng)的共鳴。他們經(jīng)常活躍于國境兩側(cè),有史以來,探親、訪友、通婚、互市、過耕放牧、朝廟拜佛、節(jié)日聚會等傳統(tǒng)交往從未間斷。本次調(diào)查的馬鹿舞正是在這樣的跨境族群所在村落中進(jìn)行的。
2 跨越邊境的馬鹿舞
馬鹿舞是傣族民間在賧佛儀式時(shí)進(jìn)行展演的一種擬態(tài)道具舞。據(jù)經(jīng)常往來于中緬、中泰的勐梭寨村民介紹,在緬甸的撣族、泰國的泰族賧佛儀式中,也經(jīng)常會跳馬鹿舞。馬鹿道具現(xiàn)在大都用竹及藤條編制骨架,彩布縫制外殼,再配上精雕細(xì)刻的木制鹿頭。表演的馬鹿一般為雙數(shù),且為一公配一母,但公母在動作及顏色上沒有嚴(yán)格的區(qū)分。表演時(shí),在傣族傳統(tǒng)的象腳鼓、排铓、镲等樂器伴奏下,每具道具由2名男性鉆進(jìn)鹿身,一人為頭,一人為尾,鹿頭由前面一人用一只手緊貼耳部高舉過頭進(jìn)行控制,鹿尾則俯身在后予以配合(類似舞獅)表演。
2.1 馬鹿舞儀式過程的人類學(xué)解讀 胡小明等[4]認(rèn)為,參與性感知能夠?qū)σ恍┨幵谄h(yuǎn)地區(qū)的、缺少記載的歷史文化內(nèi)容中具有個(gè)性化特征的關(guān)鍵信息進(jìn)行較好的解答。筆者在勐梭寨的2次田野調(diào)查期間,傣族村寨正處在關(guān)門節(jié)期間;但在跟他們慢慢熟悉之后,寨民們了解到筆者一行的調(diào)研對勐梭寨的宣傳及馬鹿舞的傳承與發(fā)展頗有益處,便在村長及佛爺?shù)臏?zhǔn)許之下,待晚上收工后,多次在緬寺前為筆者一行表演馬鹿舞。盡管此時(shí)所表演的馬鹿舞缺少了賧佛儀式的象征意義,但在整個(gè)展演過程中,馬鹿舞表演者及寨民們的沉浸狀態(tài)仍然一覽無余。通過對多次馬鹿舞表演的參與式觀察發(fā)現(xiàn),整個(gè)展演過程基本上由熱身鑼鼓,孔雀舞、白象舞墊場,馬鹿舞表演,嘎光舞收尾等幾個(gè)部分組成。
2.1.1 開場---熱身鑼鼓 鑼鼓隊(duì)成員構(gòu)成并不固定,只要掌握了擊打技巧的男性均可參與。一般為3人以上,其中擊铓者1人,擊镲者1人,擊象腳鼓者1至多人。鑼鼓在整個(gè)儀式活動中主要起到活躍現(xiàn)場氣氛、調(diào)控舞者節(jié)奏的作用。由于正值關(guān)門節(jié)期間,在傳統(tǒng)傣族人群里,此時(shí)是不宜進(jìn)行娛樂活動的,否則佛祖會怪罪寨民;但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盛行于東南亞的南傳佛教逐漸世俗化、生活化,寨子里每遇特殊情況,在關(guān)門節(jié)期間進(jìn)行娛樂活動也被予以默許。此外,熱身鑼鼓還能起到召集寨民們到緬寺匯集參與和觀看表演的作用。
2.1.2 墊場---孔雀舞、白象舞 隨著鑼鼓聲而來的寨民,有些會主動地帶上跳孔雀舞和白象舞的道具。在主角馬鹿舞尚未登場之前,勐梭寨會跳孔雀舞的女孩便在音樂聲中翩翩起舞。孔雀舞為單人表演,舞步比較簡單,主要是模仿孔雀的碎步急跑、跳、起伏步,再加上一些手部控制孔雀尾羽的動作等。白象舞道具為竹篾做架、外糊白紙的大白象,由2名男性一前一后進(jìn)入白象體內(nèi)駕馭,動作多為起伏步,緩慢而笨重。訪談得知,無論是在緬甸、泰國還是孟連地區(qū),由于受“男尊女卑、女人不應(yīng)在大眾面前過分拋頭露面”的影響,1980年以前,民間的孔雀舞、白象舞等大都由男人進(jìn)行表演,這與中原地區(qū)所了解的傣族孔雀舞多由曼妙多姿的女子表演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在文化全球化擴(kuò)展之際,特別是在以白族人楊麗萍為代表所表演的孔雀舞的影響之下,傣族社會中原本由男性所表演的孔雀舞也開始被女性所替代,傳統(tǒng)在解構(gòu)中實(shí)現(xiàn)了重構(gòu),并開始形成了新的傳統(tǒng)。現(xiàn)在所看到的傣族社會中,已少有男性跳孔雀舞了。
2.1.3 主角---馬鹿舞 在孔雀舞、白象舞的墊場之下,馬鹿舞表演者開始入場表演。馬鹿舞表演主要由鹿頭、鹿身及腳步動作組合而成,動作以擬態(tài)為主。鹿頭是通過運(yùn)用手腕關(guān)節(jié)靈活地上下左右劃“∞”字體現(xiàn)鹿的左顧右盼、機(jī)靈敏捷;鹿身則主要表現(xiàn)抖水、蹭癢等生活狀態(tài);腳步動作比較豐富,基本動作為走步、點(diǎn)步、跳步、碎步跑、起伏步等。表演者通過模仿馬鹿的跑、跳、抖身、翻滾、嬉戲及爭斗等動作,體現(xiàn)自然生態(tài)的和諧情景,同時(shí)也向佛祖祈求傣族社會的幸福安康、多金多福。
筆者通過適時(shí)地與多位傳承人、寨民等交流后得知,勐梭寨的馬鹿舞表演風(fēng)格與其他地方略有不同,且勐梭寨不同的師父所表演的風(fēng)格也各有差異。同屬孟連的勐阿,也盛行馬鹿舞,但與勐梭寨的馬鹿舞相比,他們的“馬鹿”頸更短,腳上的動作富于跳躍,更具武術(shù)表演性。勐梭寨馬鹿舞第1代傳承人波帥幫表演的馬鹿舞主要體現(xiàn)馬鹿柔美的一面,而波五相表現(xiàn)的是馬鹿機(jī)靈、活潑的一面。第3代傳承人巖三嫩綜合了2位老藝人跳馬鹿舞的特點(diǎn),集中體現(xiàn)了馬鹿的活潑“靈”性和寧靜“柔”性的特點(diǎn),藝術(shù)表演力更為豐富。普洱市每年都在神魚節(jié)、潑水節(jié)上從各地抽調(diào)馬鹿舞表演隊(duì)到各市縣進(jìn)行巡演,寨民們會依據(jù)馬鹿舞的風(fēng)格特征判斷各馬鹿的地域歸屬,并通過對馬鹿舞表演水平的“優(yōu)劣”評價(jià),提升族群認(rèn)同與族群歸宿感。
勐梭寨第1、2代傳承人的馬鹿舞表演通常為40~60 min,由20幾個(gè)動作組成。1988年前后,為了適應(yīng)外出舞臺表演的需要,在孟連縣文化館職員陳志明的組織下,在保留勐梭寨馬鹿舞原有風(fēng)格的基礎(chǔ)上,適當(dāng)加快了動作節(jié)奏,并對動作進(jìn)行了簡化,增加了一些諸如跳躍、打斗等更具觀賞性的動作。最后整套馬鹿舞共約七八個(gè)動作,4~5 min。可見,如今在勐梭寨所看到的馬鹿舞其實(shí)當(dāng)屬近30年來才“被發(fā)明的傳統(tǒng)”。
胡小明等[4]認(rèn)為,對體育的一切研究,其基本出發(fā)點(diǎn)和終極的依托主干都離不開對人類身體的影響,這也是體育學(xué)存在的依據(jù)……對于體育人類學(xué)而言,研究人類的身體形態(tài)和機(jī)能,是為促進(jìn)人類文化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無論怎樣研究身體狀況,都是文化的需要。為此,就馬鹿舞對于舞者的身體質(zhì)量的影響及動作刪減原因等問題,筆者還從體質(zhì)人類學(xué)的角度進(jìn)行了簡單探究。
筆者及學(xué)習(xí)班成員對共計(jì)12人次的馬鹿舞表演者的心率進(jìn)行了測量,他們在表演前平均心率為66次/m in,在表演后即刻再次進(jìn)行測量,飾馬鹿頭者平均心率為177次/min,飾馬鹿尾者平均心率為153次/ min。此外,筆者還對馬鹿舞表演者的力量、速度、柔韌性及協(xié)調(diào)性進(jìn)行估測,認(rèn)為這些指標(biāo)均比勐梭寨其他村民要好。通過對馬鹿舞表演者各項(xiàng)身體素質(zhì)的評估,筆者認(rèn)為其作為“被發(fā)明的傳統(tǒng)”的生物學(xué)依據(jù)較為明顯:在現(xiàn)有馬鹿舞表演風(fēng)格下,很少有未經(jīng)過專業(yè)體育訓(xùn)練的人員能在150次/min以上的心率下進(jìn)行長達(dá)40~60 min的表演。為此,生物載體的極限性決定了對動作進(jìn)行刪減成為必要。對于馬鹿舞表演者為何在力量、速度、柔韌性及協(xié)調(diào)性上好于其他村民,是否因?yàn)榫毩?xí)馬鹿舞而引起的身體適應(yīng)性發(fā)展,或因?yàn)楸硌菡叩纳眢w天賦優(yōu)勢而使得在馬鹿舞傳習(xí)過程中自然選擇了他們,有待進(jìn)一步研究。
2.1.4 收尾---嘎光舞 如果說孔雀舞、白象舞及馬鹿舞等是部分傣族人參與的向佛祖敬獻(xiàn)的儀式性犧牲,那么嘎光舞則是現(xiàn)場所有人向佛祖的祈福與獻(xiàn)禮。除了擊打鑼鼓者,幾乎所有現(xiàn)場者都會參與其中,經(jīng)常是幾十人、上百人圍著篝火,女性在里圈,男性在外圈,逆時(shí)針方向,在象腳鼓、排铓、镲的伴奏下起舞。通常以4小節(jié)、8小節(jié)或平16小節(jié)為一個(gè)舞節(jié),且每一舞節(jié)可循環(huán)往復(fù)地進(jìn)行,也可把幾個(gè)舞節(jié)串聯(lián)成一組。整個(gè)舞蹈由丁字點(diǎn)步、搓踢步、扣腿旁點(diǎn)步及“之”字點(diǎn)步等腳步動作,側(cè)平展翅、甩手高合抱翅等手上動作,配以傣族特有的三道彎身體造型構(gòu)成,并不時(shí)呼喊“水-水水水(諧歲歲平安)……”“喲-喲喲喲……”以烘托熱鬧氣氛。表現(xiàn)出佛教洗禮之下傣家人的輕盈、含蓄、柔和、感恩及祈求來世的文化特性。
2.2 馬鹿舞源起傳說的人類學(xué)解讀 田野調(diào)查中經(jīng)常會發(fā)現(xiàn),對于民間傳說的探討往往符合民俗文化的不可重復(fù)性邏輯,即每個(gè)人對同一民間活動都會有不同的理解。如筆者在對馬鹿舞的田野調(diào)查過程中發(fā)現(xiàn),在調(diào)查對象所陳述的與馬鹿舞有關(guān)的每個(gè)民間故事中,都會有不同版本的神話傳說。盡管如此,筆者依然認(rèn)為,把不可重復(fù)性的傳說置于傣族社會中進(jìn)行理解時(shí),仍然是有其特定邏輯可循的。結(jié)合訪談和觀察,經(jīng)邏輯分析,歸納整理出馬鹿舞的民間起源傳說主要有以下4種版本。
巖三嫩(馬鹿舞第三代傳承人):馬鹿舞傣語稱為“戛朵”“煩朵”。“戛與煩”都為“跳”的意思,“朵”即為“馬鹿”。佛祖做擺,來朝賀的有人、有鬼、有動物,“朵”也來了。“朵”是從幸福的地方---“來少勐”來的,它帶來了發(fā)達(dá)與興旺,很受群眾的歡迎,之后,民眾便扮成馬鹿來跳舞。
昆弄(孟連縣民間藝術(shù)家,孔雀舞傳承人):馬鹿是佛祖升天時(shí)的吉祥物,因?yàn)樗芗椋藗冋J(rèn)為模仿它的跳能帶來好運(yùn),就根據(jù)自己的想象來做馬鹿的頭,并跳“朵恩、朵喊、朵豪”(“恩、喊、豪”為傣語,即“銀子、金子、糧食”,“豪”同時(shí)還有“進(jìn)來”的意思),意思是跳馬鹿舞就會把金銀財(cái)寶拱進(jìn)自己家里。
波相三(孟連縣民間文學(xué)傳承人):佛祖降世后,世界上所有信奉佛教的人和動物都想來拜佛。馬鹿和孔雀說沒有別的心意來賧給佛,就只是會跳舞,佛祖于是讓它們跳舞。后來傣族賧佛中,不管賧多賧少,都要有馬鹿和孔雀參加,這就形成了傣族佛事活動中的馬鹿舞和孔雀舞。
勐梭寨村民:佛祖曾到孟連傣族寨子傳經(jīng),傣族在寨子里跳舞歡迎,馬鹿聽到了铓、鼓的聲音,被吸引過來,并到寨門口與人們一起聽經(jīng)。馬鹿本來是沒有靈性的動物,受佛祖?zhèn)鹘?jīng)之后,通了靈性,人們便把它迎進(jìn)寨中挨家挨戶照顧它。自從馬鹿進(jìn)寨之后,寨子里的人們安居樂業(yè),幸福安康,因此大家便以跳馬鹿舞的形式祈求寨子風(fēng)調(diào)雨順,多金多福。
斯特勞斯認(rèn)為,對民族的文化進(jìn)行研究,研究的重點(diǎn)不是神話與傳說的真?zhèn)危窃谏裨捄蛡髡f(符號、信碼)背后所蘊(yùn)含的普遍具有的原始邏輯或“野性思維”(結(jié)構(gòu))[5]。我們所能夠做的是將一個(gè)神話的所有已知變體歸入一個(gè)系列,形成某種意義上的一組置換……這樣一來,我們就在原本是一片混沌當(dāng)中引進(jìn)了一點(diǎn)點(diǎn)秩序。另一個(gè)附帶的好處是可以提取出若干邏輯運(yùn)作,它們本是神話思維的基礎(chǔ)[6]。民族學(xué)家還認(rèn)為,一個(gè)特定社會的文化及其神話之間存在著常規(guī)性的關(guān)聯(lián)是不言而喻的……有一種一致性是必然存在的,而且確實(shí)存在于一個(gè)神話的無意識的寓意,即它試圖解決的問題和它的有意識的內(nèi)容之間,后者就是這個(gè)社會為了期待這個(gè)結(jié)果而營造起來的情節(jié);然而,這種一致性不一定是一種準(zhǔn)確無誤的復(fù)制,它同樣可能以一種符合邏輯的轉(zhuǎn)換面目出現(xiàn)[6]。對于馬鹿舞源起的闡釋,實(shí)質(zhì)上應(yīng)要求人類學(xué)者考察不同文化領(lǐng)域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這些領(lǐng)域通過它們互補(bǔ)的功能而連接在一起[7]。此外,還應(yīng)對他們生產(chǎn)、生活方式進(jìn)行描述,這種描述與其所處的文化圈有關(guān),是一定文化圈內(nèi)物質(zhì)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綜合[8]。
一個(gè)流傳下來的民俗儀式,通常都會伴隨一些相關(guān)的故事,這些故事無外乎就是關(guān)于這個(gè)儀式的起源、演變以及各種禁忌,這也構(gòu)成了儀式背后故事的敘事結(jié)構(gòu);因此,很多儀式傳說的敘事結(jié)構(gòu)都有“原型”或者“母題”,而敘事或者儀式中大量的符號隱喻往往需要從基本的敘事結(jié)構(gòu)中來尋找[9]。以上對馬鹿舞的民間傳說的陳述,同樣證明了隱喻作為象征文化體系的一種表述,在儀式性民俗體育活動中也普遍使用。在傣族的文化體系中,人們選擇什么樣的東西進(jìn)行表述,他們?yōu)槭裁催x擇這個(gè)東西,所表達(dá)的意義是什么,這些意義在整個(gè)文化系統(tǒng)中占據(jù)什么樣的地位,這些象征符號是否具有“工具”的作用等[10],都可以放到他們的生活環(huán)境、宗教信仰中進(jìn)行闡釋。一是佛。盡管在不同的陳述人口中,佛出現(xiàn)的場合、時(shí)機(jī)各不一樣(有些是“做擺、朝佛”,有些是佛祖“降臨、西去”,還有些是佛祖“傳道”),但都與他們所信奉的南傳佛教有關(guān)。二是吉祥的動物。傣族經(jīng)常跟各種動物打交道,他們會根據(jù)本民族傳統(tǒng)的觀念來想象各種動物的喻意。他們認(rèn)為,馬鹿、孔雀等均象征了吉祥,能給人帶來好運(yùn)或富足。三是美好的愿望。因?yàn)樗麄冃欧钅蟼鞣鸾蹋v究來世,因此日常生活中都會向佛祖訴說心愿,祈求得到保佑。
2.3 馬鹿舞跨境傳播與傳承的人類學(xué)解讀 在進(jìn)行部落文化研究時(shí),必須同樣對待那些普遍、乏味的事物與俗人感到震驚、不同尋常的事物。與此同時(shí),整個(gè)地區(qū)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必須經(jīng)過調(diào)查研究,在各個(gè)方面之間通行的連續(xù)性、規(guī)則性和秩序把他們連接成為系統(tǒng)的整體[11]。在對民族、民俗、民間體育進(jìn)行個(gè)案研究時(shí),要想從整體上把握研究對象所產(chǎn)生的體育文化內(nèi)涵,真實(shí)地還原研究對象的緣起動力、傳承脈絡(luò)及變遷原因,把歷時(shí)性與共時(shí)性研究2種方法結(jié)合起來,將能起到互補(bǔ)有無的作用[12]。為此,筆者將依據(jù)這些指導(dǎo)思想,對勐梭寨歷史場景中的馬鹿舞跨境傳承與傳播等問題進(jìn)行探討。
勐梭寨的建寨時(shí)間較短,就歷史不足80年的小寨子里發(fā)生的事情進(jìn)行調(diào)查,部分村民(特別是部分長者)會有一定的記憶。對于勐梭寨馬鹿舞這樣缺少文獻(xiàn)記載的民俗體育活動在寨子內(nèi)代際間的變遷與傳承的調(diào)查,口述史及邏輯分析等研究方法尤為重要。由于訪談樣本具有較強(qiáng)的主觀性,內(nèi)容與事實(shí)接近與否,取決于樣本的選取情況。為了盡量避免主觀干擾,筆者及同行人員對與馬鹿舞相關(guān)的各階層人物進(jìn)行了訪談,且每天都堅(jiān)持撰寫詳細(xì)的田野調(diào)查日記。在隨后進(jìn)行的成員之間討論中,大家把多種戶訪材料統(tǒng)籌綜合起來進(jìn)行分析與整理,最終形成了勐梭寨近80年內(nèi)的6代馬鹿舞傳承譜系(表1)。

表1 云南省孟連縣勐梭寨馬鹿舞傳承譜系Table 1 Heritage Pedigree of M alu Dance in Mengsuo Village of M englian County,Yunan Province
人類學(xué)整體觀認(rèn)為,構(gòu)成人類整體的各種要素是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只要其中一種要素發(fā)生變化,其他要素必然會發(fā)生相應(yīng)的變化[13]。為此,理解和認(rèn)識跨境族群中的儀式性民俗體育活動傳承譜系的變遷與傳承問題,不僅需要關(guān)注其中的社會文化因素,還需要重視歷史進(jìn)程中各類社會事件對該儀式性民俗體育活動變遷與傳承所產(chǎn)生的影響作用。筆者認(rèn)為,要想對傳承譜系的代際特點(diǎn)進(jìn)行合理的闡釋,如要探討“第1代是基于什么原因?qū)W習(xí)馬鹿舞,接下來的各代又是在什么社會環(huán)境下進(jìn)行傳承的”等問題,就需要采用文化整體觀的視角,把傣族馬鹿舞置于整個(gè)社會歷史變遷事件中進(jìn)行分析。
從傣文文獻(xiàn)的記載來看,馬鹿舞傳入孟連的時(shí)間應(yīng)該是在第3代孟連土司“刀派送”(1349-1406年)執(zhí)政時(shí)期,并在隨后的歷代土司賧佛活動中成為重要的活動內(nèi)容之一。同時(shí),當(dāng)?shù)孛坑惺⒋蟮墓?jié)慶活動,如潑水節(jié)、開門節(jié),各寨子都要派出馬鹿舞的演出隊(duì)伍到孟連宣撫司為土司們進(jìn)行表演祈福。筆者通過與多位報(bào)告人的訪談了解到,在1939年前的西盟大勐梭時(shí)期,人們并不跳馬鹿舞,只是在賧佛時(shí),用紙?jiān)恕鞍遵R鹿、白象、白馬、白水牛”等動物賧給佛祖。由此推測,此前西盟縣與孟連縣對于賧佛活動中的“馬鹿”表現(xiàn)形式或許存在一定的差異:孟連縣在刀派送之后的歷代土司主導(dǎo)下的賧佛活動中,有可能存在以馬鹿舞、白象舞、魚舞等為主要擬態(tài)舞蹈的動態(tài)供奉品;而西盟縣是以馬鹿、白象、白馬、白水牛等紙?jiān)撵o態(tài)供奉品。訪談發(fā)現(xiàn),在勐梭寨建寨初期,在各種賧佛活動中,馬鹿舞還沒有出現(xiàn),而是采用西盟時(shí)期賧紙?jiān)R鹿的形式。隨著勐梭寨與相鄰各寨之間的文化交流增多,賧佛活動產(chǎn)生了“涵化”,使得各家賧佛活動中,那些紙?jiān)鸟R鹿逐漸開始改為由人操縱進(jìn)行表演---勐梭寨馬鹿舞開始形成,而在表演結(jié)束之后,這些紙?jiān)囊堰M(jìn)行過表演的紙馬鹿,又成為靜態(tài)供奉品,被擺放在緬寺之內(nèi)用來繼續(xù)供奉。
1950年云南解放之后,國家權(quán)力系統(tǒng)深入村落,無產(chǎn)階級無神論思想開始實(shí)現(xiàn)對村落的全面控制,并明令取締各種宗法制度,傣族社會的賧佛活動被視為封建糟粕予以禁止。隨后,一系列政治運(yùn)動對孟連縣形成了強(qiáng)烈的沖擊,如在“土地改革”“大躍進(jìn)”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部分解放前擁有一定財(cái)富和地位的傣族士紳、對人民犯下罪行的傣族權(quán)貴以及聽信各種流言的傣族平民們,借助便利的地理?xiàng)l件及相似的族源文化等,避難到緬甸、越南及泰國等國家,其中,逃往緬甸的當(dāng)時(shí)就逾萬人[14],波喃短、波五相及波帥幫等人就多次加入了這些避難隊(duì)伍。他們在國外期間,見到緬甸撣族、泰國泰族等在賧佛活動中與孟連縣不同風(fēng)格的馬鹿舞表演后,基于族群認(rèn)同及宗教信仰的需要,產(chǎn)生了要把這些國外的馬鹿舞傳播到國內(nèi)的愿望。在國內(nèi)局勢趨于平穩(wěn)之后,出于故土難離的鄉(xiāng)土情懷,他們帶著從緬甸、泰國等學(xué)習(xí)到的被認(rèn)為屬于本族群的最原生態(tài)的文化回到了孟連。在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之后的幾年是國人信仰極為匱乏的時(shí)期,這樣的時(shí)代為民俗提供了回歸的契機(jī),傣族人們希望借助馬鹿這一通靈的神獸,實(shí)現(xiàn)自己對西方極樂世界的終極皈依,于是波喃短、波帥幫等人把從緬甸、泰國學(xué)到的馬鹿舞技藝,再融匯之前的孟連馬鹿舞特點(diǎn),傳授給了第2代和第3代。
1990年后,隨著改革開放進(jìn)程的深入,民族地區(qū)文化形態(tài)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政府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控制和影響力逐漸從民族村寨中退出,民族地區(qū)自在的民俗文化逐步回歸。在經(jīng)歷了30余年無產(chǎn)階級無神論思想洗禮后,此時(shí)重現(xiàn)復(fù)興之勢的民間信仰,開始拋棄原來單純意義上“封建祭祀”的娛神功能。傣族社會的賧佛及其他佛事活動出現(xiàn)了世俗化趨勢,表現(xiàn)在由傳統(tǒng)自在時(shí)期的嚴(yán)格師徒傳承轉(zhuǎn)向較為隨意的師徒與集體傳承相結(jié)合。此時(shí),年輕一代大都是節(jié)慶時(shí)觀看長輩的馬鹿舞表演時(shí),跟著鼓點(diǎn)自己學(xué)會的,基本上沒有舉行專門的拜師學(xué)習(xí)程序。當(dāng)人手不夠時(shí),便會有所謂的第4代人進(jìn)行臨時(shí)兼職。進(jìn)入21世紀(jì),隨著經(jīng)濟(jì)及文化全球化向邊遠(yuǎn)民族地區(qū)的擴(kuò)張加劇,中國、緬甸、泰國等與佛教有關(guān)的民俗、宗教及祭祀等活動基本上被世俗化,傣族社會的賧佛活動逐漸成為只是一種具有一定象征意義的儀式活動,而非之前傣族人們實(shí)現(xiàn)來世極樂的絕對的精神寄托。作為溝通人與佛祖之間橋梁的馬鹿舞,也只是在一些集體活動中實(shí)現(xiàn)傳承,代際之間的關(guān)系開始模糊化。
3 在想象共同體下實(shí)現(xiàn)傳承與傳播的儀式性民俗體育活動
人類學(xué)界一般對個(gè)案比較關(guān)注,但個(gè)案研究并不只是因?yàn)樾枰钊爰?xì)致地分析某一單一事項(xiàng)并對其進(jìn)行文化闡釋,而是為了通過單一事項(xiàng)的闡釋,歸納出普遍的意義,從而實(shí)現(xiàn)理論的借鑒、證偽或是對相似事象的理論推演。借助馬鹿舞這一跨境族群的儀式性民俗體育活動,筆者得出“擁有想象的共同體是儀式性民俗體育活動得以實(shí)現(xiàn)傳承與傳播的重要原因”的理論觀點(diǎn)。
安德森[15]在《想象的共同體》中對“民族主義”進(jìn)行探討時(shí),參考了沃森(Hugh Watson)在《民族與國家》中的觀點(diǎn),這一觀點(diǎn)同樣適用于探討“族群”這一文化概念:它是通過具體象征物(如旗幟、民族服裝、儀式)想象出來的,因?yàn)榧词故亲钚〉拿褡宄蓡T,也不可能認(rèn)識他們大多數(shù)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聯(lián)結(jié)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筆者認(rèn)為,這種相互聯(lián)結(jié)的意象主要是基于原生的共同文化信仰及其具體象征物,聯(lián)結(jié)的結(jié)果是行動者為了“祈福”這一“工具性”目的,使用族群認(rèn)同將“我族”和“他族”區(qū)分開來,從而形成族群邊界。在族群邊界之內(nèi),作為共同文化的信仰或儀式便因族群認(rèn)同而由某一中心向周圍產(chǎn)生傳播,而傳播的結(jié)果是強(qiáng)化了“我族”與“他族”區(qū)別以及對“我族”認(rèn)同的加強(qiáng)。
從傣族馬鹿舞這一個(gè)案來看,它起源于緬甸的勐娃地區(qū),盡管緬甸與中國、泰國、越南以及東南亞各國傣人之間存在有形的國界,但是在共同的南傳佛教信仰和傣人族群認(rèn)同之下,馬鹿舞的傳播使有形國界臣服于文化認(rèn)同。傣人通過在賧佛儀式中的馬鹿舞、白象舞、魚舞等的展演,不僅實(shí)現(xiàn)神人共娛,而且也促進(jìn)了本族群文化的傳承及傳播。同時(shí),“在他族觀點(diǎn)與本族觀點(diǎn)推動下,使族群內(nèi)部認(rèn)同具有更為持久能動作用”[16],這也使得族群認(rèn)同比其他認(rèn)同有著更為持久的聚合力,其強(qiáng)大的聚合力使族群認(rèn)同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資源”[3]367。筆者在勐梭寨田野調(diào)查期間,聽人們提及馬鹿舞道具、技術(shù)動作、風(fēng)格以及伴奏鑼鼓等都是從“我們那邊(緬甸)的家人傳過來的”“我們的馬鹿舞與其他寨子的不一樣”等表達(dá)。從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觀念中,“國界”只是一個(gè)比較模糊的概念,而“傣人”在“族群文化”這一特定情境之下是超越國界的,族群邊界才是他們所關(guān)注的。
同樣,不僅是跨境族群的民俗性體育活動傳承與傳播是如此情況,鄉(xiāng)土中國下的大多數(shù)儀式性民俗體育活動都是在“想象的共同體”下得以在族群中傳播。它們都會有一個(gè)共同信仰的神靈作為支撐,然后借助一定程序的身體運(yùn)動在同一或相似族群中實(shí)現(xiàn)共同的歷史記憶。如:李志清[3]369認(rèn)為廣西三江侗族通過搶花炮這一儀式性活動,實(shí)現(xiàn)了侗族集體性記憶及結(jié)構(gòu)性健忘,并凝聚及調(diào)整了侗族及周邊族群的人際關(guān)系,以此適應(yīng)現(xiàn)實(shí)資源競爭的人類社會結(jié)群現(xiàn)象;陳奇等[17]在對廣西南丹拉者村“演武節(jié)”中的“斗牛斗”儀式性民俗體育活動的研究中也認(rèn)為,斗牛斗運(yùn)動起到了承載壯族族群文化的功能,延續(xù)了包括民俗信仰與生活習(xí)慣在內(nèi)的傳統(tǒng)文化生命。
4 結(jié)束語
就勐梭寨的“馬鹿舞”這一個(gè)案而言,它只是為筆者提供了在某一特定場景中對跨境族群文化的較為細(xì)致、特定角度的觀察,然后試圖將這一特定田野點(diǎn)置于宏觀社會背景中解釋,并期望在一定層面上將抽象和概化的理論與現(xiàn)實(shí)中的族群文化現(xiàn)象結(jié)合起來,得以理論印證。筆者同時(shí)也意識到,本文中所提及的跨境族群儀式性民俗體育活動在“跨境傳播”問題上的探討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無法跨越中緬邊境進(jìn)行田野作業(yè),只能囿于中國地理區(qū)域內(nèi),把馬鹿舞定位于從緬甸傳往中國進(jìn)行的單向度研究。筆者認(rèn)為,要想促進(jìn)族際的相互理解,加強(qiáng)東盟各國的文化包容,應(yīng)從跨文化的視角并跨越邊境對其他諸如瑤、苗、壯等跨境民族的身體運(yùn)動文化繼續(xù)進(jìn)行深入研究。
[1] 黃光成.跨界民族的文化異同與互動:以中國和緬甸的德昂族為例[J].世界民族,1999(1):25-30
[2] George Stoking.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M].Madison:University of W isconsin Press,1992:28
[3] 李志清.鄉(xiāng)土中國的儀式性少數(shù)民族體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8
[4] 胡小明,楊世如,夏五四,等.黔東南獨(dú)木龍舟的田野調(diào)查[J].體育學(xué)刊,2009,16(12):1-8
[5] 胡小明,楊世如.獨(dú)木龍舟的文化解析[J].體育學(xué)刊,2010,17(1):1-9
[6] 斯特勞斯.結(jié)構(gòu)人類學(xué)[M].張祖建,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9:206
[7] 穆爾.人類學(xué)家的文化見解[M].歐陽敏,鄒喬,王晶晶,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9:158
[8] 李延超,饒遠(yuǎn).傣族體育與“水文化”緣由探析[J].體育科學(xué),2006.26(4):76-79
[9] 熊迅.儀式結(jié)構(gòu)與國家認(rèn)同:跨越中緬邊境的傈僳族刀桿節(jié)[J].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0(12):45-50
[10] 彭兆榮.人類學(xué)儀式的理論與實(shí)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07
[11] Malinowski B K.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M]. London:George Routledge&Sons,1922:11
[12] 楊海晨,王斌,胡小明,等.論體育人類學(xué)研究范式中的跨文化比較[J].體育科學(xué),2012,32(8):3-15
[13] 胡小明.體育人類學(xu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4
[14] 萬麗.云南萬人1958年逃亡緬甸 86年后回國至今無戶口[EB/OL].[2013-07-06].http:∥news.qq.com/a/ 20121029/001037.htm
[15]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M].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16] 納日碧力戈.現(xiàn)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gòu)[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96
[17] 陳奇,楊海晨,沈柳紅.一項(xiàng)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文化人類學(xué)研究[J].體育科學(xué),2013,33(2):30-37
Imagined Community: An Anthr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Ritualized Folk Sport of th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Field W ork on“M aluDance”in Dai Village
∥YANG Haichen1,WANG Bin1,HU Xiaoming2,SHEN Liuhong3,ZHAO Fang4
imagined community;cross-border ethnic group;ritualized folk sport;Malu Dance;Dai village
G80-05
A
1000 -5498(2014)02 -0052 -07Abstract The study adopted field work to investigate the ritualized fork sport-Malu Dance,which exists in th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 of a Dai village of Menglian County,Yunan Province.It finds that the prototype of Malu Dance originates from the living environmentand religious beliefsof the Daisociety.The cross-border inheritance and communication correspond to the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Dai society.The study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an imagined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makes the inheritance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ritualized folk sport come true.
2013 -09 -10;
2013 -11 -21
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資助重點(diǎn)項(xiàng)目(10ATY001);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資助青年項(xiàng)目(11CTY022);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資助西部項(xiàng)目(12XTY005);“廣西高等學(xué)校優(yōu)秀中青年骨干教師培養(yǎng)工程”計(jì)劃資助項(xiàng)目;玉林師范學(xué)院青年科研項(xiàng)目(2011YJQN15)
楊海晨(1977-),男,回族,湖南武岡人,華中師范大學(xué)博士研究生,桂林電子科技大學(xué)體育部副教授;Tel:18064007139,E-mail:yhaichen2011@126.com
胡小明(1952-),男,土家族,四川涪陵人,華南師范大學(xué)體育科學(xué)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Tel:(020)39310230,E-mail:hxmzw@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