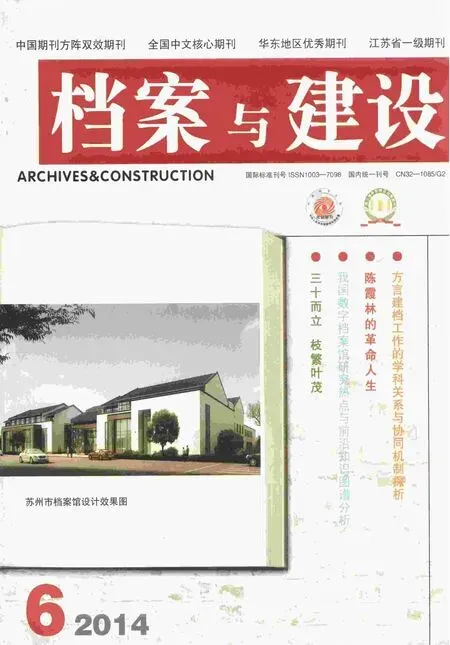《清宮揚(yáng)州御檔》中的玉璽、奏折及其它
朱 競(jìng)
(揚(yáng)州廣播電視總臺(tái),江蘇揚(yáng)州,225000)

清廷常用的“皇帝之寶”
打開(kāi)《清宮揚(yáng)州御檔選編》,在清代各朝御檔之首,都有一方9 厘米見(jiàn)方的“皇帝之寶”印章。據(jù)中國(guó)一史館清史專家介紹:在紫禁城收藏的眾多寶物中,明清帝后寶璽近五千件,而最能代表皇帝無(wú)上權(quán)威和地位的寶物,非此寶璽莫屬。
乾隆帝是清朝入關(guān)以后的第四代皇帝。乾隆以前,清代皇帝寶璽一般沒(méi)有規(guī)定確切的數(shù)目。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乾隆帝欽定御寶為25 方,后人稱這25 方印章為“二十五寶”。這25 方寶璽也是現(xiàn)存唯一的一套完整的皇帝御寶。而在清代,這25方寶璽通常儲(chǔ)存于交泰殿的寶箱內(nèi),平時(shí)由內(nèi)閣掌管,用印時(shí)須經(jīng)皇帝批準(zhǔn)才可拿出。
在25寶中,因“皇帝之寶”為皇帝日常用璽,故刻有二枚,一玉制,一木制,玉質(zhì)為絞龍紐,木質(zhì)為蹲龍紐。入選《清宮揚(yáng)州御檔選編》一書的這枚印章,實(shí)物為檀香木質(zhì),盤龍紐方形璽,漢、滿文篆書。實(shí)物面15.5 厘米見(jiàn)方(印入書中的比實(shí)物小),通高16厘米,紐高11厘米。附系黃色綬帶。《交泰殿寶譜》將此印收入其中,認(rèn)為此寶為“以肅法駕”之象征物。從現(xiàn)存清代御檔看,“皇帝之寶”為鈐用最多之寶,且鈐用的范圍也很廣,諸如皇帝登基、皇后冊(cè)命、皇帝大婚、發(fā)布進(jìn)士金榜及其重要詔書上均鈐用此寶。其所鈐詔敕制誥之性質(zhì)及使用之經(jīng)常,它寶實(shí)無(wú)以相比,應(yīng)視為清朝皇權(quán)之真正標(biāo)志。
在編輯《清宮揚(yáng)州御檔選編》時(shí),編者起初擬定各朝分別選用當(dāng)朝有代表性的印章作為各自篇首標(biāo)志的方案,后綜合各方意見(jiàn),最終僅選用清代最常用的“皇帝之寶”一枚,代表皇帝行使朝廷最高權(quán)力印入書中。實(shí)際上,在清代,最為常用的也就是“皇帝之寶”等數(shù)枚。另?yè)?jù)專家介紹,包括“皇帝之寶”在內(nèi)的25方寶璽,歷經(jīng)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等諸朝,一直沿用至宣統(tǒng)末年為止。
清代的主要公文——奏折
清代初期,公文沿用明制,為奏本、題本、揭貼等。后來(lái),隨著清初軍政事務(wù)日益繁忙,緊要之事、機(jī)密之事多,清廷對(duì)文書作了變革,廢棄明代題本的固定格式,在集奏疏、揭貼和題本形式基礎(chǔ)上演變?yōu)榍宕淖嗾郏⒊蔀橹饕奈臅问健T凇肚鍖m揚(yáng)州御檔》中,朱批奏折占據(jù)全書2/3 以上篇幅,成為該書的主要內(nèi)容。
一般說(shuō)來(lái),奏折的使用,至今有200多年的歷史。始于康熙朝中期,最初僅限于皇帝指定的少數(shù)親信官員。雍正皇帝即位后,進(jìn)一步擴(kuò)大了奏折的使用范圍,奏折也一直沿用到清宣統(tǒng)朝結(jié)束為止。可見(jiàn),清代歷朝帝君是通過(guò)批閱奏折,直接了解和掌控中央政府和整個(gè)國(guó)家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民生等諸多方面的情況。隨著奏折的作用越來(lái)越多,至乾隆年間,奏折成為臣工上報(bào)政務(wù)的另一種重要的官文書。由于奏折文字簡(jiǎn)練,由皇帝親自閱覽批示后,再發(fā)下具折人遵照?qǐng)?zhí)行,省卻了許多中間環(huán)節(jié),突出了運(yùn)轉(zhuǎn)快捷、保密性強(qiáng)、時(shí)效性強(qiáng)等優(yōu)點(diǎn),更符合封建皇帝集權(quán)統(tǒng)治的需要,所以一旦成為正式官文書,其地位和作用迅速凸顯。
清代奏折的處理部門為軍機(jī)處。軍機(jī)處是輔佐皇帝辦理軍政要?jiǎng)?wù)的重要機(jī)關(guān)。之前是“三省長(zhǎng)官”(中書、門下、尚書)、“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大臣”,有時(shí)候太監(jiān)總領(lǐng)也有收轉(zhuǎn)奏折的機(jī)會(huì)。至于上奏者,在清朝初期,上至各部尚書,下至平民、僧人都可以,并無(wú)地位要求。從清朝中期開(kāi)始,奏折只有高級(jí)官員才能上折,一般是各部尚書侍郎,大理寺監(jiān)察院御史,各省巡撫總督,軍機(jī)大臣大學(xué)士等高級(jí)官員才有資格。但并非強(qiáng)行規(guī)定,比如發(fā)生特殊事件的時(shí)候,縣官等也可以上奏折,但一般不直接送到皇帝那里,而是通過(guò)上級(jí)部門轉(zhuǎn)送。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地方大員以及皇帝派到各地、軍中的眼線,有直接給皇帝上呈奏折的權(quán)利,這種奏折都是封好后直接交給皇帝,稱為“密奏”。清康熙年間的曹寅和李煦曾分別在揚(yáng)擔(dān)任兩淮鹽政多任,而此前他們擔(dān)任的江寧織造、蘇州織造,其官銜最多為五品,尚不具備直接向皇帝上呈奏折的資格,但他倆憑著和康熙帝的私情關(guān)系,得到康熙帝的特許,近30年間可謂密奏如云,僅《清宮揚(yáng)州御檔》一書收錄的奏折就有近百件之多。他倆的奏折,無(wú)疑成了康熙帝君了解社會(huì)風(fēng)俗民情以及官員貪廉情況的重要信息管道。
奏折雖然有薄有厚,但大小尺寸、格式都完全一樣,如日常奏報(bào)公事的,每頁(yè)只寫6 行,每行18 字,遇皇帝、天、地等尊稱抬頭2 個(gè)字,全用工整娟秀的小楷毛筆字寫成。皇帝“朱批”毛筆字大多也很工整,只有乾隆帝的字常常龍飛鳳舞。雍正帝批一個(gè)折子動(dòng)輒數(shù)十字甚至數(shù)百字,顯示出他工作的勤勉。《清宮揚(yáng)州御檔》收錄雍正朝檔案計(jì)15 件,其中只有9 件為朱批奏折,顯得非常珍貴。另從外觀形式上看,奏折上的官員、官府印章刻得也很精美。正如中國(guó)第一歷史檔案館相關(guān)文史專家所言:“每份清宮檔案都是一件精美的書法藝術(shù)品。”
并不是無(wú)論誰(shuí)的奏折皇帝都會(huì)看的。一般奏折進(jìn)給皇帝批示之前,都有專人負(fù)責(zé)謄抄,然后分檔歸類,送到各個(gè)相關(guān)職能部門,再由部門長(zhǎng)官挑出重要之事來(lái)請(qǐng)示皇帝。皇帝批示后,原折發(fā)還具奏人,軍機(jī)處在原折發(fā)還具奏人之前,抄錄副本存檔,稱“錄副奏折”,保存在軍機(jī)處。據(jù)介紹,中國(guó)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清宮軍機(jī)處檔案,絕大多數(shù)為錄副奏折。而皇帝批過(guò)的朱批奏折,地方官員辦理完畢后,上繳朝廷歸檔保存。朝廷各部門都有一本類似于賬簿的登記簿,上面記載著奏折收、發(fā)及運(yùn)行處理情況。
在清代,對(duì)朱批奏折的處置有著非常嚴(yán)格的規(guī)定,私自毀壞、不按規(guī)定上繳和保存奏折都是死罪。
《清宮揚(yáng)州御檔》第三冊(cè)就有一份奏折,讀來(lái)頗為讓人尋味。這是乾隆八年四月,一個(gè)名叫安寧的官員上呈給乾隆帝題為《奏為家人途次揚(yáng)州舟覆折件落水沾濕并恭繳朱批折件事》的奏折,折中寫道:
奏為據(jù)實(shí)奏明事,竊奴才于乾隆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恭奏地方情形事共七折,于十月二十八日奉到朱批。因赍折家人回江之時(shí),途次揚(yáng)州,舟覆落水,雖幸奏折撈獲無(wú)失,但開(kāi)看俱已沾濕,奴才不勝惶悚。今同奴才回任后奉到朱批共二十二件一并恭繳,所有落水沾濕緣由,奴才不敢不據(jù)實(shí)奏明,伏乞睿鑒。謹(jǐn)奏。
安寧乾隆八年四月初二日
乾隆帝朱批:“覽”。從昔日奏折的短短幾行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清代對(duì)奏折(特別是朱批奏折)收繳、封存有著嚴(yán)格的制度,且控制得相當(dāng)嚴(yán)密,基本堵住了朱批折件私自流往民間的渠道。再?gòu)恼壑小伴_(kāi)看(奏折)俱已沾濕,奴才不勝惶悚”一語(yǔ)的分析可知,地方官員別說(shuō)弄丟奏折,連無(wú)端污損奏折,想必也要受到嚴(yán)厲斥責(zé)的。
另在《清宮揚(yáng)州御檔》一書收錄的奏折中,乾隆朝還有多份御檔提及恭繳奏折之事。如兩淮鹽政高恒在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乾隆二十七年六月,題為《奏報(bào)揚(yáng)州等處得雪等情并恭繳朱批折件事》和《奏報(bào)揚(yáng)州一帶近日得雨情形并恭繳朱批折件事》,這兩份奏折的末了,分別向乾隆帝稟明:“再,奴才節(jié)次奉到朱批共二十八件(另份為一十五件),另封恭繳。”乾隆帝在閱后分別朱批“知道了”(見(jiàn)《清宮揚(yáng)州御檔》第四冊(cè)3396頁(yè)和第六冊(cè)3918 頁(yè))。這就是說(shuō),所有朱批奏折在地方官員閱辦后,必須“完璧歸趙”,及時(shí)封存上繳朝廷歸檔。
奏折里的另類文字游戲
清代雍、乾二朝是中國(guó)文字獄最泛濫的一個(gè)時(shí)期,然而,在《清宮揚(yáng)州御檔》收錄的乾隆年間的少數(shù)奏折里,卻看到另類文字游戲。地方官員在向乾隆帝呈報(bào)上解稅銀以及糧食數(shù)量之時(shí),羅列的計(jì)量單位非常罕見(jiàn),有10 多位乃至20 位,很是讓人匪夷所思。
一般情況下,諸多的上解稅銀奏折里,常見(jiàn)銀兩的計(jì)量單位多為“兩”—“錢”—“分”—“厘”等,如乾隆十六年(1751)閏五月初七日,傅恒等近20 位京官和地方官員聯(lián)名上奏了《題為遵旨會(huì)議兩淮運(yùn)司奏銷乾隆十五年份額征正雜鹽課并帶征各年鹽課錢糧事》,奏折中寫道:“……帶征乾隆十四年折價(jià)等銀一萬(wàn)(零)五百七十五兩六錢四分六厘零……”此文中,銀兩的最小計(jì)量單位是“厘”。

“皇帝之寶”印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兩淮鹽政普福上奏的《奏報(bào)收支節(jié)省經(jīng)解腳費(fèi)等銀兩事》奏折中提到“辛未綱所經(jīng)解腳費(fèi)等銀,除公事應(yīng)支各項(xiàng)均照例支用外,鹽政衙門節(jié)銀七萬(wàn)四千四百四十五兩零。運(yùn)司衙門節(jié)省五萬(wàn)八千七百六十六兩零……”該文中的銀兩最小計(jì)量單位均為“兩”。
上述二奏折對(duì)銀兩計(jì)量單位的運(yùn)用,與我們今天的習(xí)慣基本相仿,比較容易接受和理解。而乾隆十七年五月初八日,長(zhǎng)蘆(今合肥)鹽政吉慶上奏的《題報(bào)前署鹽政高恒并運(yùn)使護(hù)理鹽政盧見(jiàn)曾各任內(nèi)督征正雜鹽課錢糧數(shù)目事》一折,該折中的銀兩計(jì)量單位卻多得讓人咂舌。
折中寫道:“盧見(jiàn)曾詳稱前署鹽政高恒自乾隆十五年九月初二日起至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止,任內(nèi)舊管銀三十八萬(wàn)一千四百三十三兩八錢一分七厘六毫二絲九忽九微七沙三塵一埃五渺四漠一虛九澄六凈三巡八梭四庾,新收銀七十六萬(wàn)九百八十一兩七錢五分三厘四毫一忽一微八纖一渺一漠四糊一虛一澄五清五逡五巡六梭九庾……”(《清宮揚(yáng)州御檔》第五冊(cè)2869頁(yè))文中提到的新收銀數(shù)比舊管銀數(shù)的計(jì)量單位還多一位“逡”,如從“兩”算起,到最后的“庾”,計(jì)20個(gè)。
讓人費(fèi)解的是,并不是這一時(shí)期的奏折都是這樣。乾隆十七年五月初八日,長(zhǎng)蘆鹽政吉慶在上奏上述折件的同日,還上呈題為《題報(bào)前護(hù)理鹽政盧見(jiàn)曾任內(nèi)督收私鹽贖變銀兩數(shù)目事》的另一奏折,折中涉及銀兩數(shù)的計(jì)量單位卻只有5個(gè)。折中道:“前護(hù)鹽政盧見(jiàn)曾自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乾隆十七年三月初二日止,督收私鹽變價(jià)銀三兩三錢七分六厘。查長(zhǎng)蘆有應(yīng)解戶部更名食鹽變價(jià)銀一百(零)六兩六錢四分八厘八毫……”
筆者以為,在清代社會(huì),計(jì)量衡器還比較落后,銀兩的單位從“兩”到“錢”再到“分”、“厘”,再下已無(wú)多少實(shí)際使用價(jià)值。再往后的“逡”、“巡”、“梭”、“庾”等,恐連理論價(jià)值也不具有。這樣小的稱重單位,即使在科技已較為發(fā)達(dá)的今天,實(shí)際操作起來(lái)也會(huì)有些難度,更何況是260多年前的清代。
值得一提的是,吉慶在同日上奏的兩份公文卻使用不同的銀兩計(jì)重單位,另一奏折銀兩計(jì)重單位只有5 個(gè)。這就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朝廷的行文規(guī)定可能并未如此要求。長(zhǎng)達(dá)20 位的銀兩計(jì)量單位,在《清宮揚(yáng)州御檔》數(shù)千份奏折中也非常鮮見(jiàn)。我們有理由認(rèn)為,這僅是某些文人官員茶余飯后別出心裁的文字游戲而已,看不出有何目的和實(shí)用價(jià)值。抑或是乾隆帝發(fā)現(xiàn)此情并令行禁止了,抑或官員自身覺(jué)得不應(yīng)該再開(kāi)此無(wú)益玩笑,抑或……
無(wú)獨(dú)有偶,在《清宮揚(yáng)州御檔》中,除了罕見(jiàn)的銀兩計(jì)量單位外,還有類似的情形不久又出現(xiàn)在乾隆年間米的計(jì)量上。如乾隆十八年,傅恒等上奏的《題為遵議揚(yáng)州府江防同知孔傳橿原參之案請(qǐng)開(kāi)復(fù)事》(見(jiàn)《清宮揚(yáng)州御檔》第五冊(cè)3042頁(yè))。
奏折里寫道:“……今孔傳橿前于懷遠(yuǎn)任內(nèi)遺漏征報(bào)乾隆十二、十三、十四等三年升科漕米,每年應(yīng)征正耗米六升七合五勺一抄八撮二圭一粟五顆三粒三黍二稷一糠,亦在于未奉部議革職之先,即已按年全數(shù)補(bǔ)征……”
從文中內(nèi)容得知,傅恒上此奏折,是為地方官員孔傳橿蒙受漕運(yùn)總督瑚寶誣告之冤一事,據(jù)實(shí)向乾隆帝作申訴。“每年應(yīng)征正耗米六升七合五勺一抄八撮二圭一粟五顆三粒三黍二稷一糠”這句話當(dāng)引自瑚寶向乾隆帝告狀的內(nèi)容。我們知道,在清代,米的常用容量單位是石、斗、升、合、勺等。從“勺”到“石”都是以10 進(jìn)位,而“勺”以下,“圭”和“撮”曾是古代的容量單位。《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解釋為:圭,1升的10 萬(wàn)分之一。撮,10 撮等于1勺。1 市撮合1 毫升。其它如粟、黍、稷等,多為糧食作物名稱,未見(jiàn)用作容量單位的文字記載。
其實(shí),就清代而言,6升多米的價(jià)值是極其低微的。據(jù)乾隆十年的史料記載,當(dāng)時(shí)揚(yáng)州、蘇州一帶的米價(jià)為每石1 兩6 錢銀左右,按此價(jià)折算,6 升米,最多也就是1/10兩(1 錢)銀。清廷規(guī)定,一個(gè)縣官的年俸是45 兩銀子,外加20 擔(dān)俸米和養(yǎng)廉銀。七品縣令的養(yǎng)廉銀在400 到2000 兩之間。漕運(yùn)總督瑚寶為這6 升多米的區(qū)區(qū)小事,動(dòng)輒就上奏乾隆帝,而且還羅列出長(zhǎng)達(dá)12 個(gè)計(jì)量單位,不外乎渲染事態(tài),引人眼球,不排除瑚寶想借此事來(lái)炒作,以達(dá)到自己某種目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