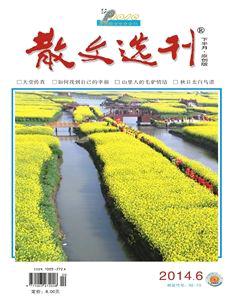大舅的水風(fēng)車
張寄寒

一到黃梅時(shí)節(jié),麥田里的麥子收割了,麥田剛剛翻轉(zhuǎn),等待上水,田野里一部部的水風(fēng)車嚴(yán)陣以待,白色的篷,悠悠地轉(zhuǎn)啊轉(zhuǎn)啊。高高的水風(fēng)車車基上支著一部部水風(fēng)車,長長的水車廂的一端擱在河畔的淺水里,隨風(fēng)而轉(zhuǎn)的篷,牽動(dòng)著幾個(gè)木齒輪軸,發(fā)出“嘰咕嚕、嘰咕嚕”的聲音,水車廂內(nèi)的木板由下而上把河里的水嘩嘩地送到田間,不多一會(huì)兒,一塊塊麥田成了一片汪洋。
大舅家是離鎮(zhèn)五里外的一個(gè)四面環(huán)水,綠樹簇?fù)怼⒎蹓焱叩男〈澹壹覒魬舫鲩T都用一條小木船,“咿咿呀呀”地?fù)u船上街。大舅上街來我家常談起他的水風(fēng)車歷史,很多年以前,村里有個(gè)學(xué)土木工程的留學(xué)日本的大學(xué)生,因病休學(xué)回家,親眼目睹父老鄉(xiāng)親農(nóng)田灌溉還在用人力踏水車,干活勞累,事倍功半。于是,他在家廢寢忘食地潛心研究,終于研究出利用風(fēng)力的水風(fēng)車,車水灌溉農(nóng)田,解放了農(nóng)民的勞動(dòng)力,受到村里父老鄉(xiāng)親的青睞,不久,在江南水鄉(xiāng)小村都有了水風(fēng)車。
大舅出生在農(nóng)村,外公給他起名叫“富農(nóng)”,長大后成了地道的貧農(nóng),當(dāng)年我媽在上海打工,不久成了家,生活殷實(shí)。我媽特地把鄉(xiāng)下的兩個(gè)弟弟帶到上海。小舅機(jī)靈活絡(luò),適應(yīng)城市生活,我爸替他在公司找到一份小職員職業(yè),給大舅在一家旅館找了一份雜勤。大舅只做二天,他說要悶死了,纏著要回鄉(xiāng)下去種田。大舅回家不久,結(jié)婚生子,住在三間破敗的平屋,門前一塊泥場,屋背后有一個(gè)小竹林。過著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農(nóng)家生活。
我十二歲那年的初夏,學(xué)校放農(nóng)忙假,我一個(gè)人步行去大舅家,剛踏進(jìn)小村口,便見到了大舅正在彎腰檢查水風(fēng)車上的零件。
“大舅,大舅……”我在大舅背后喊。
“好,我剛修好,你和我一起回家吃飯!”大舅一邊攙著我的手一邊說,你別看這部水風(fēng)車,它的能量可大哩,它要灌溉二十五畝的水田哩!走到大舅家門口,一陣飯菜香味撲鼻而來,大舅媽端出一只燉蛋、煸蠶豆、拌苣筍、燉馬蘭頭干,一股濃郁的香味,讓我垂涎欲滴,大舅媽邊盛飯邊說,不知道你來,沒啥吃,吃素!沒想到大舅媽這幾道菜都是我最喜歡吃的菜。吃罷飯,我連說,好吃,好吃!大舅媽以為我客氣,還不好意思地對(duì)我說,明天讓你大舅去河里摸塘鯉魚給你吃。
下午,薰薰的西南風(fēng)緩緩地吹著,我隨大舅去看水風(fēng)車。水風(fēng)車有六扇篷,都是白色的龍頭細(xì)布做成的,風(fēng)力最小時(shí)要扯了六扇篷,風(fēng)車才會(huì)轉(zhuǎn)動(dòng),風(fēng)力大時(shí),只要落下三扇篷。西南風(fēng)里只好扯六扇篷,風(fēng)力鼓起篷帆轉(zhuǎn)啊,轉(zhuǎn)啊,水車廂里的小木板發(fā)出“啪、啪”的聲響,河里的水從水車廂里嘩嘩地流向一塊塊麥田。
大舅替我找了一塊青草地,讓我躺在草地上休息,我好奇地躺在青草地上,聞著一股青草的清香,望著白色的篷悠悠地轉(zhuǎn),發(fā)出一陣陣木齒輪轉(zhuǎn)動(dòng)的“嘰咕嚕,嘰咕嚕”的聲音,它像一曲優(yōu)美的催眠曲。薰薰的西風(fēng)吹得讓人昏昏欲睡。
大舅媽來了,她提了一只小竹籃,上面蓋著一塊白毛巾,走到我跟前,一只手掀開白毛巾說,快吃,菜花頭塌餅!我一連吃了兩個(gè)又軟又香的菜花頭塌餅,大舅媽的熟食讓我贊不絕口。
吃罷小點(diǎn)心,我跟大舅去看水田,大舅拿了一把鏵鏟邊走邊開溝、填溝,熟門熟路,哪塊田缺水,哪塊田滿水,了如指掌。忽然發(fā)現(xiàn)一大半的水田還沒上水,而且日末風(fēng)和,風(fēng)力逐漸減弱,水風(fēng)車的篷再也轉(zhuǎn)不動(dòng)。
我和大舅回到家門口便聞到了一陣陣飯菜香味,桌上擺了紅燒塘鯉魚、拌苣筍、燉螺螄、韭菜炒蛋。大舅還喝一小杯黃酒,大舅媽說大舅是個(gè)酒蒼蠅,每天晚上要喝一杯。我立刻想起媽媽常說小舅貪杯,每喝必醉,醉了罵人打人,是個(gè)酒鬼。大舅可不這樣,他人好心善。
入晚,我和大舅睡在一床鋪上,半夜起床小便,發(fā)現(xiàn)大舅不見,我立刻穿了衣服,摸黑出門尋找,村里找遍不見大舅影蹤,我便出村走在狂風(fēng)大作的田野里,忽然發(fā)現(xiàn)一束昏黃的電筒光。
“大舅、大舅……”我追著電筒光喊。
“我在這里……”
“你在干什么?”
“半夜起風(fēng)了,我趕快給它落篷,你看它轉(zhuǎn)得多快,借助這個(gè)風(fēng)力,還有一半的水田里的水沒問題了……”大舅興奮地說。月暗天里水風(fēng)車轉(zhuǎn)啊、轉(zhuǎn)啊,發(fā)出一道道白色的光亮,水風(fēng)車打上來的水像一條條小白龍,快活地游進(jìn)了一塊塊的水田里。
大舅守著他的這部水風(fēng)車,與它說話,對(duì)它唱歌,一點(diǎn)兒不覺得寂寞。
許多年后,大舅的村里有了抽水機(jī),水風(fēng)車便退出了歷史舞臺(tái),大舅家里依然珍藏著幾個(gè)木齒輪轉(zhuǎn)軸……
責(zé)任編輯:黃艷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