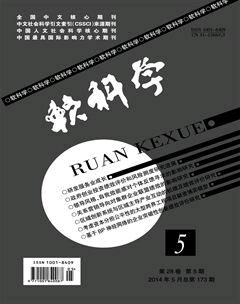研發服務業成長:模式與路徑
簡兆權 王晨 楊金花
在高新技術快速發展和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的條件下,隨著產業對技術及相關支撐服務的需求日益旺盛,研發服務業的興起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隨著知識與信息獲取途徑的增多,企業打破了原有的邊界,并集中優勢發展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以求生存。我國中小企業眾多,沒有足夠的實力進行自主研發,只能借助外部力量,由此催生出新的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服務——技術轉移與技術支撐服務。研發活動的外部化、市場化,使得研發服務業作為一種提供研發技術創新及技術轉移相關支撐服務的產業而出現,并已成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1],研發活動越來越受到重視,研發產業發展速度令人矚目[2]。雖已有研究對研發服務業相關內容進行探討[3],但是作為一種新型產業,其發展模式有無規律可循,將來的成長路徑是否能夠進行預測等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基于這一背景,本文擬對研發服務業的成長模式和成長路徑進行分析,探索其模式形成的影響因素及研發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為研發服務業相關主體提供有益參考。
1研發服務業及其成長
研發服務業是隨著研發活動外部化、市場化的結果而出現的,這一概念開始出現并被廣泛使用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4]。綜合學者的評述,本文認為研發服務業的內涵可以歸納為以知識資本密集為基礎,從事研發活動,通過市場提供智力成果、綜合技術服務的組織和企業的集合。本文依據產業發展規律,借鑒國內外相關專家的研究成果,將研發服務業的成長歷程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60年代,企業內部專職R&D機構開始設立。1876年愛迪生建立了R&D實驗室,成為工業時代企業研究與開發的原型。此后,企業中專門從事R&D的實驗室迅速發展到整個制造業,大規模的R&D科技成果商業應用逐漸成為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第二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前期,R&D活動在企業內部延伸,R&D部門開始與公司內部的生產銷售部門進行溝通。企業根據客戶或市場的需求來決定R&D產品或項目,并從戰略的角度對相關的項目進行系列化、統一規劃管理,構建R&D流程,評估長期技術戰略 [5]。第三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企業的R&D活動逐漸呈現外部化趨勢,內部的R&D活動不再是企業唯一的技術來源[6],通過與大學、研究機構等進行各種形式的合作和外包,成為企業技術獲取的重要方式。與此同時,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到R&D外部化的趨勢,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R&D外部化的問題[7,8] 。第四階段,20世紀90年代后期,R&D產業概念開始出現并被廣泛使用,產業發展初具規模。Gregory Tassey在其研究中首次使用“研究密集產業”的概念[9],R&D也被編入產業目錄[10]。
2研發服務業成長模式
本文從研發服務業價值鏈的發展角度出發,對研發服務業的成長模式進行探討,并將其分為不同階段的四種類型(見表1):研發供求一體的價值鏈模式,研發供求分離的直銷模式,三方參與的雙重價值鏈模式和研發服務價值網絡化模式。
2.1研發服務業準備階段:供求一體化模式
如圖1所示,研發服務業內部一體化價值鏈中,市場需求決定產品,產品決定企業研發內容(包括對產品本身的研發及產品生產方式的研發)。這種價值鏈形成了供求一體化模式,現從影響因素和研發服務主體的相關關系進行分析。
2.1.1供求一體化模式影響因素
首先,市場需求是研發活動出現的重要原因。供求一體化模式中的研發市場需求不是直接來源于外部市場,而是企業自身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彌補產品或生產方式的不足。市場需求與研發供給為間接關聯,市場需求導致企業的產品或生產方式革新才是研發的直接動因。其次,供應鏈慣性也影響一體化模式。客戶壓力和供應鏈慣性都會影響企業管理層的決策[11]。這種慣性影響一直存在于各個企業,許多大型跨國公司將研發、生產、銷售集于一身便是很好的證明。第三,企業內部分工細化對這一模式產生一定影響。研發內部一體化價值鏈是社會分工的一種表現,研發逐步與生產、銷售等部門分離,成為獨立的部門。但是內部研發依舊為產品生產而服務,無論其地位在內部價值鏈中如何變化,始終是產品的附屬,在研發內部價值鏈中處于被動地位。
2.1.2研發主體構成及相互關系
該模式中,研發主體以企業為主,高校與科研機構為輔。三者研發合作較少,在研發供求一體的價值鏈中,企業是一個閉循環體,以提高競爭力與獲得最大利潤為最終目的。組織自身與外界的界限分明,研發主要由組織自身完成,研發合作的需求處于較低層次。高校承擔培養人才與基礎性研究雙向任務,但由于對市場缺乏深入了解,即使研發成果有前途,也因僵化的成果轉移機制而失去市場化的機會。研發機構與高校資源重疊,導致大量重復研究。研發主體之間合作程度較低,基本各自為戰,沒有形成完善的合作體系。
2.2研發服務業萌芽階段:研發直銷模式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大型企業為了降低研發活動的風險,提高研發效率,企業內部的研發活動逐漸呈現外部化趨勢,將研發變成產品,從橫向協作鏈中剝離,加入到縱向供求鏈中。供求直銷模式立足于供求雙方對市場需求的共同理解(見圖2),在雙方信息對稱及相互信任的基礎上產生。這對雙方目標的認知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并多數靠非正式(家人、朋友等中間牽線)的合作關系來實現。但在現實中,往往由于信息不對稱、外界不確定干擾因素及非正式合作關系的局限性而使相互匹配的雙方失去合作的機會。
2.2.1研發供求直銷模式影響因素
首先,研發供求一體化固有的缺陷包括技術創新門檻、技術發展壓力、顧客需求變化及市場競爭加劇,迫使研發逐步走向外部化[12]。其次,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產品加速更新,一些研發項目的內部研發成本遠遠高于外部交易的總成本,企業依靠原有的市場慣性將研發納入內部體系變得不太可能[13]。第三,研發外部化分工使原來的橫向協作鏈與縱向供需鏈發生改變,研發需求與供給分離。一方面,研發從內部橫向協作鏈中剝離出來,不再是附屬角色;另一方面,研發成為獨立的產品參與到縱向供需鏈之中。
2.2.2研發主體構成及相互關系
研發主體逐漸多元化。在原有研發主體的基礎上,一批專門從事研發的企業誕生,以便滿足研發市場需求。它與專門從事研發的科研機構有很大不同,以滿足市場需求為目的,靠自身研發投資獲得后續資金。科研機構在市場需求的促動下進行改制,一部分國有的科研機構轉變為企業,自負盈虧,加入到研發企業的行列。高校開始直接投資企業,創建合作聯盟,興辦科技園,積極尋求與市場聯系。如圖3所示,A、B、C分別代表研發企業、科研機構、高校,及三者間可能組成的聯盟,研發合作變得緊密。企業傳統邊界被打破,尤其是一些自身很難承擔研發風險的中小企業,轉而依靠新型的研發企業。高校與科研機構改制初獲成果,研發需求者開始青睞高校與科研機構。為了更好滿足市場需求,企業、高校與科研機構開始分工合作,在研發中各取所長。
2.3研發服務業發展階段:雙重價值鏈模式
研發支撐業務的外部化是研發服務業成型最重要的成長標志,即第二產品——研發支撐服務的誕生,標志著研發服務雙重價值鏈的逐步完善[2]。
2.3.1雙重價值鏈模式成因
第一,研發服務市場逐漸成熟,原來的研發提供者內部協作開始裂變,將精力集中于研發核心,即第一產品,為研發提供支撐的服務逐步外部化,圍繞研發產品提供的支撐服務逐步成型,成為繼核心第一產品后的第二種產品,并圍繞第二產品形成獨立的供求價值鏈。第二,研發直銷適用于研發市場需求比較少,供求雙方匹配度高,信息對稱的情況。但隨著科技發展的步伐,產生了更多的研發需求,需要有新的市場化匹配方式來支持研發服務的發展。第三,隨著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研發提供者開始聚焦于研發核心,研發支撐服務進一步分離,為研發成果供求者提供支撐服務。
2.3.2研發服務主體構成及相互關系
科技中介作為研發支撐服務的提供者出現在價值鏈中,成為新的研發服務主體,其服務針對研發成果提供者與研發成果需求者展開,后二者都是研發支撐服務的需求者[2]。研發服務主體之間合作日漸緊密。研發支撐服務作為第二產品,使得科技中介成為研發成果供求者之間的橋梁(見圖4)。另外,由于研發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三者的研究側重點及獲得政府資助等的差異,在面對差異化市場需求時,三個主要的研發服務主體開始各揮所長,針對市場需求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合作聯盟,例如產學研聯盟。
2.4研發服務業完善階段:價值網絡化模式
目前,研發服務業的發展層次不齊,雙重價值鏈為主要表現模式。研發服務業的網絡化將成為比雙重價值鏈更為成熟的模式。
相比雙重價值鏈,價值網絡是一個更加成熟的研發服務業模式,以研發服務中介平臺為基礎,以提高價值鏈各交易點的耦合性為目的,主要體現在“第一產品”與“第二產品”的關系定位:在雙重價值鏈模式中,研發成果(第一產品)決定了研發支撐服務(第二產品)。網絡化模式彌補了雙重價值鏈的缺陷,對模式進行完善:第一產品從研發到最終成交的復雜程度與研發服務業整個市場發展的復雜程度和不確定性相關。在研發服務市場中,以增加研發支撐服務(第二產品)供求的復雜性來降低研發成果供求(第一產品)的復雜性。對于處于知識轉移網絡核心的企業來講,認同在創造積極的知識轉移利益機制中起著很大作用。研發服務業價值網絡化模式是知識轉移網絡化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如圖5所示,研發服務主體要受到社會行為、政治力量等外部影響。
3研發服務業成長路徑
通過對研發服務業成長模式的建構和分析,可見研發服務業在每個成長階段的表現主要是圍繞“兩大產品”展開,第一產品——研發成果,第二產品——研發支撐服務[2]。另外,研發服務業作為新型產業,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因此,本文從研發成果、研發支撐服務及政策支持三方面構建研發服務的成長路徑,如表2所示。
3.1研發成果引領路徑
首先,對于內部一體化綜合性企業來講,要注重對項目評估前期的判斷。Chesbrough提到,為了避免假陽性(看似有前景但不被市場接納)的出現,在篩選項目的同時又可能會出現假陰性(看似毫無價值的項目最后得到市場的認可)[14]。因此,研發型企業要提高自身的研發實力,對前期項目的投入把好關口,立足達到投資效益和風險的均衡。其次,增強知識發展能力與研發智力資本。在處于研發服務雙重價值鏈模式下,研發服務提供者需要重塑自身的知識發展能力與智力資本,緊跟價值需求,在滿足自身發展需求的同時,在價值鏈中為合作者提供創造性價值,達到研發服務價值共創的最終目的,使研發服務業得到真正發展。第三,形成研發價值網絡外溢。研發服務業最終的成長模式為研發價值網絡,要求各個研發服務主體根據實際不斷拓展自身的研發邊界,運用開放式研發與創新模式與周圍的研發合作圈達到很好的知識外溢。
3.2研發支撐服務推動路徑
在“第一產品”研發成果得到重點打造的同時,還要重點突顯研發服務的“第二產品”,大力發展同時具備“高知識”與“重服務”的研發支撐服務[15]。首先,要強化精度,準確抓住市場需求信息[16]。不僅研發支撐服務的供求雙方需要建立很好的溝通機制,科技中介也需要構建很好的信譽體制,對市場需求信息進行整理歸類,為客戶解除后顧之憂。其次,要建立深度,滿足客戶的需求。研發支撐服務的提供者應該在原有精度的基礎上積極擴張支撐服務的內容,在需求者未發現自身的潛在需求時,通過預見來把握供求合作的主動性,真正做到“創造需求”。第三,要擴大廣度,通過與研發成果需求者和供應者的合作與深入,構建開放式中介服務平臺,彌補單個科技中介機構的能力缺失。
3.3政策支持路徑
研發服務作為新型產業,市場運行機制尚未成熟,單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很難健康發展,因此,在各研發服務主體或聯盟沒有很好融入市場之前,政策引導與法律規范必不可少。首先,政府要加強研發服務的社會基礎環境建設,引導社會對研發服務價值的肯定,從根本上認同研發服務。大力推動官產學研合作,打破原有資源邊界,整合各路相關人才,滿足研發服務知識多樣性要求;同時構建良好的法律環境,為研發服務的知識產權提供有力保護。其次,要擴大研發服務需求,積極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大力發展科技含量高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促進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尤其鼓勵高科技中小型企業的發展。第三,提高研發服務供給能力。對于高校、科研機構來講,政策重點是引導其融入市場,通過開放式創新將研發知識產權轉讓給外部合作圈,以此獲得雙贏。對于研發企業,政府的公共研究資金投入要根據實際逐步加大,并對資金用途要進行長期追蹤與監督,以免浪費。對于研發服務新型主體——科技中介機構,政策引導與法律規范并行,構建詳細可操作的科技中介運作的法律體系,將科技中介納入研發服務主體支持體系中,對科技中介進行資金支持、政策引導和跟蹤完善,并運用政府職能對其不足進行補救,提高科技中介機構對研發服務價值鏈的耦合性。
如圖6所示,“第一產品”(研發成果)是研發服務業發展的核心,是研發服務業高知識、高技術特征的體現;“第二產品”(研發支撐服務)是研發成果發展的支撐,也是研發服務業區別于其他產業的重要特征;政策引導與法律規范是研發服務業發展的保證。三條路徑共同發展,相互作用,缺一不可。
4結語
本文從研發服務業價值鏈演變角度出發,根據當今研發服務業的發展態勢對研發服務業的成長模式演化過程進行探討,總結出研發服務業的成長經歷了四大發展階段:將研發供求一體價值鏈作為研發服務業的準備階段,將研發供求分離的直銷模式作為研發服務業的萌芽階段,將三方參與的雙重價值鏈模式作為研發服務業逐步成型階段,將研發服務價值網絡化模式作為研發服務業今后發展的方向之一。圍繞研發成果、研發支撐服務及政策支持三方面構建研發服務的成長路徑:從事研發的企業要注意項目前期的綜合評估,在增強自身知識發展能力和研發智力資本的基礎上成為研發價值網絡外溢的一部分;研發支撐服務的發展主要從精度、深度和廣度三個維度展開;政府要加強政策支持,從加強基礎環境建設、擴大研發服務需求、擴大研發服務供給能力三個方面著手促進研發服務業發展。三者相互作用,共同促進,為將來研發服務業的發展提供參考與啟示。
參考文獻:
[1]Zhang R, Sun K, Delgado M S, Kumbhakar S C. Productivity in China's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R&D[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2, 79(1): 127-141.
[2]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1996 (NSB96-21)[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cience Board, 1996.
[3]簡兆權, 楊金花. 研發服務業雙重價值鏈的構建研究[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2012, 33(3): 88-93.
[4]John E. R&D and Global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J]. Management Science, 1998, 44(1): 1-11.
[5]Michael L, Irwin F, Catherine S R. Evaluation of Maines Public Investment in Research & Development[R]. Chapel Hill, NC : Off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1.
[6]黃魯成. R&D產業內涵、成因及意義[J].科研管理.2005, 26(5): 62-67.
[7]Bessant J, Rush H. Building Bridges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Consultants in Technology Transfer[J].Research Policy, 1995, 24(1): 97-114.
[8]Love J H, Roper S.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R&D: A Study of R&D Choice With Sample Sele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2, 9(2): 239-256.
[9]Tassey G. The Economics of R&D Policy[M].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7.
[10]薛求知,王輝. 西方企業R&D的演進及其啟發[J].研究與發展管理, 2004, 16(3): 28-33.
[11]Smith M F, Lancioni R A, Oliva T A. The Effects of Management Inertia on the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of Produce-to-stock Firm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5, 34(6): 614-628.
[12]吳敏輝. R&D產業化研究[D]. 復旦大學, 2003.
[13]劉學. 技術交易的特征與技術市場研究[J]. 中國軟科學, 2000(3): 62-67.
[14]Chesbrough H W.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M].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
[15]Ehie I C, Olibe K. The Effect of R&D Investment on Firm Value: An Examination of US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0, 128(1): 127-135.
[16]Forsman H.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Small Enterpris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J]. Research Policy, 2011, 40(5): 739-750.
(責任編輯:趙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