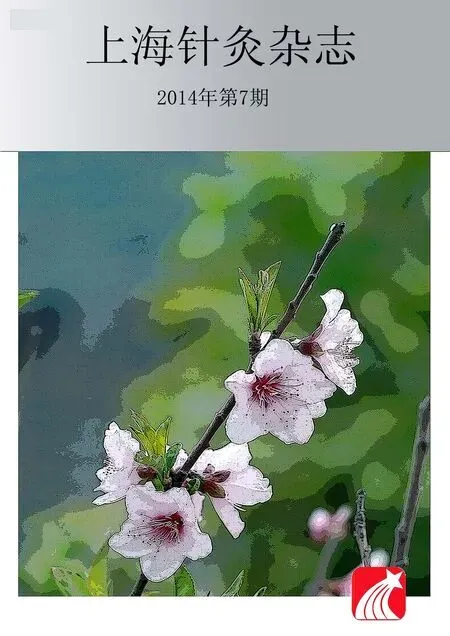不同針灸方法分期治療貝爾面癱療效觀察
陳曉琴,李瑛,邙玲玲
不同針灸方法分期治療貝爾面癱療效觀察
陳曉琴1,李瑛2,邙玲玲2
(1.彭州市中醫醫院,彭州 611930;2.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 610075)
觀察不同分期針灸方法治療成都地區380例貝爾面癱患者的臨床療效。采用臨床隨機對照試驗方法將372例貝爾面癱患者隨機分為A組65例、B組78例、C組75例、D組71例和E組83例。A組采用分期針刺治療,B組采用分期針灸治療,C組采用分期電針治療,D組采用分期經筋排刺治療,E組采用不分期針刺治療。治療4個療程后比較各組House-Brackmann(H-B)分級量表、面部殘疾指數量表(FDI)、面神經麻痹程度分級評分表及WHOQLO-BREF量表評分,并評價各組療效。5組治療后H-B分級量表、FDI、面神經麻痹程度分級評分表及WHOQLO-BREF量表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0.05)。5組臨床療效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0.05)。5種治療方案均對貝爾面癱均有效。在醫療條件受限、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治療貝爾面癱推薦使用單純針刺治療。
針灸療法;電針;貝爾面癱;面神經麻痹;排刺
貝爾面癱臨床以病側面部表情肌癱瘓為主,表現為眼瞼閉合不全,或(和)淚液分泌減少;皺額、蹙眉均不能或不全;鼻唇溝平坦,口角下垂或張口時被牽向健側;病側角膜反射消失;示齒、鼓腮、噘嘴、吹哨任意一項不能或不全;可有舌前2/3味覺障礙,聽覺過敏或聽覺障礙。
由于該病的病因病理尚未完全闡明,西醫目前主要采用藥物和手術治療。因為缺乏足夠強的Ⅰ類研究,目前仍不能明確肯定藥物(如類固醇激素和阿昔洛韋)對貝爾面癱的療效。對于手術治療,目前普遍認為療效尚難肯定,只宜在嚴重患者試用, ,偏倚的危險度較高,因而不能支持循證結論。中醫學認為貝爾面癱不同時期的病理變化是不一樣的,且針灸治療該病的方法較多。本研究主要采用嚴格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觀察不同時期采用不同方法治療成都地區380例貝爾面癱患者的臨床療效,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采用隨機對照試驗方法將成都地區380例貝爾面癱患者隨機分為A組65例、B組78例、C組75例、D組71例和E組83例。5組性別、年齡、病程、分期、神經定位基線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0.05),具有可比性。詳見表1。
1.2 診斷標準
參照《臨床疾病診斷依據治愈好轉標準》[1]和周圍性面神經麻痹的中西醫結合評定及療效標準(草案)[2],確立診斷標準。

表1 5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1.3 納入標準
①符合貝爾面癱的中西醫診斷標準、分期標準[3-5]和定位標準[6];②首次發病;③病程在1~70 d;④一側面肌麻痹;⑤年齡在15~70歲;⑥簽署知情同意書,自愿參加本項研究。
1.4 排除標準
①貝爾面癱繼發于其他疾病者;②合并有糖尿病、心血管、腦血管、肝、腎、肺和造血系統等嚴重原發性疾病者和精神病患者;③亨特氏綜合征患者;④面肌痙攣患者;⑤孕婦及哺乳期婦女;⑥正在參加其他臨床試驗者。
2 治療方法
2.1 針具
選用蘇州醫療用品廠有限公司生產的0.30 mm×25~75毫針,電針儀選用華佗牌SDZ-Ⅱ型電針儀,艾條為蘇州市東方艾絨廠生產的清艾條。
2.2 取穴
取地倉、頰車、合谷、陽白、太陽、翳風、顴髎、下關。鼻唇溝變淺加迎香;抬眉困難加攢竹;人中溝歪斜加口禾髎;頦唇溝歪斜加承漿。5組取穴相同。
2.3 A組
①急性期(1~7 d)面部穴位取患側,翳風取患側,合谷取健側。面部穴位淺刺,合谷、翳風采用常規針刺,行平補平瀉法,輕度刺激。②靜止期(8~20 d)地倉、頰車、太陽、顴髎采用透穴法(地倉透頰車,太陽透顴髎),陽白、合谷、翳風、下關采用常規針刺,行平補平瀉法,中度刺激。針后每個主穴加艾條溫和灸,每穴5 min,以皮膚潮紅為度。③恢復期(21~70 d)操作同靜止期,在主穴基礎上加足三里,采用常規針刺,行平補平瀉法,中度刺激。
2.4 B組
急性期、靜止期、恢復期操作同A組,針后每個主穴加艾條溫和灸,每穴5 min,以皮膚潮紅為度。
2.5 C組
急性期、靜止期操作同A組,靜止期得氣后地倉與下關、太陽與陽白接電針。恢復期主穴加足三里,得氣后地倉與下關、太陽與陽白接電針。
2.6 D組
急性期、靜止期、恢復期操作同A組。靜止期、恢復期采用陽明經筋排刺,即按照陽明經筋循行路線,每隔0.5寸1針,排列成兩排(8~10針)。
2.7 E組
不分期治療,行常規針刺,采用平補平瀉法。
2.8 療程
分期治療各組急性期留針20 min,留針過程中不行針;靜止期、恢復期留針30 min。E組留針30 min。每日1次,5次為1個療程,療程間休息2 d,共治療4個療程。
3 治療效果
3.1 觀察指標
①House-Brackmann (H-B)分級量表(總體評分);②面部殘疾指數(FDI)量表;③面神經麻痹程度評分;④WHOQLO-BREF量表。5組患者分別在治療前后檢測1次。
3.2 療效標準
參考《周圍性面神經麻痹的中西醫結合評定及療效標準(草案)》擬訂標準。
痊愈:H-B量表總體評分為Ⅰ級,FDI量表軀體功能評分≥20分,FDI量表社會功能評分≤10分。
顯效:H-B量表總體評分為Ⅱ級,FDI量表軀體功能評分為15~19分,FDI量表社會功能評分為11~15分。
有效:H-B量表總體評分為Ⅲ級,FDI量表軀體功能評分為10~14分,FDI量表社會功能評分為16~20分。
無效:H-B量表總體評分為Ⅳ級及以下,FDI量表軀體功能評分<10分,FDI量表社會功能評分>20分。
3.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AS9.1.3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檢驗;計數資料用卡方檢驗。
3.4 治療結果
3.4.1 5組患者治療后H-B分級量表總體評分比較
由表2可見,5組患者治療后H-B分級量表總體評分經卡方檢驗,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0.05)。

表2 5組患者治療后H-B分級量表總體評分比較 (n)
3.4.2 5組患者治療后FDI量表各項評分比較
由表3可見,5組患者治療后FDI量表軀體功能總分與社會功能總分經非參數檢驗,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0.05)。

表3 5組患者治療后FDI量表各項評分比較 (±s,分)
3.4.3 5組患者治療后面神經麻痹程度分級評分及WHOQLO-BREF量表總分比較
由表4可見,5組患者治療后面神經麻痹程度分級評分及WHOQLO-BREF量表總分經非參數檢驗,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0.05)。

表4 5組患者治療后面神經麻痹程度分級評分及WHOQLO-BREF量表總分比較 (±s,分)
3.4.4 5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由表5可見,A組總有效率為92.3%,B組為85.9%, C組為88.0%,D組為83.1%,E組為84.3%。5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0.05)。

表5 5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n)
4 討論
貝爾面癱由于其病程有不同分期的特點,臨床分為急性期、靜止期、恢復期,而不同時期其病理特點是不同的,急性期患者絡脈空虛,外邪始中絡脈,邪在衛表,病輕邪淺;靜止期病邪逐漸深入,病情繼續發展或漸趨穩定;恢復期正氣漸復,病情好轉。根據貝爾面癱不同分期具有不同的臨床特點,既往的一些研究涉及到該病分期治療的問題,多數研究結果表明分期治療比不分期治療效果好[6-8]。但課題組采用嚴格的多中心、大樣本隨機對照試驗,已經科學地評價出了針灸擇期治療貝爾面癱的臨床療效,在不同分期療法中,不分期針刺與分期針刺、分期針灸、分期電針、分期經筋排刺治療均為貝爾面癱的優勢治療方案。并根據研究結果,首次確定了針灸治療貝爾面癱的最佳介入時機為發病后的1~3星期,急性期和靜止期介入較在恢復期介入針灸效果好。在醫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在急性期治療推薦使用單純針刺治療,而對恢復期治療不推薦使用單純針刺治療;對鼓索以上貝爾面癱患者不推薦使用分期經筋排刺療法。
本研究主要對成都分中心380例患者情況進行了分析,并采用國際通行的H-B量表、FDI量表、面神經麻痹程度量表、WHOQLO-BREF量表等評價指標進行評價。本研究選擇這些多元化的評價量表進行評價,采用兩種及兩種以上量表聯合應用,取長補短,能更有效地判斷針灸治療貝爾面癱的臨床療效。本研究在針灸治療貝爾面癱的臨床研究中引入相應的生存質量評價量表,對患者治療后的全身狀況進行評估,可充分體現出其治療優勢。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分期針刺、分期針刺、分期針灸、分期電針、分期經筋排刺5種方法對成都地區380例貝爾面癱患者治療前后H-B量表、FDI量表、面神經麻痹程度量表、WHOQLO-BREF量表改善值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0.05),各組貝爾面癱療效也均無統計學意義(>0.05),與課題前期成果一致,即得出結論,對成都區域貝爾面癱患者在不同分期療法中,不分期針刺、分期針刺、分期針灸、分期電針、分期經筋排刺5種治療方案均對貝爾面癱均有效。在醫療條件受限、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治療貝爾面癱時推薦使用單純針刺治療。
[1] 孫傳新.臨床疾病診斷依據治愈好轉標準[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98:198.
[2] 楊萬章,吳芳,張敏.周圍性面神經麻痹的中西醫結合評定及療效標準(草案)[J].中西醫結合心腦血管病雜志,2005,3(9):786- 787.
[3] 王素芳.針灸分期治療周圍性面癱80例臨床觀察[J].現代中醫藥, 2005,25(5):47-48.
[4] 劉宜軍,周友龍.分期針灸治療周圍性面神經麻痹的療效觀察[J].中國針灸,2004,24(10):677-678.
[5] 韓寶杰.分期針藥并用治療周圍牲面癱的臨床觀察[J].遼寧中醫雜志,2006,33(2):212-213.
[6] Peter Duus,劉宗惠,胡威夷.神經系統疾病定位診斷學[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3:211-212.
[7] 李艷,沈特立,曹蓮瑛,等.不同留針時間針刺對貝爾麻痹的臨床研究[J].上海針灸雜志,2012,31(11):812-813.
[8] 楊志新.針灸臨床講座(1)周圍性面神經麻痹[J].中國臨床醫生, 2006,34(1):20-21.
Observations on the Efficacies of Different Staged Acupuncture Methods in Treating Bell’s Palsy
-1,2,-2.
1.,611930,; 2.,610075,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ies of different staged acupuncture methods in treating 380 Bell’s palsy patients in Chengdu area.A clinic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s carried out. Three hundred eighty patients with Bell’s palsy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to groups A, B, C, D and E, 76 cases each. 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staged acupuncture; group B, with staged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group C, with staged electroacupuncture; group D, by staged muscle-region alignment needling; group E, with non-staged acupuncture. The House-Brackmann grading scale scores, the Facial Disability Index (FDI) scores, the Classification Scale of Facial Paralysis scores and the WHOQOL-BREF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groups after four courses of treatment.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as evaluated in every group.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House-Brackmann grading scale score, the FDI score, the Classification Scale of Facial Paralysis score and the WHOQOL-BREF score (>0.05) and in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0.05) between the five groups.All the five protocols are effective in treating Bell’s palsy. Under limited medical conditions and inadequate medical resources, using acupuncture alone is recommended for the treatment of Bell’s palsy.
Cupuncture therapy; Electroacupuncture; Bell’s palsy; Facial paralysis; Alignment needling
R246.6
A
10.13460/j.issn.1005-0957.2014.07.0613
陳曉琴(1980 - ),女,主治醫師
李瑛(1964 - ),女,教授,E-mail:jialee@mail.sc. cninfo.net
1005-0957(2014)07-0613-03
2014-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