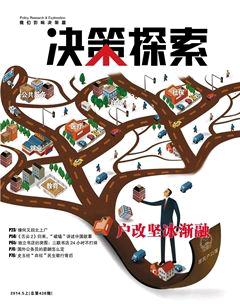“積分入戶”的探尋之路
王曉雅
“就算再難,我也要想辦法成為北京人。”盡管已在北京一家投資公司工作了6年多,薪水待遇更是讓很多人羨慕,但王軍海今年仍然下定決心辭職“考博”。“其實我也挺舍不得的,但是沒辦法,不通過這個渠道,就成不了應屆畢業生,也就很難再有機會解決北京戶口。”
截至2013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14.8萬,其中常住外來人口802.7萬。2014年,進京指標限定1萬人。
按照目前規定來說,落戶北京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類特定人群是應屆畢業生。從2005年起,“留京指標”逐年壓縮,今年約1萬人左右,呈逐步趨緊態勢。第二類特定人群是“千人計劃”、高層次海歸、博士后等特殊人才。第三類特定人群是投靠的夫妻、子女,且“投靠落戶”有嚴格的條件限制。第四類特定人群為商人,有納稅和住房等要求。非上述特定人群,落戶北京只有3種方式:考公務員,應聘有進京指標的企事業單位的部分崗位,考取能解決北京戶口的大學生村官和大學生社工崗位。
2007年,王軍海從北京一所大學研究生畢業。“當時找工作最關注的是待遇,戶口的事真沒怎么上心。”王軍海說,直到2011年結婚生子后,才越來越感到有沒有戶口大不一樣。“就說生孩子吧,有北京戶口的,基本上一天就能辦好準生證等必需的證件,而像我這樣,夫妻倆都沒京戶的,就要分頭回老家辦理,來來回回至少要四五天,而且影響孩子一輩子。”
鬧心的事遠不只這些。“買房買車,戶口都是硬杠杠,即便有變通,條件也很苛刻;沒戶口,子女上學就要比別的孩子多花錢,而且還要面臨高考必須回原籍的窘境……”王軍海說,那頁看似不起眼的戶口簿已成了他人生路上最難逾越的壁壘。“我也曾想過離開,可早已習慣了北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這里的軟硬件確實要高出一大截,孩子在北京成長,未來成才的希望就能更大些。”
最近,保定傳出將承接首都的部分行政事業功能,這讓王軍海似乎又有了新的選擇。“這是不是意味著,以后搬到保定也能享受到和北京人一樣的待遇?”王軍海的眼中閃過一絲喜悅,但又迅速暗淡下來,“即便能實現,估計也要好多年,還是先安心考博,不能誤了孩子。”
如今,類似因戶籍而產生的艱難抉擇,幾乎每天都在北上廣這些大城市上演著。“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糾結局面,就是因為我們的戶籍分量太重。”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段成榮說,在我國,戶籍早已不再是簡單的人口登記手段,而是與教育、醫療、社保等福利待遇緊密相連,成為了配置社會資源的重要手段。“這一點,在北上廣這些特大城市更加突出,它們的戶口含金量更高,聚集的非戶籍人口更多,矛盾自然也就更突出。”
作為城鄉二元發展結構的基礎性制度,我國的戶籍制度一直是制約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的最大藩籬,也是影響農民工市民化的最大制度性障礙。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戶籍制度的堅冰也日益有所松動,因城市規模大小存在不同程度的改革。總體來看,中小城市的戶籍改革環境相對寬松,沒有太多的制度限制。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戶籍改革相對困難,主要是擔心城市承載力有限,放開戶籍之后會導致人員大量擁入,難以負荷。正是出于此種顧慮,使得像上海、北京這種特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一直有些瞻前顧后,甚至表現出停滯不前的狀態。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不僅要放開小城鎮落戶限制,也要放寬大中城市落戶條件。對于特大城市可采取積分制等方式設置階梯式落戶通道調控落戶規模和節奏,這也是首次在國家層面為特大城市的入戶問題正式提出了解決方案。
事實上,“積分入戶”并非全新事物。從2013年7月1日起,《上海市居住證管理辦法》正式施行,持有上海市居住證的“新上海人”迎來積分時代。隨著持證人在上海市居住年限、工作年限、繳納社會保險年限的增加和學歷、職稱等的提升,其分值相應累積達到標準分值的,可以享受子女教育、社會保險、證照辦理、住房、基本公共衛生、計劃生育等公共服務待遇。
上海的積分落戶政策表明,如果取得120分的標準值,就可以獲得上海市居住證。而新版居住證在功能上與上海戶籍相差無幾,包括其子女可在上海參加中高考,其配偶和同住子女也可以參加上海社會保險,享受相關待遇等,僅在親屬投靠、低保領取和經濟適用房購買這三個方面存在差異。
因此,在上海居住證積分制下,“異地高考”得到了制度層面的突破,也成為最大的看點。上海市發改委總經濟師翁華建指出,與過去引進人才入戶的管理辦法相比,居住證積分制突破了本科學歷、職稱等條件門檻,突出了能力和貢獻的導向,為平凡崗位的普通勞動者提供了一個融入渠道。
上海的居住證積分制度,簡單來說就是以積分換公共服務,并非其首創。2010年廣東就在全省范圍內推廣“積分入戶”制度,外地在粵務工者只要積分達到一定標準就可以申請入戶。與廣東實施的“積分入戶”制度相比,上海的居住證積分制度雖然在具體操作上有所差異,不過究其核心,都是通過個人情況和實際貢獻的累積,賦予其享受與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的權利。應該說,這是我國戶籍制度改革中的一大創舉。
當然,城市不僅對人口的數量有控制,對人口的質量也有追求。這一點,從各地“積分入戶”政策的制定上便能窺知端倪。如廣州對“教育部重點建設高校、211工程高校、985工程高校、廣東省屬及廣州市屬重點高校或其他重點高校”的畢業生加10分,對“個人在廣州市企業的投資額在5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加20分;中山制定的附加分指標包括個人基本情況、急需人才、專利創新、獎勵榮譽等10項內容。
總結已經實行積分落戶城市的標準來看,年輕、學歷高、有較高專業技術職稱和技能等級、繳納社保時間長、遵守計劃生育政策、沒有違法犯罪記錄的人,更有可能落戶大城市。
一些學者在隨后的調研中發現,對于普通農民工來說,門檻仍然很高。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顧駿指出,普通農民工如果學歷不高,那積分就少得可憐。“盡管工作年限增加會帶來積分,但一年只有2分,而過了40歲后,最高不過30分的年齡積分,每年還要倒扣2分,什么時候能積滿120分?”在他看來,如果各地都采用這種自我本位的“準入門檻”,中國的城鎮化可能將變為“精英城鎮化”。
“很多在城里的人希望這個城市的人口是有一定素質的人,希望要達到一定的學歷,要達到一定的專業技能才能進入城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認為,可各種低端服務是一個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只剝奪他們的剩余價值,不解決他們的公共服務問題,不解決他們在這里長期生活的困難。”
正如中國社科院當代城鄉發展規劃院院長傅崇蘭所說,“都是學者、博士后、科學發明家,肯定是難以為繼的”。多名學者表示,積分制度的考核方式是否合理并不是最重要的,是否公平才是關鍵。建議積分設置標準要更有操作性,針對不同特點、不同類型的人口,設定多元化指標推行積分標準,避免“一刀切”。對人才的評價,可以分行業、產業制定落戶計分指標,可先圍繞一些亟待發展的重點產業先行試點。
上廣深三地的政策,盡管不完美,甚至有著種種爭議,可這畢竟讓漂在這些城市的外來人口,看到了融入城市、安家落戶的希望。
繼廣州、深圳實施“積分入戶”制度之后,作為國內一線城市的上海,也通過居住證積分制度,向所有外來務工者打開了城市的大門,其破冰意義顯然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