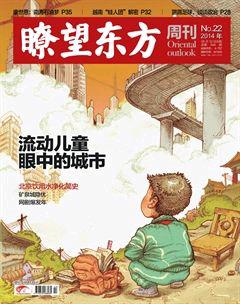“植物獵人”中國探險
王亞宏



當北京連續經歷35攝氏度以上高溫,大家紛紛賣萌般“求被打入冷宮”時,在8000公里外的倫敦,英國人查爾斯·林奈對于18攝氏度的溫度已經滿腹抱怨。
“這么熱的天氣,花都快受不了了。”林奈說。42歲的林奈是一名園藝師,他帶著自己的作品參加一年一度的切爾西花展,在他看來,這樣的溫度下一些新采摘的鮮花要熬過5天的花展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已經做好第三天就換掉一些花的準備。
中國植物裝點英式花園
2014年是英國皇家園藝協會第101次舉辦切爾西花展,中國主題也首次出現在這個全球最大的花展上。一些熱衷園藝的人在今年的花展上會發現,他們花園里多年種植的一些花草比如百合、牡丹以及繡球花等,其實最初都源自中國。
來自英國西南康沃郡的卡爾漢思城堡,用其花園里培育的101種中國植物組成了巨大的園藝作品參展。
城堡的主人查爾斯·威廉姆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看到了這個關于中國植物的展覽,人們會意識到一些在英國花園中常見的植物其實是來自中國,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植物的歷史,以及它們為什么能在花園中茁壯成長。”
在花展上露面的中國原產植物,最早都是查爾斯的祖父J.C.威廉姆斯收集的。老威廉姆斯是位業余植物學家,他在世的19世紀正是英國博物學最繁盛的時代。
當時借助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的成果,有興趣有實力的英國貴族們致力于收集各國奇珍,但并不是每個博物學家都會像達爾文那樣拿出幾年時間,以身赴險用全球旅行來收集第一手資料。
這就催生了一個特殊的探險家群體,他們踏遍千山萬水,將收集來的各種物品高價賣給有需求的收藏者和研究者。這些探險家中既包括斯文赫定這樣聲名狼藉的文物大盜,也包括“植物獵人”這個低調神秘的群體。
在一個多世紀前,卡爾漢思城堡的老威廉姆斯就資助了一批“植物獵人”到中國收集珍奇的種子,并將獲取的植物培育生長至今。
一個合格的“植物獵人”,不但要有足夠的勇氣、強壯的體魄在野外渡過一次次難關,還要有豐富的知識和扎實的植物學功底,以幫助其辨別哪些植物值得收集。
“那可不是一份安全的工作,在人跡罕至的地區,植物獵人們要冒著一不小心就會從山上掉下去的危險。還有的植物獵人不慎誤入流沙區,很快被吞沒。還有人千辛萬苦找到了稀有的植物,但在采摘時劃傷了自己,結果嚴重感染。”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泰豐資本的首席投資官葛涵思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泰豐資本連續幾年為卡爾漢思城堡參加切爾西花展提供贊助。
在“植物獵人”受到資助開始進入中國尋找稀有植物的同一年,英國皇家園藝協會搬進了倫敦切爾西區。幾年之后,當切爾西花展開始舉辦時,英國上下掀起了園藝熱潮——甚至接踵而至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沒有阻礙這種熱情——而園藝熱又加大了人們對植物品種的需求,從而鼓勵“植物獵人”尋找更多植物來裝點園藝。
“中國威爾遜”
為了給城堡里的花園收集足夠多的來自神秘東方的植物,當年老威廉姆斯資助了恩斯特·威爾遜、喬治·福雷斯特以及弗蘭克·沃德等多名“植物獵人”,這些“植物獵人”都在探險史上留下了一段段傳奇。
恩斯特·威爾遜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最有名的“植物獵人”之一,在他1930年死于交通事故之前,共收集了4000多種亞洲植物運往英國。由于他長年在中國活動,在英國博物界有“中國威爾遜”的綽號。
威爾遜是在花園里長大的,從小對植物就有濃厚興趣。他13歲時輟學當了學徒花匠,三年后被推薦到伯明翰植物園培植花木。1896年,威爾遜在園藝技術考試中贏得“女王獎”,這使他得以進入英國皇家植物園丘園,隨后取得了皇家科學院植物學講師的資格。
正當威爾遜準備從事教學工作時,一個全新的機會展現在面前。他被頂頭上司、主管丘園的老威廉姆爵士看中,受托開始了他在中國西部長達12年的植物采集歷程。
1899年春,威爾遜第一次進入中國,他此行的目的只為尋找著名的觀賞植物珙桐。珙桐又稱“中國鴿子樹”,是與大熊貓同時期遺存的古老物種。自30年前法國傳教士達維在四川發現珙桐后,西方園藝界一直想引進這種植物,但一直未找到蹤跡。
根據前人留下的線索,威爾遜經歷了一年多的跋涉,深入巴東地區,歷盡千辛萬苦終于發現了珙桐,而且他那趟探險還有另外一個收獲:他在宜昌西南部考察時,發現了中華獼猴桃。他將這種植物介紹到西方,現在“奇異果”已經成為新西蘭重要的出口水果。
在完成第一次探險后,威爾遜后來又三次前往中國,前后探訪云南、湖北、四川等地,為要找尋新品種的植物甚至上到西藏高山。他尋訪后帶到英國的植物,包括 “高傲的瑪格里特”黃花杓蘭、“帝王百合”岷江百合、“花中皇后”月季、“華麗美人”綠絨蒿等。
面對在中國看到的眾多植物,威爾遜感慨道:“如果沒有早先從中國大花園引進的品種,我們今天的園林和花卉資源將是何等可憐。”
為收集這些植物,威爾遜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1910年他第四次前往中國時,在岷江河谷邊遭遇山體塌方,右腳被石塊砸斷。一個月后等他到達上海時傷口已嚴重感染,右腳落下了終生殘疾。之后由于身體原因,威爾遜結束了“植物獵人” 生涯,開始著書立說。
三年后,威爾遜出版了《一個博物學家在華西》,他給中國極高的評價:“在整個北半球的溫帶地區的任何地方,沒有哪個園林不栽培數種源于中國的植物。”他稱中國為“世界園林之母”。
死于云南騰沖的“杜鵑花之王”
威爾遜涉獵頗廣,比他晚幾年的福雷斯特則專精杜鵑。藥劑師出身的福雷斯特很早就了解了許多植物的藥用價值,也懂得如何干燥、分類和制作植物標本。29歲時他結識了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的包爾非教授,再次學習了生物學知識,尤其是掌握采集植物標本的技能和知識。后來他也在包爾非教授的推薦下成為一名“植物獵人”。
福雷斯特曾數次來到中國,足跡幾乎遍及中國西南地區,為西方植物研究機構采集了3萬多份干制標本,也為西方園林界收集了1000多種活植物,最有名的是大量的杜鵑花。
福雷斯特采集的中國杜鵑花標本曾被作為新種描述過的達400多種,經過近百年的研究至今仍被接受的名稱有150多種,這些種類的模式標本成為英國從事杜鵑花分類、區系等領域研究的重要材料和依據,福雷斯特也因此被譽為西方的“杜鵑花之王”。
除杜鵑外,福雷斯特帶回英國的還有收集到的大量種子、樹根和植物,包括著名的將軍百合、橘紅燈臺報春和高穗報春等。
為了收集這些植物,福雷斯特曾常年行走于怒江流域,他對當地人非常尊敬和友好,還利用藥理學知識給當地人治病,自費給成千上萬的云南人接種天花疫苗。至今威廉姆斯家族還留著福雷斯特11次前往中國收集植物時留下的大量照片。
而拍下那些珍貴歷史照片的福雷斯特,就是在最后一次在中國探險的途中死于云南騰沖,至今在他去世的地方還能找到“洋人墳”這樣的地名。
中國傳入英國的植物影響至今
“植物獵人”除了尋找種子外,沿途還采集了大量植物標本,每一種都可以對照充實當時植物學的門綱目科屬種分類,大大推進了植物圖譜的建立——比如蘇格蘭愛丁堡的皇家植物園后來之所以能成為世界杜鵑花研究中心,福雷斯特功不可沒。
帶回英國的種子同樣影響巨大。由于英國的氣候條件與中國西南相似,土壤都呈酸性,因此大批原產中國的植物在那里茁壯成長,其中一些適應性強的植物很快傳遍英國全境。
當“植物獵人”們歷盡風險回到英國后,他們會得到熱情歡迎和豐厚回報,“人們都想聽他們講述冒險經歷,也想參觀他們帶回來的新品種植物。”葛涵思說。
當年“植物獵人”們遠赴重洋搜索到的品種,早已成為英國園藝里的重要組成部分。葛涵思感慨:“很多人其實并不知道中國對目前英國園藝的影響有多大。在花展上看到這些原產于中國的植物,有助于吸引全世界的人去中國觀光,也會讓人們知道中國不僅有長城,還有美麗的花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