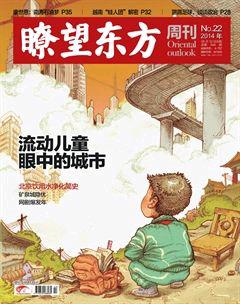顧彬:希望和孔子、老子、莊子見面
沈杰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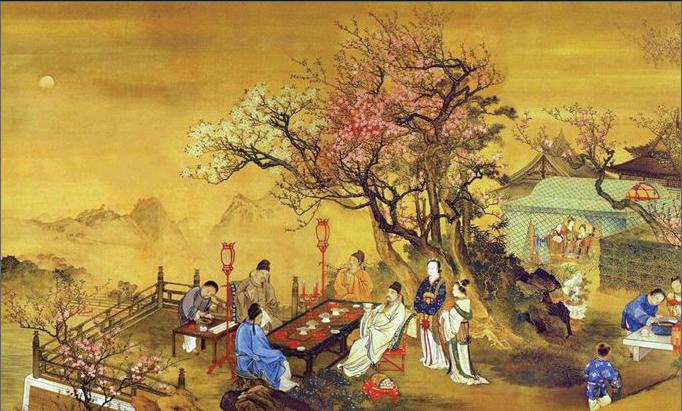

別再談論花開,它們早就建議,
也別再談論樹,你最好對玉石、
泉水和山巒,沉默。
一切早在一手之下。
這惟一之手不是你的,
它是守佛之手,
守護佛的睡眠和所有的睡眠,
在久醉的大地。
4月的晚上,在北京一所高校,顧彬講完課后,邀請了一位來自上海旁聽的女生朗讀了上面這首詩——他寫的《在香山》,還邀請了一位男生朗讀了中國13歲小詩人朱夏妮的《耶穌》。
隨后,顧彬又用德語朗讀了一遍《在香山》,非常用心、用力。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小時候老師就教導朗讀時該如何站立,眼睛看著哪兒。
早在1966年,還在德國北方的明斯特大學學習神學的時候,顧彬就經常參加朗誦會。顧彬認為,好的朗誦可以打破時空限制,了解、認知過去作者的寫作。
不可避免地,他又說到中國作家的朗誦。準確地說,他是在批評,一如既往的犀利。他對本刊記者說,除了王蒙、張承志、楊煉等人,很少有中國作家擅長朗誦。
他提到作家余華,他說在波恩大學余華受邀朗誦自己的作品,但他拒絕站在講臺前,想讓他的德文翻譯朗誦。顧彬再三邀請,結果余華的朗誦“沒有味道,沒有意思”。
講臺上的顧彬不茍言笑,講桌上整齊地平放著他一直帶著的《精選漢德德漢詞典》,朱夏妮的《初二七班》,還有一本他在德國出版的詩集以及關于德國詩人格仁拜因的一本書。
課程結束后的晚上8點,有些疲憊的他推著自行車,找了一家咖啡廳接受本刊記者專訪。
李白的詩抓住了我的心
如此一個顯得有些刻板的老頭,盡管被稱為“德國的李白”,卻怎么看也沒有李白的瀟灑。
他之所以被稱為“德國的李白”,很大程度因為與中國文化的結緣起自李白。1967年,還在大學學習神學的顧彬讀到了譯成德文、英文的《送孟浩然之廣陵》。他對本刊記者回憶:“李白的詩太美了,它抓住了我的心,讓我有了學習古代漢語的沖動”。
那年10月,顧彬23歲。他開始上德國第二代漢學家司徒漢的古代漢語課。文藝青年顧彬開始計劃逃離設定好的牧師人生。
1969年,因為“文革”,他沒有辦法來中國大陸,去了日本,尋找李白的唐朝。他覺著自己找到了,那里有他喜歡的中國古代文化。回德國后,他決定學習現代漢學。
其時,雖然司徒漢等德國漢學家的古代漢語掌握得很好,但基本都不會說現代漢語。曾有一位教授對顧彬講:“你們學現代日語、現代漢語,也只能用來點點咖啡而已,沒有必要學什么現代語言。”
這個思想顧彬抱持了很久,一直到他有機會來中國,他遇到了第一個主張學習現代漢語的德國漢學家霍福民,霍福民強烈建議他到中國來。29歲的顧彬,到北京語言學校開始學習現代漢語。
至于他酒后寫詩的傳言,完全是誤讀。“我需要腦袋清醒,我的寫作太復雜。中國的酒讓人太舒服、太高興、太愉快,酒后無法進行嚴肅的寫作。”他說。
中國作家更需重新學習漢語
與顧彬的對話中,有幾個關鍵詞是他常常提起的,比如傳統、語言、翻譯等,他想集中表達的是對漢語、對語言的責任。
一個外國人,談到對漢語的責任,聽起來似乎有些滑稽。言及此處的顧彬對本刊記者自嘲:其實中國的文人是我,我一直在用中國傳統的觀念寫作,我的文字中充滿了中國傳統、中國古代哲學的觀點。
這也是顧彬一直批評中國作家的關鍵所在。“海德格爾、伽達默爾都說過,除了語言我們什么都沒有,語言是一切,語言是我們的故鄉。”
顧彬覺得當代大部分中國人只是把語言當作工具。他說中國傳統經典《莊子》、《道德經》中的每一個字都是思想本身,這也是它們為什么能對德國思想界產生影響的原因所在。
顧彬更喜歡用德國來說中國。他說“二戰”以后,德國的作家意識到必須重新學習德文,因為德國的語言已經被政治錯誤使用了。同樣的情形發生在中國,中國的語言也有被政治破壞的歷史,中國作家更有必要重新修復、學習漢語。
他認為中國的語言在時代變換中產生了很大的斷裂:“如果我們要了解王家新、歐陽江河,可以把所有的中國傳統剔除不看,但卻需要好好學習西方文學史。而只有少數的詩人才會到中國傳統中去,比如翟永明。”
對于中國當代詩歌,顧彬的評價非常高。他認為中國當代詩人有幾位是世界級的,只是很遺憾,中國當代詩歌與傳統是斷裂的。中國當代散文同樣如此。
傳統,往近了說,在顧彬的坐標軸上是魯迅、周作人的散文。往遠了說,他把坐標軸上的刻度放到了《詩經》、韓愈、歐陽修、蘇軾等人身上。
顧彬自己寫一首詩有時候需要一個星期或一個月,甚至更長。他一直堅持在詩中不用“愛情”、“心”這樣的詞語,他解釋說,這些詞語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只是別人用得太多了。他又補充了一句,這樣的詞匯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勉強使用。
“我希望和孔子、老子、莊子見面”
年輕時的顧彬做過許多夢,諸如神學家、音樂家、足球運動員、導游、中學教師等。這位被稱為“書桌前的苦行僧”的漢學家看起來比常人都喜歡做夢,而且許多夢一做數十年。
“首先我希望能夠成為德國的李白;第二能夠回到唐朝去;第三我希望能夠和孔子、老子、莊子見面——大概老子不太可能,他存在與否是個問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他們若能在天空等我,就好了!”
顧彬給本刊記者講這些的時候滿臉童趣,雖然話題有時難免陰郁。對這個在“死亡之都”維也納生活過的漢學家來說,他的詩總是在憂郁、墳墓、死亡、異鄉等主題中穿行。他說德國人總是背負著“罪”——“二戰”時期的“罪”,所以他總是在思考著死亡。
他還喜歡去墓地,常常去拜訪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大師的墓地。他說:“歐洲的墓場很漂亮,是博物館,可以了解我們的生活和生命。”在北京,他覺著最好的墓地是萬安公墓。朱自清、戴望舒、王力都長眠在那里。說到此處,他神采奕奕,似乎自言自語:“他們都還認識我,對我說,你又來了,很高興你來了。”
顧彬知道中國人不喜歡談論死,他曾經帶中國作家、文人參觀歐洲的墓地。“他們顯然無法理解墓地的含義”。他說莊子認為死亡就是我們的另一種狀態,所以“他們沒有學好莊子”。他還說,蘇格拉底有個有意思的說法:我們要學會死亡。孔子也說我們死的時候才完成我們的生活,才是我們的生命。“所以死不一定是可怕的,死是好的。”
顧彬的妻子張穗子曾對北島說起他的憂郁,“有人表面挺樂觀的,結果扭頭就自殺了。我們顧彬看起來憂郁,但沒事兒。”
在提出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論”后,顧彬聽到了許多批評,有些更近乎侮辱,他曾經想寫信反駁,最后還是沉默。一些中國作家支持他,歐陽江河就勸他對這些言論“別說話”。
他很高興地對本刊記者說:“莫言比較開放,他接受了我的批評。所以我非常重視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