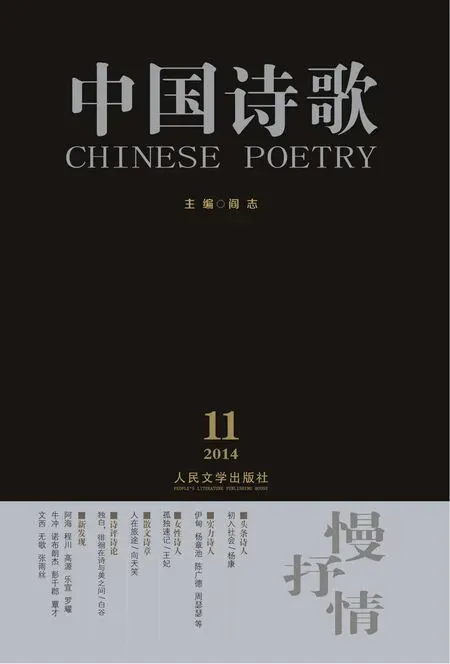李鋮的詩
2014-06-19 06:52:04LICHENG
中國詩歌
2014年11期
LICHENG
李鋮的詩
LICHENG
六月
汗水,瘋長的草
喜歡在六月漫游,同流合污
母親躺在竹床上,不打針,不吃藥
一把破蒲扇,打破三五天的寂靜
就好起來了,一好起來又彎著
一頂舊麥帽,不住點頭
麻地、稻田、菜園……
天沒亮,晶瑩的露珠,不知哪顆是母親身上的
好多年了,兒女像草一樣長大
無數個六月,戴上大紅花
竹床、蒲扇、薅草的鋤頭
離一個人,越來越遠
大把大把的陽光,越來越毒
山丘上的小土堆,越來越多
早晨起來,風隨便輕輕一觸
就驚動一棵草
就驚動一顆珠子大的汗滴
七月半
昨夜,沒有風聲
只有灰燼,在大地的角落
畫了好多圓圈
圓圈,一點點硬起來
像小時候,滾的鐵環
沿著母親走過的路
一條龍,北街、東街、西街
不能再往前走了
前面是車站、碼頭,還得過河
過了河,就是一望無際的稻田、麥地
那么多小路,蜿蜒、凹凸、積水成淵
我得把鐵環背在肩上
望一眼,身邊的草地、荊棘、牛羊
遠方的山坡,云霧
繼續小心翼翼
糖汁
雨,下著密密麻麻的糖汁
我家陽臺上的花盆終于蘇醒
它露出春天般的臉
用母親的微笑向我招手示意
整個早晨,我好陽光,好明媚
仿佛回到二十年前,一塊稻田邊
風是綠的,風蕩漾出的水波也是綠的
看著陽臺上的花盆,花盆里的花草
看著密密麻麻的糖汁下個不停
看著無名的山雀在空中呼來喚去
我相信鄉下所有的事物都變年輕了
像水蜜糖一樣的年輕
臂
它長在肉體中
如杠桿,支撐靈魂與信仰
這比身體還寬的骨頭
如彈簧,收縮有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