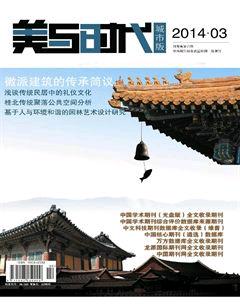由“庖丁解牛”觀莊子美學
田恬
摘要:
莊子是道家思想的繼承和發揚者,他于道的理解和感悟在中國古代是最具開放性和藝術性的。在《莊子》一書中,莊子塑造了許多藝術形象,并常常以寓言故事的方式暗喻其“道”。庖丁就是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形象之一。庖丁解牛之道,比較真實地表達出莊子對道的感悟。
關鍵詞:莊子;庖丁解牛;道;美學
莊子的思想明顯屬于老子的體系,但他們的思想卻有所區別。在對宇宙本體“道”的理解上,老子更多注重道的客觀性,莊子則更注重道的主觀性。老子更多地論道是什么,而莊子則更多地論如何體道。與之相關,老子的道論更多的是哲學,然莊子的道論雖然也是哲學,卻增加了不少心理學的成分。老子哲學重辯證法,莊子哲學重相對論。前者反復論述事物的相輔相成,后者則談論事物在“道”這一本體上的一致,淡化事物的區別。
莊子對藝術持肯定態度。他看到了藝術陶冶人的心靈和培育人性的作用,也看到了藝術創造之于人的精神追求的作用。從促進人的身心健康、構建理想人格的高度來認識和要求藝術活動和藝術作品。
莊子美學并不討論藝術的社會功能、教化作用,它所觸及到的是有關藝術創造和藝術欣賞的規律和特點。這里的藝術觀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藝術觀,它主要是在論及人的生產、技藝活動和精神修養時,大量地、精深地涉及到的與藝術活動相似,以致完全相同的一些規律、特點。《莊子·外物》篇說:“言者所以在意,一得意而忘言。”這里說的不止是一般的語言文字與意義的關系,實際上是藝術創造、審美欣賞的帶規律性的特點。它告訴我們,藝術創作、欣賞要善于把握審美意象,體味藝術意境。同樣,老子“大音希聲”的命題,莊子“象閣”說和“至樂無樂”的觀點,都極為深刻地道出了藝術活動所達到的境界。
“庖丁解牛”出自《莊子·內篇·養生主》。故事說庖丁解牛非常神奇,其刀專在骨頭縫隙中運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而且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為什么能做到這樣呢?庖丁回答說:“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從這段文字中,能明確知道解牛理論中所反映的莊子的美學觀點。
一、解牛之由技入道
從文章看,庖丁是從技術層面逐漸進入道的層面,這個過程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解牛之始,“所見者無非全牛者”;第二個階段是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第三個階段是方今之時,“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乃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解牛技術并不是天生就有的,也需要有一個學習的過程。解牛之初,庖丁眼中的牛都是客觀存在的、真實的、完整的牛。庖丁對牛的筋骨結構并不了解,他看到的只是一個完整的牛的形體。因此,牛與庖丁之間的關系,存在著物與物之間的客觀對立。三年之后,從技術角度看,庖丁已經做得非常嫻熟。牛的整體的概念已經消解,而庖丁與牛的物物對立也逐漸消解。庖丁對于牛的各個部位的結構走勢了然于胸。到了第三個階段,庖丁“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容知止而神欲行”,庖丁與牛的對立徹底消解,逐漸融合為一,達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五官的感覺已經不再左右庖丁的行為,而單憑道的感知推動其肢體的運動。
由此可見,庖丁對技法的千錘百煉最終進入巔峰狀態,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澄明世界。而由技入道的根本顯現,則是“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而更直接的表現則是“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
二、解牛之精神享受
庖丁解牛技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其藝術性表現在:“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庖丁解牛體現了由高超的技術所成就的藝術性的效用,使看似純技術性的宰牛技術超越了實用性而產生了可供人們精神享受的藝術性。由于達到“進乎技”的“道”的至高境界,庖丁在解牛過程中并非被動,其動作所發聲音或“砉然”,或“響然”,或“騞然”,這些聲音在音質與音高方面各有特色,使其具有音樂技術美之音響美的要素。它們在解牛過程中是按照有序節奏而發出,紛繁多樣但又合乎節奏,所以才產生“莫不中音”的效果,這又符合了音樂美的特色。
由于勞動過程是在一定的時間段中展開,庖丁以其充分的精神自主性全神貫注地從事自己的事業,使得各種聲音在整體上具有變化統一的協調性,從而形成類似一首樂曲的效果。庖丁在解牛過程中的動作極其復雜,分別為手觸、肩倚、足履、膝踦,但庖丁的每一動作之間又配合得那么和諧,因此能給人一種視覺之美的享受。這種全身心的整體運動又是伴隨著“莫不中音”的節奏而展開,所以解牛過程又產生了類似于一場配樂舞蹈的效果。而且庖丁解牛的技藝極為精湛,其動作展開時的意識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其每一個動作的技巧表現都“游刃有余”,從而達到了如經典樂舞一樣的境界,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解牛”是種艱難而辛苦的勞動,但庖丁解牛完畢后“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的神態也充分表明,他也同樣享受到了演奏的快樂。“技術美學的研究,正是人類勞動生產和工業生產的技術審美活動和技術產品的時髦鑒賞力問題。它把美學應用于物質生活和精神享受中。藝術審美能力,必然也是技術審美能力發展的結果。”如林同華所言,從“庖丁解牛”這一寓言中可以找到這段話的源頭。
莊子通過“危丁解牛”的故事討論了“技”與“道”的關系,實際上又涉及到了藝術的創造問題。它揭示了:真正的藝術創造,是種合乎規律、目的的自由活動,它需要的是純熟的藝術經驗而不是刻意做作的矯飾。當創造和欣賞進入自由無礙的境域時,就可以“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獲得并非有為卻又有為的效果。因此,庖丁解牛之道,便是對莊子之道的完美闡釋。
【參考文獻】
[1]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M].上海:中華書局,1983
[2]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林同華.超藝術:美學系統[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4]蒲鵬英.先秦儒家道家美學思想比較[J].內江師范學院學報,1988(01)
[5]王斐.從“庖丁解牛”看莊子的人生境界[J].社科縱橫,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