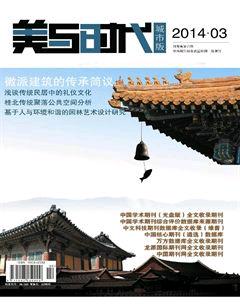淺析中國木版年畫與日本浮世繪版畫的異同
王穎 馬佳明
摘要:
中國木版年畫對日本浮世繪版畫的產生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中國年畫啟發并發展了對西方后印象畫派有深遠影響的日本浮世繪。
關鍵詞:中國木版年畫;日本浮世繪版畫
中國木版年畫在清盛期康雍乾三朝時期最為輝煌。畫店作坊最多時達50余家,題材以描繪城市生活和市民風俗為主,尤以景物、仕女和文學、戲曲、歷史故事為最典型。中國四大民間木刻年畫有蘇州桃花塢、天津楊柳青、山東濰坊、四川綿竹的木刻年畫。天津楊柳青年畫因地近京畿,明顯受宮廷繪畫影響;山東濰坊、四川綿竹等地的年畫更為接近廣大農村地區,最能體現農民審美傾向,更顯原始和質樸;而蘇州桃花塢年畫最受文人畫傳統和外來文化影響,其市民化的特征表現得最為明顯。在日本古典美術中,浮世繪的知名度最高。浮世繪樣式的發展主要是在木版畫形式上進行的,因此,人們提到浮世繪,往往專指木版畫形式,其中以刻繪美人畫、歌舞伎俳優畫和風景畫居多。在浮世繪中還出現了模仿桃花塢木版年畫的作品。這種與中國明清版畫在文化上的同源性,使日本藝術家們所面臨的問題以及為此而進行的嘗試和努力,都與中國的同行頗為相似。首先是透視和明暗畫法的運用,成為了在“西畫東漸”的大背景下,向日本輸入西畫技法的“二傳手”。如1740年日本出現了具有透視效果的“浮繪”,以線條方式來追求空間深度表現;而在中國俗稱“西洋鏡”的西方游戲具也就通過長崎傳入東瀛,透過鏡頭可以看到描繪的風景畫具有很強的透視效果,繪制的畫片也因此被稱為“眼鏡繪”。這些版畫中的西畫因素比1783年司馬江漢(日本早期西畫代表性人物)制作的日本第一幅銅版畫《三圍景》要早40余年。日本藝術家們既有執著傳統的精神,同時又大膽吸收外來文化,具有開放意識和融合性,從而最終積淀起真正屬于自己的藝術傳統。
同是版畫,但是蘇州版畫與浮世繪版畫既有共通性,也存在個性上的差異。
受中國繪畫的影響,在日本浮世繪的孕育、發展過程中,中國的版畫藝術曾經起到過不容忽視的促進作用。浮世繪版畫與中國版畫之間存在著無法割裂的密切聯系。最明顯的共同點就是:一,多法互融。從現有漳州木版年畫舊樣來看它的構圖明顯繼承了明清插圖版畫的傳統,同時還靈活運用多種優良的民族傳統形式,包括漸已失傳的古代界畫、宋元花鳥人物畫、院畫、連環畫、甚至西洋繪畫等因素。浮世繪技法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日本傳統繪畫的精華、中國以及西方繪畫藝術。浮世繪是以日本“大和繪”的屏障畫、描寫閨情與尋常世態的“繪卷”和古典小說的木刻插圖基礎形成的,同時也吸收了大量外來藝術的精華。二,題材一致,大都是表現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內容包括歷史故事、神話傳說、戲曲故事、美人兒童等。尤其是浮世繪畫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女性作為描繪對象,是浮世繪一大特點,如歌舞伎雅集、農家女收割、紡織女煮蠶繭、平民女子出行等。在表現這些市景民俗時,藝術家們力求在審美上達到帶有純粹日本精神的古典和歌式的境界。
而他們的不同點也有許多。其一,人格意識。木版年畫里的漳州木版年畫是民眾集體意識的產品,絕大多數作品都不寫作者的名字。而浮世繪畫家卻大方地在作品上簽字畫押,留下自己的姓名或畫坊店號。其二,不同的藝術個性。中國木版年畫極富象征性,將豐富的意味性主題如神、鬼、人物、動物、文字等用作符號,通過比喻或暗示來傳達創作主旨。而浮世繪則強調感觀性和工藝性,這與其所具有的招攬觀眾等實際功能是分不開的。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日本藝術家在本土繪畫與外來繪畫的碰撞中,不僅樂干學習與模仿,更善于交融與雜揉,不斷攝取養分,探索出適合本民族的獨特風格和嶄新的藝術形式。但需要指出的是,浮世繪的產生與發展,與中國版畫有直接關聯。如浮世繪的美人畫、春興摺物(猜謎用印刷物)、芝居番付(戲劇節目單)、雙六(玩具繪)及一些繪本,在內容與形式的表現上均與蘇州版畫相似。“明末清初的彩印插圖本,對浮世繪版畫的‘紅摺繪之成立,”則“不無影響”。錦繪的套色印刷,據載也是“模仿中國的套色版畫……在版上刻見當,試印四、五次之后,逐漸改良成功的”。可見,日本浮世繪離不開對中國版畫的攝入與再創造。
從東方藝術的特性來看,中日兩國藝術關系的密切,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中國年畫啟發并發展了對西方后印象畫派有深遠影響的日本浮世繪。正如日本畫家中村不折氏在他的《中國繪畫史》序言中說:“中國繪畫是日本繪畫的母體,不懂中國繪畫而欲研究日本繪畫是不合理的要求。”因此對于民間藝術,我們既要研究和發掘其自身價值和潛力,也要注重結合與借鑒國內外其它姊妹藝術,弘揚優良傳統以促進其發展,為創造新時期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化添磚加瓦。
【參考文獻】
[1]秋山光和.日本繪畫史[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
[2]石琪.吳文化與蘇州[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2
[3]王樹村.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香港:嘉實出版社,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