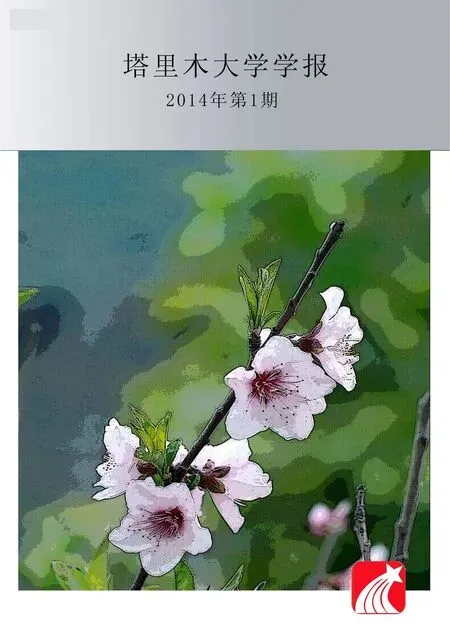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新疆高校少數民族外語教育認同狀況調查分析
嚴兆府 姚小玲 盧鴻進
1 研究背景
少數民族外語教育(主要指英語)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年來,新疆少數民族“雙語”教育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外語教育較為薄弱,尚處于探索階段。新疆部分高校為非英語專業少數民族學生開設了一年的基礎英語課程,多數高校未做具體的教學要求;對英語專業少數民族學生多采用與漢族一樣的外語教育模式。當前,高校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學生對英語學習表現出強烈的愿望,并參加英語輔導班或自發組織學習英語;全國研究生統考以及國家正在實施的“少數民族高層次骨干人才計劃”研究生考試都要考外語,外語教育已成為制約新疆少數民族高層次人才培養的主要因素。少數民族語言傳承民族文化,維系民族心理;漢語是國內各民族間相互交往的族際語;英語作為國際流行語言具有獨特的社會功能。培養少數民族高素質人才不僅要求他們精通本民族語言、掌握漢語,還要加強外語教育。在此背景下,調查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新疆高校少數民族學生對外語教育的認同,對于發展新疆民族高等教育,制定正確的民族語言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2 研究方法
調研主要采用問卷法、訪談法,綜合運用語言學、教育學、民族學等多門學科理論,從多個角度調查高校少數民族學生對外語教育的認同。所選被調查對象為新疆少數民族較為聚集的塔里木大學、喀什師范學院250名少數民族學生,絕大多數為非英語專業的學生,英語專業30人、英語輔導班學生40人,實際收回有效問卷226份。
3 少數民族對英語的評價和認同

表1 高校少數民族學生對不同語言的評價(選取高頻選項)
人們對一種語言的評價是語言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調查了少數民族對本民族、漢語、英語三種不同語言的評價(多選題),這些評價包括對語言的情感傾向、學習感受和社會功能評價等方面的內容。從表1中高頻選項結果可看出,少數民族對本民族語多從情感、功能角度評價,87.61%以上學生認為本民族語好聽、易學、親切、有民族特征;對漢語多從功能角度評價,89.82%的學生認為漢語有用;對英語多從地位角度評價,88.94%以上的學生認為英語時髦、有身份。從語言心理學角度來看,人們從情感、功能、地位的角度對一種語言進行評價的結果,往往與其學習該種語言的目的相一致,同時會影響其對學習何種語言的選擇,也會影響其語言學習程度[1]。調查結果表明,英語作為目前世界強勢語言,對少數民族青年大學生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們對英語評價較高,感情上樂于接受,態度積極。

表2 高校少數民族學生對英語的認同
表2中,80.53%的少數民族學生在諸多外語中 首先選擇英語來學習,普遍認為英語在社會語言中的聲望高。由于新疆與俄語國家接壤,俄語學習有明顯的經濟價值,選擇俄語的學生占12.83%。而在新疆目前的生活、學習和工作環境下,85.4%的學生認為應先學好漢語。語言的社會功能是影響學習者選擇學習何種語言的重要因素,漢語作為國內各民族的“族際語”,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此題中,選擇“本民族語”的比例12.39%要高于選“外語”的比例2.21%,說明少數民族對英語與本民族語的差別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也反映了目前新疆語言社會的真實情況。
4 少數民族對英語學習的認同

表3 高校少數民族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認同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英語已成為世界上最強勢的語言。在以網絡化與多媒體為特征的信息時代,學習英語將會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最新的信息和最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從表3中可看出,77.88%的少數民族學生認為學習和掌握英語很有用,80.53%的學生迫切希望學校為少數民族學生適當開設英語課程,68.58%的學生希望自己成為會講本族語、漢語、英語的三語人。不難看出,目前新疆高校大部分少數民族學生對英語學習至少從“工具意義上”予以認同,普遍持積極樂觀的態度,有強烈的英語學習愿望,在潛意識中有一種崇尚和追求。少數民族大學生作為社會未來的精英和中堅力量,他們追求知識、渴望進步,對周圍的事物有著強烈的關注。隨著知識的更新、教育程度的提高,他們對英語學習的需求也逐漸增加,語言觀念也逐步趨向更大的開放。
5 少數民族對學習英語的行為傾向

表4 高校少數民族學生對學習英語的行為傾向
從表4中可以看出,42.92%的少數民族學生在上大學前“學過不少”或“學過一點”英語;上大學后,32.3%的學生一直堅持學習英語,45.58%的學生時斷時續或者偶爾學習過英語,22.12%的學生沒學過英語。總體上看,少數民族大學生學習英語的人數比沒學過英語的多。78.32%的學生學習英語最直接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升學求職。在對英語學習的期望值上,13.72%的學生希望通過學習能流利準確地使用英語,60.18%的學生希望能通過升學(研究生)英語考試,23.45%希望能用英語進行一般的交際。可見,少數民族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認識,情感的因素少一些,理性認知的因素多一些,即表現為一種實用即功利性認同。結果顯示,新疆高校少數民族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十分明確,在付諸實踐上表現出較為穩定的行為傾向,但與學習愿望存在一定的差距。
6 少數民族對英語文化的認同

表5 高校少數民族學生對英語文化的認同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人們在習得語言能力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內化其中所蘊含的文化因素。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語言學習就是文化學習[2]。從表5中,可看出61.06%的少數民族學生不希望本民族全體成員都成為會講本族語、漢語和英語的三語人,這與本文表2的調查結果看似矛盾,但實則不然。通過訪談了解到,作為當代大學生,他們希望自己成為會講本族語、漢語、英語的三語人,但不希望本民族全體成員都成為三語人,認為這樣會不利于本民族語言今后的發展和繁衍。少數民族對本民族語言文化有著天然的、深厚的感情,將本民族語言作為最主要的民族特征,看成民族文化認同的符號。而對英語文化認同問題上,表現出謹慎、冷靜的民族傳承意識,既保留自己的民族特點,又希望了解、接納異質文化。85.84%的學生迫切希望用英語來表達本民族文化,認為英語學習及運用并不意味著喪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學好英語可以跨文化交際,使本民族文化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為深入了解少數民族對英語文化的認同情況,筆者從宗教、禮儀、語言、飲食習慣及娛樂活動等5個角度[3]對英語學習者進行了訪談。調查得知:大部分少數民族英語學習者對英語文化認同度不高,認為英語學習無須內化本族人的文化標準[4],盡管一些學生認識到英語文化知識很重要,但是對考試并不實用;由于課堂上英語文化導入不夠,英語文化與本民族文化差異較大的情況下會給學習者帶來無準備的心理文化沖突,但是學習者已經具備雙語學習的經驗,他們大多數能夠正視這種語言文化的差異性。
7 少數民族對英語教育環境的認同

表6 高校少數民族對英語教育環境的認同
從表6中看出,61.43%的學生對當前所用英語教材滿意,38.57%的學生對所用教材不滿意。通過訪談了解到,當前少數民族學生英語教學均使用漢語編寫的全國統編教材,他們認為教材內容上缺乏民族文化元素,忽視了各民族的差異性。正如Byran指出“雖然外語教材不愿過于強調學生自身的文化,本族文化仍不應就此輕而易舉地被拋棄[5]。”64.29%的學生認為學校對民族學生英語教學最好用本族語、漢語和英語三種語言,說明少數民族學生能夠認識到師生的情感距離、語言距離、文化認同對外語學習產生影響[6],認為民、漢雙語基礎上的外語教學需要具備民、漢、外三種語言知識、學習經驗和三語能力的教師[7]。筆者了解到,大部分少數民族學生是以民、漢雙語作為參照語言來學習英語,他們在基本句型學習中經常把英語翻譯成漢語,通過漢語來學習英語,漢語在他們語言能力中占相當大的比重。當被問到老師是如何教英語時,英語學習者普遍反映“老師用漢語教英語”,具備三語能力的少數民族英語教師十分缺乏。調查結果顯示,少數民族對當前的英語教育環境認同度不高,當前普遍照搬“漢族化”的外語教育模式,給少數民族英語學習帶來諸多障礙,教學效果不能令人滿意。
8 新疆高校少數民族外語教育的思考
少數民族外語教育是用學生的民族語、漢語以及外語相結合組織教學的一種教育體制,其本質特征是少數民族雙語基礎上的外語教育[10],屬于三語教育范疇,具有民族性與文化多元性特點。新疆雙語類型的多樣性,決定了少數民族外語教育的復雜性。因此,發展新疆高校少數民族外語教育,需要同少數民族自身特點結合起來,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高校應正確認識和把握少數民族在外語教育認同上的種種矛盾狀態,充分考慮少數民族的實際需求和主觀愿望,因地制宜地開展少數民族外語教育,而不能采取強制的一刀切的辦法。
8.1 因勢利導,加強高校少數外語教育觀念的正面引導
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高校少數民族對外語教育認同上表現出種種矛盾的狀態。例如:少數民族學生在對英語學習上雖然表現出積極的學習愿望,但在付諸實踐上與愿望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對英語教育認同方面,雖然能夠認識到英語學習的重要性,但表現在行為傾向上,更多的受到功利因素的影響,并不是所有少數民族學生都積極主動地支持在高校實施英語教育。對于這些矛盾現象,高校必須正確地認識和把握,應當將少數民族在語言教育認同上的情感因素與價值觀因素區別對待。既要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感情,又要充分理解他們作出的選擇。同時,還應加強教育觀念的正面引導,積極宣傳英語教育的重要性、優越性,并以取得的實際成果來說服他們,絕不能采取強制性手段,否則只能適得其反[11]。
8.2 加大投入,努力改善高校少數民族外語教育環境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目前新疆高校對少數民族學生的英語教育還處于探索階段,沒有一個較為成熟的教育模式和完善的教學體系。針對少數民族積極學習英語的主觀愿望與教育環境缺失的矛盾,需要制訂出科學合理的外語教育體制。
一是加強師資建設。師資是教育系統的關鍵因素,決定著教學質量的優劣和教學的成敗。新疆高校英語教師缺乏,尤其是精通民、漢、英三種語言與文化的教師極為缺乏,進而制約少數民族英語教育進一步發展。因此,盡快培養和提高少數民族英語教育師資水平,顯得尤為迫切。
二是科學優化教材建設。教材是完成教學任務的基本保證。在少數民族英語教材的編寫上,既要考慮少數民族外語教育的民族性,又要考慮新疆社會語言文化的多元性。教材中,要增加民族文化元素,重視民族語、漢語、英語三語文化背景知識的導入,注重文化差異的比較。
三是加強少數民族外語教育的研究。少數民族外語教育屬于三語教育范疇,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地區的特色教育。在新疆高校多民族、多語言和多元文化區域,少數民族外語教育中所涉及的語言、社會、心理和文化等因素錯綜復雜。因此,應加強對少數民族學生外語作為第三語言學習的特點、三語習得規律的深入研究,并且把民族外語教育與正在實施的九年制義務教育體制相銜接,使民族地區英語教育走上科學發展的道路。
9 結論
教育的目的不僅是促進人的發展和民族的進步,更重要的是促進社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少數民族的外語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它涉及語言、教育、社會等多方面的內容。呂叔湘先生指出“學習語言不是學一套知識,而是學一種能力。”面對當前多元文化匯聚的世界格局,我們已經進入雙語和多語時代,多語人才是最具競爭力的人才之一。美國語言學家Lado指出“一個人所掌握的語言越多,越有利于其學習新的語言。”具備雙語知識和二語學習經驗的少數民族在英語學習上具有潛在的語言認識優勢和語言學能[12]。新時期新疆高校少數民族雙語、雙文化建構是天然的人力資源寶庫,為培養三語或多語能力者提供了不可多得語言基礎和經驗基礎[13]。因此,調查分析新疆高校少數民族對外語教育的認同,正確認識和把握少數民族外語教育在社會環境、語言文化背景、語言習得經驗等方面與漢語學生存在的差別,從而把研究引向深入,將英語教育的研究和少數民族自身特點以及語言學理論相結合,探索在多語言、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數民族外語教育規律,對于培養少數民族高層次人才具有重要意義。
[1] 王洋.新疆維吾爾族語言態度探析[D]:[碩士學位論文].新疆:新疆師范大學,2004.
[2] 楊玉.和諧語言生態:少數民族外語教育的文化使命研究[J].繼續教育研究.2012(10):142.
[3] Bhugra Dinesh,Bhui Kamaldeep,Mallett Rosemarie,et al.Cultural Iden tity and its Measurement:A Questio nnaire for Asians[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1999(11):244 -249.
[4] McKay S L.Teaching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J].ELT Journal,2003(2):145.
[5] Byran M.Cultur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89:143.
[6] Cenoz J,Hufeison B,Jessner U.Cross - 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M].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1:21 -24.
[7] [13]張貞愛,俞春喜.北方少數民族師生三語教育認同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2(1):16-22.
[8] Odlin T.Language Transfer:Cross- 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9] 曾麗.從“三語習得”視閾探討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外語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12(1):32
[10] 張貞愛.朝漢雙語人與英語教育[J].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1):152-155.
[11] 王洋.從語言態度的角度透視新疆少數民族雙語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07(2):60.
[12] 李珂.三語習得及其對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下英語教學的思考[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0(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