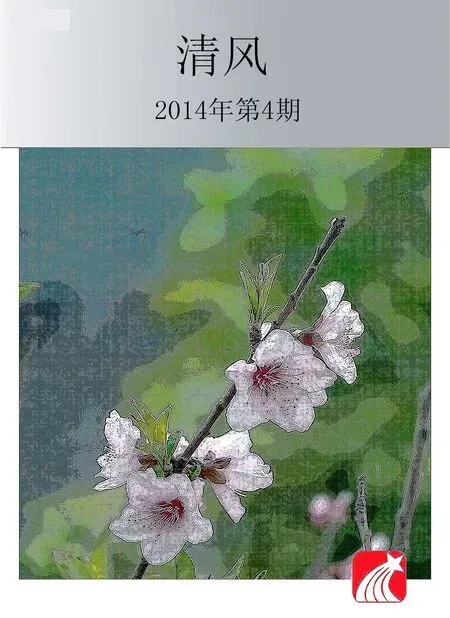當醫生就是要盡到責任
文_本刊記者 楊宇勃
當醫生就是要盡到責任
文_本刊記者 楊宇勃
時下,人們在提及醫患關系時,往往有說不完的抱怨,醫生與患者之間似乎有種不可調和的矛盾。誠然,在不少地方,醫患關系緊張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矛盾也日漸成了社會的“熱點”“焦點”。然而,社會上并不乏醫德醫術卓著的醫生,他們有的晝夜站在手術臺上,為患者醫治病痛;有的為了搶占最佳治療時機,穿梭在各個城市之間;也有的扎根在社會的最基層,為普通百姓帶來福音。
實際上,很多醫生認為,當醫生并不單單只是為了名利,更多的是一份責任。正如中南大學湘雅附二醫院主任醫師、醫學心理學教授姚樹橋所說:“像我們心理學這塊,不是個賺錢的行業,要想賺錢,就不做這個了,我們好多人在這都是盡一種責任……”
只想著治病,沒時間想其他的
對于醫生而言,時間就是生命,也許,別的行業任務重了還能擠出片刻的歇息,任務多了可以往后挪一挪,但醫生卻只能不停地去追時間、追生命,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將患者從病痛中解救出來,從死亡線上拉回來。
“一年下來,像我們(周末)都休息,像他90%以上的周末都不會休息,要到全國各地做手術。他是亞洲國際血管聯盟副主席,所以現在是國內國外都有手術、會議……只要他在長沙,科室的患者他都要查病房,堅持早查房、晚查房。”血管外科劉姓醫務人員在談到他們科室主任舒醫生(受訪者為人低調,不愿透露姓名)時,這樣對記者說。他連給自己輸液的時間也沒有,“每天都是專門挑一個空閑的時間,上午打一點,下午打一點……”
對舒醫生的采訪正是在他輸液的過程中。他告訴記者,現在醫生帶病上班的多得很,就在現在,科室里就有醫生帶病站在手術臺上做手術,“這你是看得少,你看得多就知道了”。舒主任說,“我沒有做什么,你不應該來采訪我,我們科室像我這樣的很多,像我們的醫生王暾、六坤、黎明、邱劍等。你可以你去采訪他們,真的。”
雖然舒醫生說沒做什么,但他的同事卻還記得,在2008年,一名患有艾滋病的假性動脈瘤患者大出血,生命垂危,急需手術治療。然而為艾滋病患者施行手術存在被感染的風險,于是有人建議讓患者轉院或保守治療。但舒醫生卻說,現在把這位患者推出醫院,等于把他推向死亡線,這個手術就由我來主刀吧。最終,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續。
當問到怎么看待醫德醫風問題時,舒醫生說:“在我當醫學生時,我們從來不提這個詞(醫德醫風),當醫生本身就應該有良心、有道德。我就想不明白,我們在做醫學生的時候,醫患關系很好,醫生認真給患者看病,患者也很相信醫生,哪像現在這樣……我沒時間想這些,我只想著怎么樣給患者看病,怎么把手術做好,否則就沒辦法專心把病治好了……”
在采訪舒主任的過程中,時不時有電話打入打出,電話這頭,舒說:“這樣吧,我下午把這邊忙完,就趕過來,過來后,我們連夜做手術,明天我再從廣州飛北京。”掛了電話后,他又馬上改訂當天飛廣州的機票。他對記者說:“廣州那邊有個患者情況惡化,晚上我得去做手術。古人講,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一個人活在這個世上,就應該為社會做點事情,就這么簡單,我也沒有其他的想法。”
退紅包也是個技術活
湘雅附二醫院血管外科的醫生黎明說,在他看來,醫生主要是處理技術問題,怎么給患者治病、怎么減輕患者的痛苦才是醫生應該思考的。
在國外,有專門的人員負責處理醫患關系,然而,我國并沒有這樣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說,一位醫生從患者住院到出院需要處理好多事情,比如費用的問題、醫保的問題,甚至交流的問題。
正如黎明告訴記者的那樣,有的患者的病情是需要做手術的,可是患者本人卻不想做;而有些沒必要做手術的患者卻會要求做手術。這個時候,醫生往往需要在短時間內,把自己所學的東西調動起來,給患者家屬解釋,讓他們理解。但是,“我們醫生每天接觸的患者太多了,可能有些患者會認為自己花了那么多錢,醫生說了兩句話就‘打發了’太不該。可是患者太多了,醫生根本就忙不過來,如果給一個人說多了,可能后面的人就說少了。”
作為醫生而言,他們的確很無奈。“現如今,社會上的輿論很多是要醫生來解決這個矛盾,但是,醫生的精力是有限的。”黎醫生告訴記者。在他們科室,要求醫生首先要站在患者的角度分析病情,同時也要站在患者的經濟情況角度考慮問題。“站在患者的角度說,一個是費用的問題,一個是后果的問題,有時候手術風險高,所以要考慮患者能不能接受這樣的花費以及承擔相應的手術風險。”
醫生在處理醫患關系時,最重要的是要在職業道德與個人利益方面做出合理恰當的取舍,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醫生行業必須恪守自己的醫德。正如黎醫生所說:“關鍵是操守,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操守,具體到每個醫生就是如何處理‘紅包’,我們整個科室的紅包都是護士長退。”據該科室護士長劉某說,血管外科每個月退五六例。
“患者送紅包有時候求得一個心理安慰,他們認為送了紅包后,醫生做手術時會細致點……按照患者家屬的這個心理,我們一般手術完了會退給家屬,你要是之前退的話,患者家屬心理上會有顧慮。”護士長劉某告訴記者。
看似簡單的退紅包也是一個技術活,黎明醫生坦言:“退得早了,患者會認為對他不照顧……有的時候,做完手術退也是有風險的,比如手術難度比較大,手術效果不太好,你去退紅包,患者會認為你手術做差了,所以說醫生現在背負的額外負擔很多,但是沒辦法……現在這個行業追求的是理解。”
選擇了就堅持做好
在采訪湘雅附二醫院兒童醫學中心新生兒科副主任薄濤時,記者體會最為深刻的是醫務人員對于生命的敬畏之感。
“每個月要有七八天必須通宵看護新生兒”,這是薄濤對于忙碌生活最簡短的總結,至于休息對于他而言似乎始終是“奢侈”。新生兒科的“患者”,是出生二十八天以內的新生兒,這些新生兒在新生兒科都是無家屬陪護的,一切生活都依靠醫生和護士的全天候服務。“我們的工作是個‘良心活’,(嬰兒的)父母沒在跟前,我們只能是既當爹又當媽,在這里也沒有人監督你,全得憑良心、操守做這個事。”
薄濤告訴記者,他經常給自己的研究生上上“思想政治課”,選擇新生兒科不要想著賺大錢,新生兒科在所有的醫學學科中是掙得比較少的。“選擇新生兒科意味著勞累,在我們這完全都是靠醫護人員看著,是非常累的。你必須有非常大的愛心,必須喜愛這個工作,如果你不愛它,那就不要去做了。”
一位醫生告訴記者,他們有時候會遇到一些棄嬰事件。有些孩子因為心臟病等問題,被父母遺棄,還有的家屬因為怕試管嬰兒將來發育不好,或者有什么病癥,所以拒絕撫養。然而他還是想盡辦法幫助孩子尋找父母,并耐心給他們做思想工作。“我們整個科室都是這樣,并不是我一個人這樣,當然,我們同時也會積極地聯絡公安機關幫助尋找家屬,這些都是應該的。”
2011年5月,新生兒科收治了一名被家長遺棄的早產女嬰,滯留醫院長達2個多月。由于孩子生下來就沒有得到父母的愛,薄醫生給予了這個孩子比其他患兒更多的關愛,每天抱著她,給她喂奶、喂藥,抱著去做檢查,墊付奶費,并通過各種渠道為她尋找父母。
談起工作壓力,薄濤坦言:“在新生兒科,有新生兒的壓力,更有家屬的壓力,新生兒病情的變化很快,所以你需要愛心、細心、責任心,必須要認真地對待每一個孩子。對于一個剛出生的小孩而言,他們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不管有沒有錢,小孩沒有錯……終究是個生命,所以作為一個新生兒科醫生,愛心是最重要的。”在薄主任看來,醫德醫風主要是你喜愛這個工作,喜愛這些孩子,這樣,醫風醫德就自然高了。
做醫生是一個良心活,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患者受益,醫生也同樣能夠體會到其中的快樂。“我們新生兒科室和其他科室不同,它是一個‘朝陽’科室,每天,新生兒一點點長大,給予他們媽媽的照顧,你天天都可以看到一種希望,給人一種積極的、向上的感覺,挺好的。”薄濤說。
在新生兒科,記者發現這里有很多護理人員,因為科室的特殊性,這里的護理人員需要照顧新生兒的吃喝拉撒,工作十分繁重,一位護理人員告訴記者:“沒有別的,只要細心、耐心、用心就好。”也正是因為這“三心”,新生兒科護士長吳麗元與她的護理團隊曾經獲得過中南大學頒發的“優秀護理單元”稱號。
醫生的工作很忙也很瑣碎,然而,面對這樣的工作,他們并沒有退縮。在采訪中,“操守”二字是醫生們一直強調的,他們告訴記者,這是醫生應該做的,“既然選擇了,就得為之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