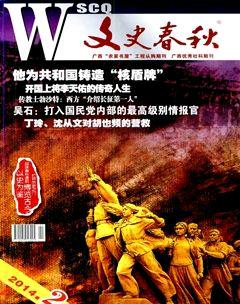傳教士勃沙特:西方“介紹長(zhǎng)征第一人”
顏梅生
勃沙特,是被紅軍當(dāng)作“西方間諜”扣留并押上長(zhǎng)征路的外國(guó)傳教士。1936年底,他所著的自傳體回憶錄《神靈之手》在倫敦出版發(fā)行,比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早了整整一年。對(duì)于被紅軍扣留并押上長(zhǎng)征路,勃沙特不但沒(méi)有怨恨,反倒飽含熱情地以自己的親歷贊揚(yáng)紅軍,甚至還大膽呼吁年輕的基督徒要學(xué)習(xí)紅軍精神,以紅軍那種簡(jiǎn)練有效的辦法,重視窮困的民眾,并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yùn)。勃沙特因而成為西方“介紹長(zhǎng)征第一人”。
不期而遇,傳教士遭意外扣押
貴州黃平縣城——舊州,有一所天主教堂,居住著加拿大籍英國(guó)基督教中華內(nèi)地會(huì)舊州教會(huì)牧師阿諾利斯·海曼夫婦和他們的孩子。
1934年9月30日,瑞士籍英國(guó)傳教士阿米弗雷德·勃沙特夫婦經(jīng)安順趕往舊州,“只想盡快趕到海曼那里過(guò)禮拜日”。勃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復(fù)禮,時(shí)年37歲,早在1922年秋,便受英國(guó)基督教會(huì)派遣來(lái)到貴州,從事傳教布道,并在鎮(zhèn)遠(yuǎn)福音堂擔(dān)任牧師。最終,他們?nèi)缭敢詢(xún)數(shù)嘏c海曼一起“度過(guò)了一個(gè)快樂(lè)而寧?kù)o的禮拜日”。
次日,勃沙特夫婦、海曼夫婦及其兩個(gè)年幼的孩子、新西蘭籍英國(guó)基督教中華內(nèi)地會(huì)思南教區(qū)傳教士埃米·布勞斯小姐,加上6名中國(guó)女仆、廚師、挑夫,離開(kāi)舊州前往鎮(zhèn)遠(yuǎn)。但誰(shuí)都沒(méi)有料到,上帝居然將他們轉(zhuǎn)送到紅軍長(zhǎng)征的隊(duì)伍。
當(dāng)時(shí),紅六軍團(tuán)經(jīng)過(guò)55天的艱苦征戰(zhàn),已進(jìn)入黃平境內(nèi),并在一個(gè)小山村與勃沙特等不期而遇。
那時(shí),貴州的大多數(shù)教會(huì)都支持反動(dòng)政府和土豪劣紳,以宗教迷信欺騙麻痹教友,進(jìn)行反動(dòng)宣傳,指責(zé)紅軍是“洪水猛獸”、“土匪流寇”。紅軍每到一處,教會(huì)都號(hào)召教友“堅(jiān)壁清野”,與反動(dòng)政府一起撤退,與紅軍為敵。因此,紅軍抓到教會(huì)骨干成員,都要甄別審訊,沒(méi)問(wèn)題的當(dāng)場(chǎng)釋放,有問(wèn)題的都以帝國(guó)主義間諜罪處以徒刑和罰款。
勃沙特等自然也被紅軍扣押,并于10月2日押解回舊州。紅六軍團(tuán)之所以這樣做,不僅以為這些身份不明的外國(guó)人是“西方間諜”,更主要的是從突圍西征以來(lái),傷病員日益增多,藥品和物資卻越加奇缺,認(rèn)為傳教士有條件、有辦法幫助搞到藥品和經(jīng)費(fèi),所以決定讓他們交納一定數(shù)量的贖金或與之相等價(jià)值的物品。
勃沙特等被交給紅六軍團(tuán)政治保衛(wèi)局看押和審理。鑒于他們的特殊身份,由紅六軍團(tuán)保衛(wèi)局局長(zhǎng)吳德峰、保衛(wèi)局黨總支書(shū)記戚元德(吳德峰之妻)具體負(fù)責(zé)。勃沙特并不知道他們的性質(zhì)、名字、職責(zé)、身份,故把吳德峰稱(chēng)為“法官”或“吳法官”,將戚元德稱(chēng)為“法官的妻子”,其在自傳體回憶錄《神靈之手》中寫(xiě)道:“帶去見(jiàn)法官時(shí),法官的妻子始終坐在床上注視著我們。最初,我認(rèn)為那個(gè)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實(shí)證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過(guò)很好的教育。當(dāng)我告訴他們,我妻子不可能堅(jiān)持跟他們走這么多路時(shí),法官的妻子寬慰我:‘我也是一個(gè)女人,她將會(huì)像我一樣慢慢適應(yīng)的。”
經(jīng)審訊,紅軍出于人道主義考慮,釋放了兩名已婚婦女、兩個(gè)小孩、女仆、廚師、挑夫,只扣留了勃沙特、海曼、埃米3人,規(guī)定在交納70萬(wàn)元贖金后,方可獲得人身自由,此前必須跟著紅軍走。
因?yàn)槔圪槪C妆粺o(wú)條件釋放
戚元德的任務(wù),主要是負(fù)責(zé)監(jiān)管埃米。埃米因?yàn)樘中袆?dòng)遲緩,只走了兩天,腳上就打起很多水泡,鞋子也被磨爛。戚元德不僅把棉布被單撕成長(zhǎng)條,打成比較柔軟的布條“草鞋”讓埃米穿上堅(jiān)持行走,還在埃米走不動(dòng)或不肯走時(shí),想辦法將馬背上的物資分散給戰(zhàn)士背上,讓埃米騎馬,甚至用一把竹椅穿上兩根竹棍當(dāng)做滑竿,讓?xiě)?zhàn)士們抬著她走。
一次,行軍至一條非常難走的羊腸小道,面對(duì)左邊是懸崖斷壁,右邊是萬(wàn)丈深溝,埃米嚇得雙腿發(fā)軟,又哭又鬧,兩個(gè)戰(zhàn)士一前一后幫著、扶著,她都不肯挪動(dòng)。早就將埃米視為“累贅貨”的戰(zhàn)士提議,干脆將她處置掉或扔下別管了。吳德峰堅(jiān)決不同意,強(qiáng)調(diào)她罪不至死,在這荒山野嶺,扔下她不是被餓死、凍死,也會(huì)被野獸吃掉。最后,大家用床單做了個(gè)大網(wǎng)兜,把埃米的手腳捆綁在一根木杠上,用毛巾將她的眼睛蒙住,由兩個(gè)戰(zhàn)士連哄帶騙地抬過(guò)了危險(xiǎn)路段。
鑒于埃米在行軍中不斷制造麻煩,甚至在后來(lái)穿越一處隘口時(shí),差點(diǎn)讓隨身保護(hù)的戰(zhàn)士墜落深澗,一周后,當(dāng)紅軍來(lái)到一處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帶時(shí),盡管還沒(méi)有獲得贖金,還是決定無(wú)條件地將她釋放。臨走時(shí),埃米對(duì)紅軍的拼死保護(hù)及釋放感激涕零,走了很遠(yuǎn),還回過(guò)頭來(lái),向紅軍招手致謝。
對(duì)女紅軍的所作所為,勃沙特寫(xiě)下不少贊譽(yù)之詞:“就像前面提到的吳法官的妻子一樣,真是不為環(huán)境所動(dòng)的高尚女性。”“最講人道的是那些婦女”、“在這支隊(duì)伍中,我們也首次領(lǐng)教了那些有趣的女共產(chǎn)黨人的鋒芒!”
對(duì)于埃米,勃沙特充滿(mǎn)著同情,在《神靈之手》中寫(xiě)道:“他們經(jīng)過(guò)考慮,將埃米小姐放在隊(duì)伍后面,不過(guò)天黑前也要到達(dá)宿營(yíng)地。”“可憐的埃米小姐,她總是在后面追,往往好像后面剛趕到,前面又吹響了出發(fā)號(hào)。”聽(tīng)說(shuō)埃米被釋放, 勃沙特起初并不相信:“路越走越難,但我們一直走到天亮。這時(shí),埃米小姐的衛(wèi)兵從后面追上來(lái),用過(guò)去常用的處決某某時(shí)的那種口吻,平淡地告訴我,埃米小姐已經(jīng)被釋放。我疑竇叢生,懷疑和擔(dān)心埃米小姐的命運(yùn)。”直到收到埃米的來(lái)信,勃沙特才“心中感到十分寬慰”、“對(duì)埃米小姐生存與否的久久掛念才冰釋于懷”。
送一半贖金,只先期放了海曼
紅六軍團(tuán)與紅二軍團(tuán)會(huì)師后,為擺脫敵軍的堵截,進(jìn)行了連續(xù)多日的急行軍。但紅軍并沒(méi)有虧待勃沙特和海曼,正如勃沙特的回憶所言:“因?yàn)闅夂虺睗瘢甓啵覀兲岢鲆獕K雨布,結(jié)果給了一件床單。我們后來(lái)才知道,這在紅軍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應(yīng)了”、“紅軍很體貼人,凡遇到危險(xiǎn)路段,總會(huì)有人走出隊(duì)列幫我們一把”、“在外宿營(yíng),當(dāng)紅軍官兵們睡在潮濕冰冷的泥地上時(shí),我和海曼卻得到了難得的鋪草和門(mén)板”、“吳法官很可能注意到我們衰弱的情況,晚上,他命令衛(wèi)兵給我們買(mǎi)只雞補(bǔ)養(yǎng)一下。衛(wèi)兵從那對(duì)老夫婦房東家里買(mǎi)了只雞。”“這段行軍太累了!法官的妻子可能感覺(jué)出了這個(gè)原因,她答應(yīng)將為海曼和我找匹馬。3天后,大概是到了湖北境內(nèi),給了我們一頭騾子,我和海曼每人各騎它三分之一的路。不久,又將一頭騾子給了海曼。”
但勃沙特、海曼卻并非“善茬”,時(shí)不時(shí)會(huì)給紅軍制造麻煩。如面對(duì)紅軍要求其給組織、上司和所在教會(huì)頭目寫(xiě)信,索要罰金或紅軍所需的等價(jià)急需物品時(shí),勃沙特、海曼并不老實(shí),欺負(fù)紅軍不懂洋文,借機(jī)夾帶情報(bào)、信息,以至于每次送信出去后,敵人的飛機(jī)就來(lái)騷擾、轟炸紅軍駐地。勃沙特還多次耍小聰明,在文字上與紅軍較量。紅軍要求勃沙特在信中“承認(rèn)自己是間諜”,而他卻在“間諜”一詞前面加了個(gè)“as”,即“當(dāng)作”間諜。1934年12月17日,因圣誕節(jié)即將來(lái)臨,渴望自由的勃沙特“單憑想與家人團(tuán)聚這一點(diǎn),就足以刺激我們?nèi)プ鎏优艿膰L試”。于是他唆使海曼一起逃了出去,可又被紅軍抓了回來(lái)。
同月底,紅軍分別以3項(xiàng)間諜罪判處海曼有期徒刑12個(gè)月、勃沙特18個(gè)月。因長(zhǎng)時(shí)間無(wú)法獲取贖金,紅軍表示“愿將贖金折換成一張所需的彈藥、電臺(tái)、電池及藥品的貨單”,如“能得到兩挺高射機(jī)槍的話(huà)”,甚至可以減少贖金。
對(duì)于紅軍提出的罰金等條件,教會(huì)出于政治等種種原因,總是作出不友好的回答和不符合實(shí)際的宣傳報(bào)道,且一拖再拖,在數(shù)目上也是討價(jià)還價(jià),原定的70萬(wàn)元贖金減到1萬(wàn)元,紅軍最后甚至還允諾不能少于6000元。但教會(huì)聲稱(chēng)可以提供6000元作為伙食費(fèi),而不是什么贖金。紅軍同樣出于政治等目的,非要教會(huì)低頭認(rèn)罪、賠禮道歉、交納罰金或等價(jià)物品,哪怕是少量罰金或物品,只要說(shuō)明問(wèn)題性質(zhì),就立即放人,否則就必須刑滿(mǎn)到期才可以釋放。
直到1935年11月18日,負(fù)責(zé)營(yíng)救的英國(guó)基督教中華內(nèi)地會(huì)牧師貝克爾才派代表從永順縣城送來(lái)藥品、物資和錢(qián),因?yàn)椤柏惪藸栔凰蛠?lái)了一半的錢(qián)”,紅軍只先期放了海曼。次日,押著勃沙特由桑植縣繼續(xù)長(zhǎng)征。
刑期已滿(mǎn),勃沙特獲得自由
當(dāng)然,勃沙特也為紅軍提供過(guò)一些幫助。
當(dāng)時(shí)紅軍極為缺乏地圖,用的是中學(xué)生課本上的地圖,圖上只有省會(huì)、縣城、大市鎮(zhèn)和大河流、大山脈,無(wú)法準(zhǔn)確標(biāo)定行軍打仗的路線(xiàn)。攻克舊州后,紅軍找到一張近1平方米大的貴州地圖,但上面所標(biāo)地名不是中文。聽(tīng)說(shuō)勃沙特能講英語(yǔ),紅六軍團(tuán)軍團(tuán)長(zhǎng)肖克派人把他請(qǐng)來(lái)。勃沙特認(rèn)出是張法文地圖,而他專(zhuān)門(mén)學(xué)過(guò)法語(yǔ)。于是勃沙特講,肖克記,把地圖上重要的山脈、村鎮(zhèn)、河流等譯成中文標(biāo)記。肖克后來(lái)回憶說(shuō):“當(dāng)時(shí),我們?cè)谫F州轉(zhuǎn)戰(zhàn),用的是中學(xué)課本上的地圖,沒(méi)有戰(zhàn)術(shù)上的價(jià)值。當(dāng)我們得到一張大地圖后,勃沙特幫助譯成了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幫助的時(shí)候,解決了我們一個(gè)大難題。同時(shí),他在邊譯邊聊中,還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情況,對(duì)我們決定部隊(duì)行動(dòng)起了一定作用。他幫助我們翻譯的地圖成為了我們?cè)谫F州行軍作戰(zhàn)的好向?qū)А!?/p>
1936年4月11日,紅二、六軍團(tuán)逼近昆明,準(zhǔn)備強(qiáng)渡金沙江北上,鑒于勃沙特刑期已滿(mǎn),肖克告訴勃沙特:“你是一個(gè)瑞士公民。我們知道,瑞士不是帝國(guó)主義國(guó)家,沒(méi)有同中國(guó)簽訂不平等條約,也沒(méi)有在中國(guó)設(shè)租界,所以我們決定放你走,明天就給你自由。”
次日,肖克擺了一桌酒席為勃沙特餞行,還專(zhuān)門(mén)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作陪的有貴州地方知名人士周素園、原國(guó)民黨第四十一師師長(zhǎng)張振漢,還有在石阡被捕的天主教堂神甫漢斯·凱勒等。勃沙特就此回憶:“當(dāng)一切準(zhǔn)備就緒時(shí),好消息就在飯桌上和吃飯的同時(shí)宣布了……吳法官的妻子、肖克將軍和我們坐在一起。”“吳的妻子還弄了一大罐很甜的咖啡拿到桌上。”吳德峰還向勃沙特交代了有關(guān)事項(xiàng),并問(wèn)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費(fèi),勃沙特以?xún)商炻烦逃?jì)算,提出要4塊銀元,“吳法官叫來(lái)分管財(cái)務(wù)的同志,告訴他:給這個(gè)外國(guó)人10塊銀元!”臨別之際,肖克希望勃沙特作為中國(guó)人民的朋友,繼續(xù)留在中國(guó),“可以辦一所學(xué)校什么的,只要不強(qiáng)迫學(xué)生信仰上帝就可以”。
就這樣,勃沙特結(jié)束了這段長(zhǎng)達(dá)18個(gè)月的經(jīng)歷。期間,勃沙特隨紅軍轉(zhuǎn)戰(zhàn)貴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省,行程萬(wàn)里,成為紅軍長(zhǎng)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參加者。
在與紅軍的朝夕相處中,勃沙特逐漸認(rèn)識(shí)了紅軍。紅軍生活條件惡劣,但卻盡量照顧他的習(xí)慣和習(xí)俗,盡可能滿(mǎn)足他的要求,令他非常感動(dòng)。尤其是紅軍隊(duì)伍紀(jì)律嚴(yán)明、愛(ài)護(hù)群眾,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zhàn)斗,不賭博、不抽鴉片,充滿(mǎn)著追求精神、決心建立共產(chǎn)主義政權(quán),給他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由紅軍的一個(gè)敵視者變?yōu)橐粋€(gè)堅(jiān)強(qiáng)的同情者和忠實(shí)朋友。他對(duì)被紅軍拘押的經(jīng)歷一點(diǎn)也不感到反感,相反,隨著對(duì)紅軍的認(rèn)識(shí)不斷加深,勃沙特感悟到了紅軍先扣押他,之后又釋放他的真正原因——“紅軍很可能要借此告訴人們,扣押外國(guó)人的目的并非財(cái)物,金錢(qián)對(duì)紅軍并非大事,重要的是紅軍要借此告誡外國(guó)人,他們反對(duì)在中國(guó)傳教。”
于是乎,勃沙特離開(kāi)紅軍去了昆明后,沒(méi)有把時(shí)間和精力花費(fèi)在游玩上,而是迫不及待地著手整理自己在紅軍中的那段親身經(jīng)歷,他要把這些告訴人們、告訴世界。在他人的協(xié)助下,勃沙特寫(xiě)出了一部傳奇紀(jì)實(shí)作品《神靈之手——一個(gè)為基督事業(yè)在中國(guó)被俘者的自述》(又名《神靈之手》、《紅軍長(zhǎng)征秘聞錄》)。1936年11月,當(dāng)紅二、六軍團(tuán)還在長(zhǎng)征途中時(shí),該書(shū)便由倫敦哈德?tīng)枴雇蓄D公司出版發(fā)行,從而成為西方最早介紹紅軍長(zhǎng)征的專(zhuān)著。12月,該書(shū)在英國(guó)脫銷(xiāo),接著又發(fā)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該書(shū)被譯成法文,由瑞士艾莫爾出版社出版。
1978年,勃沙特在出版商的一再邀約下,又重寫(xiě)了這段經(jīng)歷,并定名為《指導(dǎo)的手》。英文本面世以后,該書(shū)又被譯成法文,書(shū)名為《導(dǎo)手》,由瑞士教會(huì)出版社出版。
1984年,美國(guó)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為寫(xiě)《長(zhǎng)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shū),專(zhuān)門(mén)前來(lái)中國(guó)采訪(fǎng)和搜集史料。在采訪(fǎng)肖克時(shí),肖克向索爾茲伯里介紹了勃沙特幫助紅軍長(zhǎng)征的往事,并拜托索爾茲伯里幫助尋找勃沙特。
功夫不負(fù)有心人。索爾茲伯里在英國(guó)找到了勃沙特。1986年5月27日,肖克委托中國(guó)駐英大使冀朝鑄前去拜訪(fǎng)勃沙特,并轉(zhuǎn)交了他的一封信件:“久違了!從索爾茲伯里先生處知道了你的近況。雖然我們已分別半個(gè)世紀(jì),但50年前你幫助我翻譯地圖事久難忘懷。所以,當(dāng)索爾茲伯里先生問(wèn)及此事時(shí),我欣然命筆告之。1984年我在出國(guó)訪(fǎng)問(wèn)途中,曾打聽(tīng)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們都早過(guò)古稀,彼此恐難再見(jiàn)。謹(jǐn)祝健康長(zhǎng)壽。”
直到現(xiàn)在,有關(guān)部門(mén)都還沒(méi)有從外國(guó)人,尤其是親歷長(zhǎng)征的外國(guó)人那里搜集到紅軍長(zhǎng)征的史料。有專(zhuān)家們認(rèn)為,《神靈之手》的史料價(jià)值已超過(guò)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的《長(zhǎng)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它是目前專(zhuān)家學(xué)者研究中共黨史,尤其是研究紅軍長(zhǎng)征史的來(lái)自國(guó)外的惟一原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