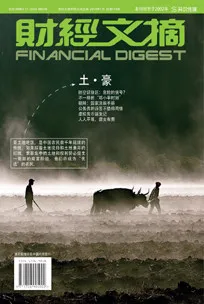“冷漠”的藝術(shù)
袁家珣


“藝術(shù)無(wú)論是過(guò)去還是現(xiàn)在,常常是一件不美的東西。”
如果用一般花紅柳綠的審美趣味來(lái)看,當(dāng)代藝術(shù)大抵和英國(guó)學(xué)家H.里德所說(shuō)的差不多。
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美術(shù)館,耿建翌的《燈光下的兩個(gè)人》,黑色的背景,一對(duì)男女正襟坐在桌前。灰衣女子表情黯淡,漠然,光影交錯(cuò)下五官模糊,活似面具,唯一清晰的是凝望著觀者的一雙眼,泛著冷光;一旁低頭看報(bào)的男人更像是冷峻的靜物,黑框眼鏡下,什么也沒(méi)有。
這是1985年,“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相繼畢業(yè)于浙江美術(shù)學(xué)院(現(xiàn)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的學(xué)生的畢業(yè)作品。“85新潮”不是偶然,學(xué)院里,西方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表現(xiàn)主義四處彌漫,藝術(shù),不用服從于“美”或者是“政治正確”的思想,但必須揭露現(xiàn)實(shí);學(xué)院外,“沒(méi)我”的時(shí)代剛走不久,都市化進(jìn)程日益加速,那些藝術(shù)家開(kāi)始了“我”的表達(dá),向公眾展示浮光掠影下的種種異端。
冷漠與荒誕
那屆浙美油畫(huà)系的畢業(yè)作品大都如此“冷漠”,比如魏光慶的《工業(yè)風(fēng)景》,畫(huà)上出現(xiàn)類(lèi)似于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的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所,兩根鋼管筆直地從畫(huà)中地平線向地面伸出,將棋子般靜靜立著的兩個(gè)人隔開(kāi)。
“那些冰冷而不安的機(jī)械、廢鐵是一種真實(shí)......使我無(wú)法再接受那些在場(chǎng)面上大而空,內(nèi)容上虛假‘積極向上,唯主旋律的作品。”藝術(shù)家回憶道。
當(dāng)全國(guó)布滿了“干柴”,這種挑釁的火藥就有了燎原之勢(shì)。各地的藝術(shù)青年自發(fā)形成藝術(shù)群體,他們大都來(lái)自學(xué)院。丁方、楊志麟、徐累等藝術(shù)家組成了“紅色·旅”藝術(shù)團(tuán)體,群體宣言稱:“地球上的人們被孤獨(dú)所籠罩,沉積于我們靈魂的最深處而凝聚為一種悲劇意識(shí)。”
四年后,藝術(shù)家肖魯朝著自己的作品開(kāi)了兩槍。那是在1989年中國(guó)美術(shù)館的“前衛(wèi)藝術(shù)展”,肖魯?shù)热嗽诖笮脱b置作品《對(duì)話》里設(shè)立了兩個(gè)電話亭,中間被一個(gè)臺(tái)子隔開(kāi),一個(gè)聽(tīng)筒從鏡子前懸掛下來(lái),在電話亭的一男一女顯然不是在相互通話。然而她認(rèn)為作品“缺少破壞的能量”,在開(kāi)幕那天,給了藝術(shù)界內(nèi)外一個(gè)當(dāng)頭棒喝。
藝術(shù)媒介逐漸多元,并且更加驚世駭俗,各種規(guī)則也都在新的藝術(shù)觀念面前受到挑戰(zhàn)和質(zhì)疑。藝術(shù)家不再歌頌具有忍耐精神、有著英雄本色的西藏牧民、農(nóng)民,而是用夸張的事物來(lái)象征“一切現(xiàn)代的荒誕”。
應(yīng)該如何看待這種美感?有藝評(píng)人解讀:“中國(guó)人在努力前行的過(guò)程中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這一時(shí)代現(xiàn)實(shí)不可能以一種小清新美學(xué)來(lái)承載。”
85運(yùn)動(dòng)雖然隨著這兩槍戛然而止,但是事實(shí)上,85只是一個(gè)切面,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脈絡(luò)在之后近三十年出現(xiàn)過(guò)不同名稱,而變形的、反叛的、冷漠的藝術(shù),為持續(xù)異化的社會(huì)現(xiàn)象下注解。
“新生代”之困
裸女、玻璃缸、鳥(niǎo)籠、垃圾袋、避孕套......那些難以直視的景象不斷地在藝術(shù)展廳出現(xiàn),然而縱觀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不長(zhǎng)的藝術(shù)史可以看出,當(dāng)各種符號(hào)被不斷地copy,便失去它們的意義,或是成為一種噱頭。這不禁使人發(fā)問(wèn):“中國(guó)制造”的藝術(shù)價(jià)值何在?
隨著改革開(kāi)放三十年,當(dāng)代藝術(shù)也跌跌撞撞地成長(zhǎng)了三十年,從傷痕藝術(shù)到政治波普,到“新生代”寫(xiě)實(shí)、卡通一族等不同藝術(shù)陣營(yíng)相繼出現(xiàn),卻往往是毀譽(yù)參半。除了來(lái)自極左思潮的沖突,尖銳的評(píng)論紛紛對(duì)當(dāng)下藝術(shù)的批判性表示懷疑。
“文革”時(shí)期的震顫造就了一批攝人心魂的傷痕藝術(shù),在這之后,新一代創(chuàng)作者沒(méi)有“文革傷痕”的切身感受, 寫(xiě)實(shí)走到80年代末之后也悄然退出主流。
也是在這時(shí)候,受到西方的解構(gòu)主義的影響,藝術(shù)與非藝術(shù)的界限模糊了,但是畫(huà)貓成虎卻一直是中國(guó)藝術(shù)的一大病痛。在觀念藝術(shù)的基礎(chǔ)上,“看不懂”沒(méi)關(guān)系,所以似乎什么都可以拿來(lái)當(dāng)藝術(shù)。一個(gè)藝評(píng)人曾開(kāi)玩笑地點(diǎn)了一根香煙,稱之為“行為藝術(shù)”,他解釋道:“薩特曾說(shuō),香煙是虛無(wú),煙斗是存在,我選擇香煙,表示著我對(duì)于現(xiàn)代精神的虛無(wú)與虛偽的藐視。”
藝術(shù)評(píng)論家朱其認(rèn)為,美院缺乏文史哲的思想訓(xùn)練,學(xué)生“不看書(shū)”,使得當(dāng)下的藝術(shù)甚少有80年代的爆發(fā)力,歸根結(jié)底,是“對(duì)于現(xiàn)代史缺乏深刻的反省,對(duì)消費(fèi)主義的自我異化缺乏討論”。
是時(shí)候面對(duì)所謂的消費(fèi)主義了,用傅柯的話來(lái)說(shuō):“藝術(shù)不是為了創(chuàng)作者或是當(dāng)政治的附庸,而是屬于那些有錢(qián)有閑的老大哥。”當(dāng)拍賣(mài)場(chǎng)頻頻敲下上億人民幣的油畫(huà),金字塔底下千千萬(wàn)萬(wàn)的草根藝術(shù)家固然成為資本博弈的犧牲者。沒(méi)有烏托邦,只有灰色調(diào)的現(xiàn)實(shí),或許“冷漠”只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