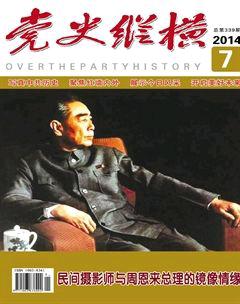蘇聯與西安事變
孫果達+王偉
在以往對西安事變的研究中,人們總以為蘇聯與西安事變并沒有直接的關系,但真實的歷史恰恰相反。
蔣介石西安之行由“和”到“剿”的轉變
從1935年底起,蔣介石主動派人在莫斯科試探國共談判的可能性。當時蔣介石以為,長征中的紅軍已經不足為患,“安內”基本完成,政策的重心開始傾向“攘外”。如果不乘勝抓住機會同中共和談,就不能指望從蘇聯方面得到“攘外”不可缺少的援助與支持。
對于這段歷史,陳立夫在其回憶錄《成敗之鑒》的“準備抗戰招撫共黨”一章里有比較明確的回憶:“早在抗戰以前,他(蔣介石)就要我做兩件工作:第一,要我和中共交涉,萬一中日戰爭爆發,中共應及時發表宣言,共同抗日。第二,要我和蘇俄交涉一旦中日戰爭掀起,中蘇兩國要站在同一戰線。”這一回憶表明,國共談判是蔣介石為爭取蘇聯支持以應對中日矛盾日益激化的戰略抉擇,“招撫”兩字雖然居高臨下,卻也突顯出當時蔣介石對紅軍的基本戰略已經以“和”為主。如果蔣介石始終堅持這項政策,西安事變顯然就無從談起。
193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接到中共談判代表張子華從西安發的電報:“國民黨方面的談判條件是:(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同國軍;(三)中共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四)即派人具體談判。”為了配合談判進程,毛澤東迅速于10月15日以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通過蘇維埃新聞社發表關于停戰抗日的談話,表示“一切紅軍部隊停止對國民革命軍之任何攻擊行動”。同一天,葉劍英從西安致電毛澤東:“蔣明日到此。”10月17日,毛澤東與張聞天、周恩來一起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并告彭德懷:“與南京談判有急轉直下之勢······蔣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們正交涉由蔣派飛機接恩來到西安與蔣直接交涉。”毛澤東廣為告知的電報顯然認為和談可能成功在即,因為已經到了雙方最高級別的會面,因此歡欣鼓舞之情也溢于言表。
但是,蔣介石突然推遲了原定10月16日到西安的行程。毛澤東在18日致朱德等將領的電報中開始略顯擔心:“正與國民黨談判,彼方當有不欲使談判弄僵之意。”可見當時的毛澤東還沒有意識到蔣介石已經變臉,但對胡宗南又開始加強進攻已經隱隱有所不安。于是毛澤東又專門致信胡宗南,表示雙方宜“棄嫌修好”,還“請專函繕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軍發送。”毛澤東顯然還以為胡宗南的行動只是其個人行為,因此寫信做其工作。20日,葉劍英急電毛澤東:“蔣介石令胡宗南急進”。“從10月20日開始,蔣介石調集十幾個師由南向北大舉進攻,企圖消滅紅軍于黃河以東甘肅、寧夏邊境地區。”
完成對紅軍進攻的新布置,蔣介石于10月22日到達西安逼迫張學良剿共。24日,毛澤東致電葉劍英:“蔣的確實企圖查明即告。”26日又同朱德等46人聯名發出《紅軍將領給蔣總司令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提出:“不論諸先生派代表進來,或要我們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線上談判,我們都愿接受。只要內戰一停,合作門徑一開,一切談判都將要在抗戰的最高原則之下求得解決。”毛澤東雖然感覺形勢發展不妙,卻依然心存希望,為和平談判做最后的努力。10月29日,葉劍英致電毛澤東:“蔣張會談結果亟惡。蔣表示匪不剿完,決不抗日。”蔣介石的西安之行完成了由“和”到“剿”的轉變,國共和談功虧一簣。
蘇聯對中共紅軍的出賣
以蔣介石10月16日突然推遲赴西安為界,和談就此變為進攻。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使得蔣介石的政策出現了180度的轉折?陳立夫在其回憶錄中說出了驚天秘密。據《西安事變前后的周恩來》一書披露:1936年10月,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文字已逐漸形成。陳立夫在《參加抗戰準備工作回憶》中這樣表述:在一次討論中,困乏的蘇聯駐華大使、蘇方談判代表鮑格莫洛夫對陳立夫說:“一旦中日爆發戰爭,我們決不會幫助中共。”陳立夫驚奇地瞪大眼睛,以為聽錯了。可鮑格莫洛夫還在喋喋不休地說道:“陳先生,中共只有兩三千兵力,如果他們不聽話,你們就把他們消滅算了。”鮑格莫洛夫漫不經心地收拾著文件,準備退場。陳立夫張著嘴,半天沒動窩。他不知道鮑格莫洛夫的此番話究竟是什么意思。事后,陳立夫趕緊跑到蔣介石那里去匯報,蔣介石也愣住了,連連追問“;談判中你們喝酒了沒有?”
“沒有。”陳立夫回答。
“這個鮑先生有無精神病史?”“翻譯有無錯誤,是否口譯錯了?”蔣介石一連串地追問。
陳立夫說:“我找兩個翻譯仔細核對過,沒有任何差錯,況且鮑格莫洛夫也懂不少漢語,他還是半個中國通呢。”
蔣介石還是不放心:“你能準確地說,他說的是真的嗎?”陳立夫肯定地說道:“我認為他說的是真的!在談判過程中,精力始終是充沛的,而且也是認真的。”陳立夫瞇起眼努力回憶道:“在談判時,我跟他說過,如果中國將來共產化,對你們蘇聯有什么好處?你們能制服一個比你們人口多三倍的中國嗎?他并沒表示反對,而且還同意讓我將此話可以告知蘇聯政府。”
蔣介石由此判斷,原來共產黨的談判是因為已經到了窮途末路,那還講什么條件,命令部隊加緊進攻,“剿匪”已到最后五分鐘階段。
該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應該是具有一定權威性和可靠性的。
陳立夫的這一回憶應該基本屬實,理由起碼有八:
一是形勢逼迫。1936年10月德、意的“柏林—羅馬軸心”已經形成,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即將正式簽訂,蘇聯不得不加速聯蔣步伐,在中蘇同盟談判的節骨眼上亮出了“必殺技”。
二是合乎邏輯。這里所說的合乎邏輯體現在六方面:背景邏輯,大國的博弈使得力量微不足道的紅軍即將被“邊緣化”;交易邏輯,放棄紅軍既清除中蘇同盟的主要障礙,又是蘇聯獲取對手信任與讓步最有力的籌碼;蘇聯軍援計劃的邏輯,鮑格莫洛夫必須促使蔣介石重燃戰火是其中關鍵一環;慫恿邏輯,鮑格莫洛夫有意縮小紅軍數量,顯然是為了誘使蔣介石早下決心;因果邏輯,蔣介石就此化“招撫”為“圍剿”;記憶邏輯,事關重大,陳立夫當然刻骨銘心。
三是有電報佐證。10月10日,中共和談代表張子華在西安致電毛澤東:“陳立夫赴寧數日可回”。可見當時也負責對蘇談判的陳立夫回寧正是為了與鮑格莫洛夫的會談。隨后蔣介石突然推遲原定10月16日到西安準備與周恩來談判的計劃,因此不難界定鮑格莫洛夫表態的時間當在10月中旬的前幾天里。
四是有行動佐證。《周恩來年譜》說,10月21日,中共中央以為蔣介石缺乏誠意,就決定先由潘漢年作為談判代表,并“通知正在西安的張子華,要他電告曾養甫、陳立夫。”可見原本“數日可回”的陳立夫根本就沒有回西安繼續談判。
五是合乎鮑格莫洛夫的身份。鮑格莫洛夫具有雙重身份:對國民政府是蘇聯駐華大使;對中共中央是斯大林的“全權代表”。由他出面轉告莫斯科對中共政策的改變確實最為直接、機密與權威。
六是合乎陳立夫的身份。陳立夫是當年這段歷史最主要的當事人,當時全權負責與中共及蘇聯的談判并向蔣介石匯報。鮑格莫洛夫通過陳立夫向蔣介石透露莫斯科的真實意圖完全順理成章。當時這類最頂尖的機密在中國極可能只有蔣介石與陳立夫兩人才有資格掌握,因此陳立夫晚年的回憶只能成為孤證也同樣順理成章。
七是欲蓋彌彰。陳立夫的這段回憶發表在1977年出版的《參加抗戰準備工作回憶》。但是,在1994年出版《成敗之鑒》時,陳立夫在“準備抗戰招撫共黨”一章里,卻刪減了關于鮑格莫洛夫的講話,以及蔣介石與陳立夫的對話內容。很顯然,1977年以后,隨著西安事變研究在大陸的不斷深入,并非歷史學家的陳立夫也已經意識到這段歷史秘密的披露就像一把雙刃劍,在指證蘇聯駐華大使卑劣的同時,恰恰證明破壞當時國共和談的正是蔣介石,尤其是證明了被逼出來的西安事變正是蔣介石的自取其辱和自食其果。因此,投鼠忌器的陳立夫不得不改動回憶錄中的重要內容。但是,兩本回憶錄相隔17年的白紙黑字,恰恰表明陳立夫不得已的刪改,正是對當年歷史事實的欲蓋彌彰。
八,蔣介石的突然變臉。要真正坐實陳立夫的所憶,還必須證明蔣介石確實及時采取了鮑格莫洛夫所希望的行動。令人難以置的是,前述歷史事實給出了肯定的回答,蔣介石確實在10月16日撕毀了和談協議。
正是蘇聯的慫恿,使得蔣介石突然以“剿”廢“和”,既幫了蘇聯,更幫了自己,又豈能聽從張學良不明就里的諫言。鮑格莫洛夫雖然得逞了,但絕不會料到就此點燃了西安事變的引線。此點正好說明,蘇聯為何一得知事變就忍不住暴跳如雷。直接聽命于斯大林的鮑格莫洛夫在西安事變后不久就死于蘇聯的“肅反”,很可能就是為此失誤,以及知道得太多太深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蘇聯出賣中共紅軍的原因
蘇聯出賣紅軍是謀求其國家安全。1936年夏是世界醞釀力量組合的重要時刻。德、日反共產國際同盟簽訂在即,中、德關系如日中天,日本加緊用文武兩手誘逼蔣介石。一旦德國調停中、日關系成功,蘇聯就立刻陷入腹背受敵的險境。因此,不惜代價拉攏蔣介石就成為蘇聯當時迫在眉睫的唯一選擇,其核心就是由反蔣轉向聯蔣。
蘇聯對蔣介石的需求,最直白的表述是在西安事變發生后。當時斯大林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轉告中共中央的電報中透露:“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楊虎城當時也認為:“……這次西安事變之不成,完全在于當時日本與蘇聯都在拉南京,蘇聯已經比日本領先了一步,因此它力主中國應在蔣的領導下實現和平統一,當然不會有援助西安之舉,這是事變事實上不能成功的關鍵。”確實,“唯一人物”、“力主”等表述,充分體現了斯大林的聯蔣決心。
既然蘇聯對國民政府的基本戰略是聯合,對蘇聯而言,紅軍原先的歷史使命顯然也就不復存在。換句話說,已經元氣大傷的紅軍在蘇聯的聯蔣戰略中不僅失去了價值,甚至已經成為累贅與隱患。但是,如果把紅軍作為禮物送給求之不得的蔣介石,既能最大限度地顯示蘇聯的“誠意”,促使蔣介石早日下定中蘇同盟的決心,又能乘機消除自身的包袱與威脅;不僅能化解德、日、中的合作,還能利用中國拖住與對抗日本。簡而言之,蘇聯只需犧牲紅軍就能輕易實現如此一舉多得的戰略需求。楊虎城就曾經擔心:“莫斯科己經為自身利益出賣了西安”,“它為爭取南京,是否會……將中共也送入蔣介石的懷抱呢?”楊虎城當年的擔心顯然不是信口開河空穴來風,抑或他日后還為此失言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也足以使張學良對相關秘密三緘其口噤若寒蟬。如此看來,西安事變本身其實并無多大秘密,真正的秘密是在西安事變背后大國不能曝光的交易。張學良卷入如此之深還能保住性命已經實屬萬幸,但終身被囚以確保其永遠閉嘴也就在所難免。
蘇聯對蔣介石的救援
蘇聯慫恿蔣介石發動軍事進攻的結果竟然使得蔣介石身陷囹圄,西安事變直接影響蘇聯聯蔣政策的成敗,也就直接威脅到蘇聯的國家安全戰略。基于這些原因,蘇聯決不可能置之度外袖手旁觀。因此,救援蔣介石就成為蘇聯刻不容緩的頭等大事。西安事變真正參加談判的是兩國四方這就掀動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過程中最為隱秘的一頁。
(一)對各方的訴求
蘇聯自身的訴求簡單明了:必須“救蔣”。但從目前的資料看,西安事變發生后的第一個星期里,蘇聯政府除了激烈地口誅筆伐似乎無所作為,難道斯大林竟然只想用“罵”來救蔣介石的命,來保衛受到嚴重威脅的自身大戰略?其實,只要確認事變最后結局完全滿足了蘇聯的訴求,就能對蘇聯采取的隱蔽而高超的策略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蘇聯對中共的訴求:支持“釋蔣”。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相關研究都認為在事變發生后,斯大林立刻要求毛澤東“釋蔣”。其實這是個誤解,理由很簡單,毛澤東手中根本無“蔣”可“釋”。因此,不能公開出面的斯大林是要求毛澤東“支持”釋蔣,也就是去勸張學良“釋蔣”,卻不料遭到堅決的拒絕。
蘇聯對張學良的訴求:立即“釋蔣”。斯大林應該很清楚,真正能夠實現蘇聯訴求的關鍵人物是張學良。因此,為了確保蔣介石的安全,斯大林必定會直接找張學良,理由起碼有四:毛澤東拒絕“釋蔣”,張學良就成了斯大林當時唯一的希望;只有直接與掌握蔣介石生死的張學良達成協議才是“救蔣”的根本之道;斯大林與張學良有直接的聯系通道,張學良的秘密代表莫德惠就在莫斯科;張學良有求于斯大林。
當時張學良已經勢成騎虎:莫斯科反對西安事變,使得張學良的“革命”難以為繼;毛澤東堅持“除蔣”,使得張學良的“兵諫”難以自圓其說;蔣介石居高臨下,使得張學良有口難開。因此,站在張學良的立場看,當時真正有迫切需要并有強大實力能夠幫助張學良走出困境和險地,確實也只有莫斯科了,而且唯有莫斯科的“釋蔣”與張學良的“兵諫”還有共同的政治基礎。更何況,張學良在事變前就一直在苦苦尋求蘇聯的支持。早在13日,美國就稱“消息靈通之觀察者相信,張學良或能接受談判。”這應該就是張學良最初向蘇聯發出直接談判的暗示。因此,張學良沒有理由不寄希望于斯大林。
既然斯大林與張學良互有迫切需求,他們之間的直接談判應該是勢在必然的。也就是說,斯大林在要求張學良立即“釋蔣”的同時,也必須滿足張學良“兵諫”的政治訴求,以及張學良與部下的人身安全。確實,如果張學良得不到類似的承諾,是決不會、也不敢放虎歸山的。就此而言,西安事變中張學良真正的談判對手應該是斯大林。目前雖然沒有看到相關的文字記載,但歷史當事人的實際行動就是最過硬的證據:為了避免夜長夢多,張學良迅速而果斷地采取了一系列貌似瘋狂的舉動:如親自陪同蔣介石赴南京以保證其安全、嚴禁部下有任何反抗、無條件釋放眾多被扣的南京高官與飛機等等,非常干脆而徹底地放棄了手中按照常理原可以充分利用的談判籌碼。這些當時使人目瞪口呆,至今看來依然匪夷所思的舉措,無非是張學良在履行秘密談判中的承諾或付出的代價,只是外人不知內情,張學良更不能明說而已。令人遺憾的是,張學良由于過于匆忙,或許在談判中只注重獲取人身安全而忽視了人身自由的保證,才讓蔣介石不光彩地鉆了空子。
蘇聯對南京的訴求:配合“救蔣”。因為要兌現對張學良的承諾,就必須要南京配合。其實從西安事變發生起,莫斯科就與南京開始了緊張而密切的秘密接觸。《中國新民主主義通史》說:“蘇聯為澄清南京的誤會,南京為爭取蘇聯幫助釋蔣,雙方在莫斯科和南京進行了頻繁的交涉和接觸。”
12月13日,“孔祥熙在南京寓所召見蘇聯駐華代辦司皮禮瓦尼克說:西安之事,外傳與共黨有關,如蔣公發生危險,則全國之憤恨,將由中共推及蘇聯,將迫我與日本共同抗蘇。故促其速告蘇聯政府,并轉知第三國際注意。同日,駐蘇大使蔣廷黻訪蘇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要求蘇聯出面協助釋放蔣介石。”同一天,翁文灝致電蔣廷黻,要求其“在蘇俄酌量速妥接洽”。南京施加的壓力正中蘇聯的命門。這就決定了斯大林必將全力以赴地保證蔣介石的安全,絕不會也不可能僅僅停留在輿論方面的表態。
《中國新民主主義通史》說:“南京當局16日給蔣廷黻發去‘銑電,令其加緊與蘇聯當局交涉,注意搜集蘇聯與西安事變關系的證據,并詢問與蘇聯談判需要付出什么代價等。”南京突然提到“代價”,顯然是開始與蘇聯談判。更為過硬的證據是隨即發生的事實:(《周恩來年譜》說,同一天,“宋美齡表示愿同宋子文、顧祝同到西安會商。張學良表示歡迎。”17日下午,張學良突然派出飛機把周恩來接到西安。18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蔣態度開始表示強硬,現亦轉取調和。”需要指出的是,17日注定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重要日子,因為這一天毛澤東不再堅持“除蔣”,張學良迎接了周恩來,蔣介石也不再拒談。三人同時變化顯然不會是巧合。
蔣介石態度的轉變,實際上顯示談判的最后障礙消除。通常以為宋美齡信中所謂南京的“戲中有戲”改變了蔣介石的不合作態度其實是牽強附會不足為訓的,因為蔣介石完全知道當時唯一有需求也有能力救他的不是南京不是張學良更不是中共而是蘇聯。因此,“戲中有戲”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宋美齡讓端納給蔣介石帶來了蘇聯加入談判的信息。確實,惟有得知斯大林出手時,蔣介石迅速改變原先決不與張學良談判、不與周恩來見面的強硬態度才顯得順理成章。就此而言,西安事變中蔣介石真正的談判對手也應該是斯大林。
(二)暗渡陳倉的策略
盡管南京要求蘇聯“出面”,但蘇聯卻實施了暗渡陳倉的戰術,對張學良進行極其猛烈的公開譴責以掩人耳目,達到了一箭五雕的目的。
首先是撇清與西安事變的關系。事變一發生,蘇聯就斬釘截鐵地表明與西安事變毫無關系。12月15日,李維諾夫在回答蔣廷黻的求助時說:“我找不到這樣的辦法,因為自從張學良離東三省后,我們與他沒有任何聯系。”12月16日,蘇聯政府在授權司皮禮瓦尼克發表的聲明中說:“我政府不言而喻不論過去和現在都同西安事變沒有任何關系,而且自從日軍占領東三省后與張學良絕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間接往來。”
其次是建立了與南京的互信。蘇聯對西安事變的強烈譴責為雙方的談判掃清了障礙。12月19日,張群正式致電蘇聯政府,對“一向友好并同情中國政府的蘇聯政府的態度而表示感激”,保證“盡一切努力制止第三者在中國散布誣蔑性的含沙射影的說法。”國民政府絕不會僅僅看到蘇聯政府在報紙上的態度就表示“感謝”。
第三是動搖了張學良與中共中央的關系。蘇聯的表態使得張學良對中共中央大失所望。確實,那時的毛澤東除了表示繼續對西安事變堅定不移的支持,已經無法滿足張學良的其他訴求了。
第四是掩護了與張學良的談判。從13日起,張學良屢次公開表態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但周恩來17日晚在與張學良的會談一結束就致電“毛并中央”:“張同意在內戰階段不可避免圍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張學良這句話真正的解讀是,如果“兵諫”訴求無法實現,那“最后手段”就是唯一的選擇。宋子文在其日記中說:“漢卿直言不諱告訴我,其委員會已經決定,若一旦爆發大規模戰事,為安全起見,他們將把委員長交給中共。這決非憑空之威脅。”張學良亮出的底牌,表明當時張學良與蘇聯的談判正在緊張進行,因此這一表態不僅是告訴周恩來和宋子文,更是告訴斯大林和蔣介石的。
第五是對保安實施了雙重政策。首先是封堵了毛澤東的“除蔣”政策。蘇聯與南京、張學良的直接談判,對毛澤東的“除蔣”政策無疑是釜底抽薪。就此而言,毛澤東審時度勢權衡得失,主動改變“除蔣”政策也就有了最為合理的解釋。換句話說,毛澤東當時不是不想“除蔣”,而是無法“除蔣”了。但是,蘇聯由于不可能“出面”,因此要實現其訴求就必須為周恩來提供各種有效資源以加強其話語權。
歷史事實表明,蘇聯暗渡陳倉的策略是成功的。
(三)對談判的保密原則
迄今為止,西安事變各方秘密談判“頻繁的交涉和接觸”竟然未見任何檔案材料,它們究竟去了哪里?
蘇聯對外交的保密工作極其重視。自從1927年4月6日張作霖查抄了蘇聯駐北平大使館繳獲了眾多有損蘇聯形象的秘密文件后,蘇聯立即就吸取了教訓。據有關檔案記載:1927年5月12日,蘇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研究保密的會議,通過的決議中包括成立專門機構“修訂外交人民委員部、共產國際執委會、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和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關于保管檔案、發送和保管發往國外的密電和其他機密材料的程序問題的各種細則,以便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有必要派遣專人去中國,以保證銷毀所有多少有損名譽的文件,并防止其他人可能的暴露。”據歷史相關人士回憶:“莫斯科命令銷毀所有檔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個月的來往信件,保留的條件是:要使大使館一旦遭受襲擊時,能夠立即銷毀一切損害蘇聯政府名譽的材料。”毫無疑問,蘇聯參與其聯蔣政策引發的西安事變絕對是“有損名譽”的最大秘密,當然不會留下任何的文字證據,更何況絕對保密也完全符合當時談判各方的利益。
南京的需要。作為領袖,蔣介石必須在保持尊嚴的情況下獲得自由,當然不希望談判的內容外泄。《張學良年譜》說,當宋子文一見到張學良,“宋勸張對此次兵諫應早作一個面面俱到的妥善處理,原則是:不落痕跡,不公開附帶任何條件,先生安然離陜返京,立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原來“不落痕跡”是談判前就確定的原則,這就難怪蔣介石或宋子文的日記,都沒有絲毫關于秘密談判的內容。為了修補或掩飾可能露出的“痕跡”,甚至兩份日記竟然對蔣介石與周恩來會面日期的記載都可以不一樣。
中共中央的需要。在涉及如此重大又復雜異常的事變時,中共中央表現得非常慎重。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毛澤東告訴他“所草擬的電報,處處給張學良暗示,要他堅決對付蔣,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說出來,否則將來要留下痕跡的。”張國燾還說毛澤東“要周恩來設法銷毀一切同張、楊來往的證據。可能的話,也請張、楊方面毀滅這方面證據。”張國燾也提及了蘇聯,說“當時毛澤東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訊機構,以達到封鎖消息的目的。”“所有中共中央與莫斯科來往的密電”,“中共與西安方面的聯絡”,“概由毛澤東一個人包辦。”當時張國燾沒有參與核心機密,因此對其所見表象只能做偏頗的主觀臆測。其實,張國燾的這段回憶恰恰證明毛澤東當時確實嚴格履行了保密承諾,以支持與保證周恩來能夠在談判中爭取紅軍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是個人行為。
張學良的需要。從莫德惠赴蘇起張學良就開始嚴守機密,隨后不僅是實現“兵諫”訴求勢在必行的承諾,更是保證長久安全真正的護身符。因此,老調重彈又守口如瓶,就成為張學良唯一可靠而又無奈的選擇。學界對張學良有朝一日能夠“解密”的指望,其實從一開始就是一廂情愿,更何況宋美齡竟然不可思議地比張學良活得更為長久。
歷史事實已經證明,西安事變時各方有關秘密談判的相關電報都已蕩然無存,現在只能從當時的歷史事實中才能發現當年這些絕密電報確實存在過的蛛絲馬跡,其中比較過硬的材料除了前述國民政府與蘇聯的頻繁交涉、張學良駐莫斯科的秘密代表外,就是關于蔣經國的內容。
周恩來關于蔣經國回國的承諾是與蔣介石會談的重要籌碼之一,《博古傳》說:“會見中,周也與蔣略敘家常,蔣提及他在蘇聯的兒子蔣經國,言下之意微露思子之情。周告蔣,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他愿協助他們父子團聚。”另一本重要著述,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國共談判中的周恩來》也提及周恩來的承諾,說周恩來“并與蔣氏略敘家常,說到其子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蔣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滿口答應將助他父子團聚。”周恩來信息來源的及時與“滿口答(轉46頁)(接16頁)應”的背后,盡管沒有任何檔案文字可以佐證,但其答案應該是不言而喻的。當時莫斯科與中共中央之間電訊聯系的頻繁、周密與細致由此可見一斑。
作為歷史性證據,相關的歷史檔案雖然重要,但相關歷史當事人的具體行動顯然更為重要。歷史的辯證法表明,當歷史已經證明某項重要的談判確實發生過,卻匪夷所思地失去了談判內容的所有文字記載,那么這一共同“蒸發”的本身就是對當時會談各方共同采取保密措施的鐵證。關于這一點,史學界顯然還需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由于秘密談判中的蘇聯最為強勢,這就決定了唯一有能力實現各方利益最佳均衡者,非斯大林莫屬。這也許就是談判中的三方都付出了程度不同的代價,唯獨蘇聯大獲全勝的根本原因。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西安事變的發生,蘇聯對蔣介石有無可推卸的“虧欠”,當然不僅是鮑格莫洛夫的慫恿,更因為是蔣介石竟然與斯大林犯了一模一樣的錯誤,都未料到張學良竟敢用武力來“苦迭打”。也就是說,斯大林的疏忽也在無意中誤導了蔣介石。如此,戴笠不可思議的失誤以及事后竟未受嚴厲懲罰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斯大林在事變后的全力救蔣與抗戰中的全力援蔣,甚至在解放戰爭末期其駐華大使還緊跟著蔣介石,也就有了另一層雙方都心照不宣的原因。由此可見,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在日后漫長的歲月里都只字不提莫斯科與西安事變的秘密關系完全是理所當然的。至于蔣介石生前對張學良的一些“互動”,顯然不僅是“作秀”,更像是在提醒甚至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