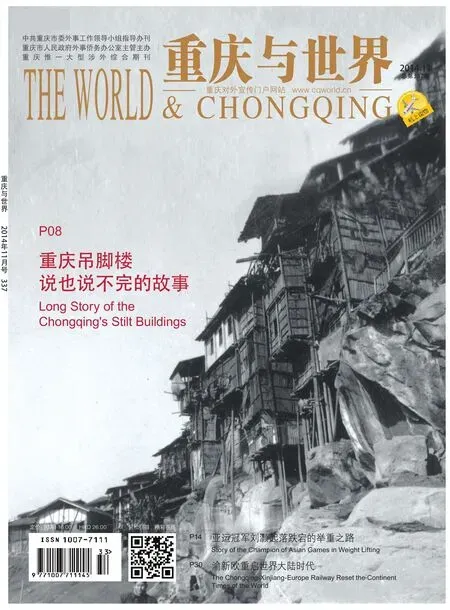釣城遺事成敗已定,忠奸難分
文/本刊記者 吳俊琰
釣城遺事成敗已定,忠奸難分
Incidents of the Diaoyu Town in the Past Ages
文/本刊記者 吳俊琰
在中國(guó)漫長(zhǎng)的歷史中,從來(lái)不缺少忠臣良將。而有宋一代盡忠死節(jié)之人可謂冠絕列朝。其他朝代都有盜賊強(qiáng)梁猖獗到危害國(guó)家社稷的時(shí)候,宋朝卻沒(méi)有發(fā)生過(guò)足以威脅王朝統(tǒng)治的內(nèi)亂,即便是在所謂“奸臣當(dāng)?shù)馈钡臅r(shí)候,也仍然有很多剛正不阿的士大夫一心定國(guó)安邦。
但積貧積弱的宋朝大半輩子都活在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的威脅之下,好不容易等到遼滅亡了,又得面對(duì)新崛起的金;聯(lián)蒙抗金勝利了,又得面對(duì)野心勃勃的蒙古人——也是時(shí)勢(shì)造英雄:宋朝,這個(gè)成吉思汗不屑一顧的弱鄰,卻成了蒙古大軍征戰(zhàn)亞歐大陸過(guò)程中最硬的一塊絆腳石。硬到什么程度呢?硬到成吉思汗、窩闊臺(tái)、貴由、蒙哥四代大汗都沒(méi)能拿下,硬到僅在合川釣魚(yú)城就硌死了蒙古先鋒猛將汪德臣和將蒙古疆域擴(kuò)張至前無(wú)古人的大汗蒙哥。蒙哥死后,蒙古內(nèi)部由于爭(zhēng)奪汗位而四分五裂,不得不停下在亞歐大陸擴(kuò)張的步伐。
忠義祠真的“忠義”?
在堅(jiān)守釣魚(yú)城期間打死汪德臣和蒙哥的主將王堅(jiān)自然是名垂青史、功震朝廷,受封寧遠(yuǎn)軍節(jié)度使——這是宋朝武將至高無(wú)上的榮譽(yù),獲此殊榮的還有岳飛和南宋砥柱孟珙等著名將領(lǐng)。戰(zhàn)后合州軍民感其忠義,為之建立祠堂紀(jì)念。與之同樣受人供奉的還有他的前任:東川地區(qū)“山城防御體系”的完善者、四川制置使余玠,王堅(jiān)副將、重慶知府張玨,“播州(今遵義)義士”冉琎、冉璞兄弟。
祠堂名“忠義祠”,始建于明孝宗弘治年間。最初因?yàn)橹还┓钔鯃?jiān)、張玨而命名為“王張祠”,清兵入關(guān)時(shí)毀于兵燹。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合州知州王采重建祠堂并增祀余玠、冉氏兄弟,更名為“忠義祠”。不久后,吳門(mén)(今江蘇蘇州)陳大文知合州,把王立、李德輝、熊耳夫人請(qǐng)進(jìn)“忠義祠”。
但陳大文這個(gè)舉動(dòng)可捅了大簍子了。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遵義華國(guó)英知合州,修繕忠義祠,立“重建忠義祠碑”,把上述三人牌位移出。碑文記載:“(王立)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以之從祀,是為瀆祀。”鄙視、不屑之情溢于言表,把這位釣魚(yú)城最后的守將貶得一文不值。忠義祠前至今仍保留著華國(guó)英所撰楹聯(lián):
“持桿以釣中原,二三人盡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盞而澆故壘,十萬(wàn)眾披肝瀝膽,竟不圖王立貳心”
這就說(shuō)得更煞有介事了:釣魚(yú)城的將是忠的,士兵是頑強(qiáng)的,就這個(gè)王立,是個(gè)叛臣降將、持二心的人,忠奸對(duì)立何其分明啊,怎么能夠在“忠義祠”里祭祀他呢?勸說(shuō)王立投降的熊耳夫人也被當(dāng)成是紅顏禍水,同招降釣魚(yú)城的李德輝被移出了忠義祠。
抗戰(zhàn)時(shí)期,郭沫若游覽釣魚(yú)城,曾賦詩(shī)一首,現(xiàn)刻于山崖之上,詩(shī)曰:“卅載孤稱(chēng)天一線(xiàn),千秋共仰宋三卿。貳臣妖婦同祠宇,遺恨分明未可平。”“宋三卿”指余玠、王堅(jiān)、張玨,“貳臣妖婦”分別指王立、熊耳夫人。郭沫若此詩(shī)大有恨不能將王立、熊耳夫人扒皮抽骨的意思,甚至連祭祀他們的陳大文也要被掘墓鞭尸。考慮到抗戰(zhàn)時(shí)的特殊情況以及郭沫若本人并不了解那段史實(shí),做出這樣淺薄的見(jiàn)解也情有可原。
不過(guò),王立到底做了什么事讓他承受如此罵名呢?
正史實(shí)無(wú)可考(事實(shí)上,元脫脫編撰的《宋史》并不嚴(yán)謹(jǐn),同樣沒(méi)有為王堅(jiān)立傳。此外,“奉旨填詞”柳三變、“大宋提刑官”宋慈、“三外野人”鄭思肖等人都未收錄)。但是《元史·李德輝傳》中提及王立,證明此人確實(shí)繼張玨之后鎮(zhèn)守釣魚(yú)城。不同的是,王立并沒(méi)有像他的前任那樣寧死不屈,而是在元安西王相李德輝的勸說(shuō)下棄城投降了。所以,他的前任受人尊敬,而王立卻飽受爭(zhēng)議。
釣魚(yú)城最后的守將:叛臣降將?
他是值得尊敬的英豪,還是賣(mài)主求榮的貳臣?
1275年,戰(zhàn)功卓著的釣魚(yú)城守將張玨調(diào)任重慶,主持四川地區(qū)抗元大局。其后不久,王立奉命守城,可以說(shuō)是臨危受命。此時(shí)的南宋朝廷已經(jīng)千瘡百孔、岌岌可危了。曾支起南宋半壁的西川戰(zhàn)區(qū)在蒙古大軍連年征伐之下地乏民疲,支離破碎了。甚至,由于蒙古大軍封鎖,釣魚(yú)城曾“三年不通誥命”——當(dāng)時(shí)沒(méi)有無(wú)線(xiàn)電,也沒(méi)有移動(dòng)和聯(lián)通。本來(lái)抗戰(zhàn)就已經(jīng)變得很艱難了,還到處都是噩耗頻傳。1276年,南宋謝太后抱著年僅5歲的南宋恭帝對(duì)元投降,標(biāo)志著南宋朝廷正式滅亡。這個(gè)時(shí)候還不忘關(guān)照一下聲名遠(yuǎn)揚(yáng)的釣魚(yú)城:你就從了吧,大宋宗室都投降了,你們還反抗個(gè)什么勁呢?
宋亡的事實(shí)肯定給張玨、王立等人很大打擊,雖然尚有二王(趙昰、趙昺)南逃,也不過(guò)是茍延殘喘罷了。但王立仍拒絕投降。是什么原因呢?我們可以大致思考一下。
首先,不得不佩服宋朝的“忠孝節(jié)義”觀念實(shí)在是太深入人心了,王立肯定受到這種觀念制約,不愿背負(fù)罵名:在得知二王出逃后,王立就增筑“宮殿”,準(zhǔn)備迎二王入蜀。其二,南宋朝廷雖已滅亡,但精神寄托還在,不到萬(wàn)不得已,他也不會(huì)投降。其三,他的老上司張玨鎮(zhèn)守重慶,釣魚(yú)城為重慶門(mén)戶(hù),互為唇齒,他受張玨器重,不能在這個(gè)時(shí)候拆他的臺(tái)啊。當(dāng)然,理由很多,但最重要的,應(yīng)該是因?yàn)獒烎~(yú)城抗戰(zhàn)經(jīng)歷是在太輝煌了,以至于蒙哥曾留下遺言:“我之?huà)爰玻瑸榇顺且病2恢M之后,若克此城,當(dāng)盡屠之!”(光緒《合州志》卷十二)釣魚(yú)城與元朝管理這片地區(qū)的東川行院本就勢(shì)不兩立,而且,蒙古軍隊(duì)可是說(shuō)到做到,僅僅成都一城,便遭到蒙古軍隊(duì)屠殺兩次……戰(zhàn),軍民皆亡;降,軍民皆亡,但戰(zhàn)死還能落個(gè)好名聲,除了抵抗,還能怎么辦呢?
三年過(guò)去,元軍還是沒(méi)有攻下釣魚(yú)城,不過(guò)這時(shí)候,戰(zhàn)事已經(jīng)出現(xiàn)轉(zhuǎn)機(jī):連續(xù)兩年大旱讓釣魚(yú)城內(nèi)幾乎彈盡糧絕;因?yàn)榕淹匠鲑u(mài),重慶城破,張玨被俘,于押解大都途中“解弓弦自盡”。從此,釣魚(yú)城成了孤城,就像風(fēng)暴中的舴艋舟,隨時(shí)都可能被風(fēng)浪打翻——釣魚(yú)城城破之日就是城內(nèi)百姓亡身之時(shí)。
這個(gè)時(shí)候,元西川行樞密院(簡(jiǎn)稱(chēng)西川行院)副使兼安西王相李德輝(《元史·列傳第五十》)堅(jiān)持對(duì)釣魚(yú)城招降,并稱(chēng)可保釣魚(yú)城全城百姓平安(沒(méi)有說(shuō)可以保住王立的性命)。在進(jìn)退維谷的情況下,王立有了投降的心思,但礙于名節(jié),舉棋不定。
話(huà)說(shuō)也巧,王立身邊有個(gè)寵室,乃是當(dāng)年王立奉張玨之命攻占瀘州時(shí)于亂軍中所獲,帶回釣魚(yú)城后以“義妹”相稱(chēng)。不過(guò),這個(gè)“義妹”有連王立都不知道的身份:她是被王立所殺的瀘州戰(zhàn)將熊耳之妻,更是李德輝同母異父的妹妹(一說(shuō)是表妹),后世稱(chēng)之為“熊耳夫人”。她看出王立有投降的心思,便暴露身份,勸其投降,讓他以個(gè)人名節(jié)為輕,以全城軍民性命為重。
于是,李德輝負(fù)責(zé)勸止屠城,王立負(fù)責(zé)撫軍安民,在一個(gè)風(fēng)和日麗的早晨,二人城外相見(jiàn),共同宣告釣魚(yú)城抗戰(zhàn)終止——四川最后一塊難啃的骨頭就這樣被拿下了。此時(shí)是公元1279年,崖山之戰(zhàn)前不到一個(gè)月。
有著36年抗戰(zhàn)優(yōu)良傳統(tǒng)的釣魚(yú)城就這樣陷落了,難免讓人產(chǎn)生心理落差,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輝也因此受爭(zhēng)議不斷。李德輝還好,他本是元臣,所做之事不過(guò)是盡忠職守,而且有恩于釣魚(yú)城軍民,受人祭祀并無(wú)不妥。不過(guò)熊耳夫人是個(gè)有大局觀的巾幗呢?還是敗壞忠烈風(fēng)骨的禍水呢?王立是個(gè)知天命、盡人事的英雄呢?還是個(gè)沒(méi)有氣節(jié)的叛臣降將呢?
王立在宋亡之后仍然領(lǐng)導(dǎo)釣魚(yú)城抗戰(zhàn)3年,這種行為已經(jīng)足以證明他對(duì)朝廷的忠誠(chéng)。而且,據(jù)野史記載,王立降元后差點(diǎn)被東川行院殺害,幸好李德輝和安西王從中周轉(zhuǎn),忽必烈親自降旨赦免,并封他為安西王府的大將。后來(lái),王立在征討察合臺(tái)汗國(guó)中戰(zhàn)功卓著。但他最終為尋找宋的宗室而被統(tǒng)治者賜死。這樣看來(lái),王立的投降實(shí)在是難能可貴的:犧牲個(gè)人名節(jié)、保全全城軍民,完全就是一樁“損己利人”的買(mǎi)賣(mài)。這要拿到現(xiàn)在,不說(shuō)拿諾貝爾和平獎(jiǎng),拿個(gè)感動(dòng)中國(guó)是沒(méi)問(wèn)題的。在滿(mǎn)朝文武視名節(jié)如生命的宋朝,王立雖然落下個(gè)“叛臣”的罵名,但卻堪稱(chēng)是“人道主義”的典范。
在釣魚(yú)城之戰(zhàn)前一百多年,西方舉世聞名的十字軍東征期間,十二世紀(jì),在第二次十字軍和第三次十字軍東征之間,伊貝林的小貝里昂(Balian d'Ibelin)曾在薩拉丁大軍強(qiáng)攻下拼死守衛(wèi)圣城耶路撒冷,迫使薩拉丁與之講和,保全圣城的騎士團(tuán)安全撤出。貝里昂并無(wú)太多出色戰(zhàn)績(jī),卻因?yàn)閭ゴ蟮娜说乐髁x功績(jī)而受人稱(chēng)頌。釣魚(yú)城守將王立比之不遑多讓?zhuān)覀兪遣皇菓?yīng)當(dāng)從更現(xiàn)實(shí)的角度來(lái)看待那些古人們由于時(shí)代原因而無(wú)法公正判斷的事情呢?
不過(guò),歷史本就沒(méi)有絕對(duì)的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遼宋夏金元的迭代也不過(guò)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無(wú)論是王立、李德輝,還是王堅(jiān)、余玠他們恐怕都想不到,在領(lǐng)土上征服中原的民族卻最終拜服中國(guó)文化,在不斷學(xué)習(xí)融合的過(guò)程中,逐漸與中華文化同化,成為中華民族絢爛多姿的大家族中一顆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