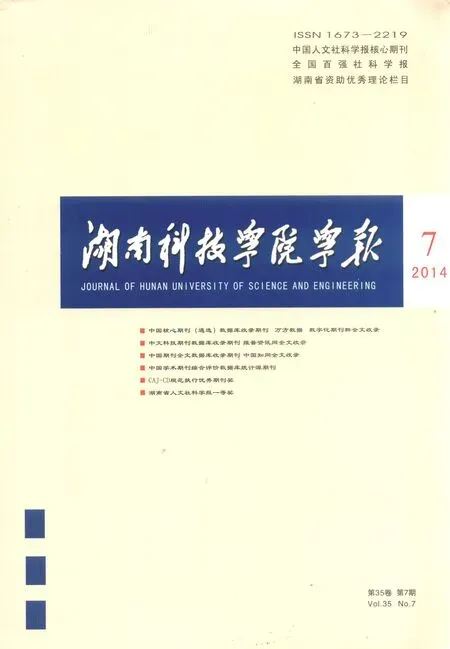格賴斯循環在關聯下的消解
許小艷
(西安交通大學 外國語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9)
始于 20世紀初的理想語言哲學主張把自然語言形式化,把句子意義歸為其真值條件,由句子成分的意義與其組合方式決定。與之相反,日常語言哲學認為,采用邏輯的方法研究自然語言會掩蓋其本質,從而倡導用描述的方法來研究,強調它的語用特征,其結果是語用學的誕生。但是,如果承認存在語用侵入(pragmatic intrusion)對話語解釋的必要性就會出現一個語義解釋和語用解釋孰先孰后的問題。這是任何格賴斯理論都需面對的問題。Levinson提出,如果承認語用侵入語義內容不可避免,我們就需要依賴所含(implicature)來明確指示語、解釋歧義、完成語用充實或語義收窄等語用處理獲得所言(what is said),而所含又必須以所言為輸入,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這就是格賴斯循環(Grice’s circle)。
應該說,格賴斯循環并不是語用學發展的絆腳石,而是其動力。正是由于怪圈問題的出現,才會使眾多語用學者重新反思語用學,提出新的語用理論或原則,比較有代表性的是 Hawley、Capone、徐盛桓等。也有學者認為,格賴斯循環是語用學家區分所言和所含過于絕對的結果。但是,這些論述都沒有對格賴斯循環產生的根源進行哲學上的反思,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可能會有異議。鑒于此,本文試圖首先通過剖析格賴斯循環產生的哲學基礎,以基于關聯的話語解釋來消解格賴斯循環,之后分析交際行為和語用推導過程的復雜性,最后提出存在一種類似于格賴斯循環的言語交際策略。
一 格賴斯循環的哲學基礎
傳統上,處理真值條件語義學和語用學的方式是:“所言是推導所含的語用處理的輸入,即所含的計算要以所言為基礎。所言等同于句子所表達的命題或話語的真值條件內容,反過來又依賴于指稱的確定、指示語的析解以及歧義的明確。”如果接受該觀點,就會出現:“所含在生成所言的過程中也發揮作用。這就出現一個雞和蛋孰先孰后的問題,即所言和所含孰先孰后?”
需指出,Levinson在這里似乎將說話人的意圖等同于所含。如下圖所示,這就出現說話人的意圖(或所含)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作用于所言的建構(語用處理 3),但所言建構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說話人的意圖(語用處理1和2),這卻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語用處理過程,格賴斯循環由此產生。

從該圖來看,格賴斯循環可分解為以下2個假設:
(a)所言優先假設:所言是推導所含的唯一條件(語用處理 2),即語用學以語義學為其輸入;(b)所含依賴假設:所含對所言的建構發揮作用(語用處理 3),即語義學需以格賴斯意義上的語用學為條件。
新格賴斯語用學者的解決方案多針對所含依賴假設(b),即所言的生成并不依賴說話人的意圖即所含。這類方案實質是將語用入侵真值條件內容這一階段(語用處理1)看作是不依賴于說話人意圖的推導,因此具有語義學性質,比如Recanati的第一語用處理,Capone的普遍語義語篇原則,徐盛桓的常規推理等。問題是所言的建構(語用處理1)似乎或多或少總是受制于交際者的意圖,這些方案實際上并未完全擺脫格賴斯循環。
實質上,這個怪圈的產生源自語義學和語用學的話語解釋地位之爭。具體是,語義學試圖保持其地位,而讓語用學僅限于處理所含推導的語用過程,Leech稱為語義/語用的互補觀。為分析該思想的問題,Levinson提出格賴斯循環,認為“這一怪圈折磨著任何一個通過區分語義學和語用學來解釋意義的理論。”也就是,只要將所言建構的處理過程看作是語義學的而非語用學的,這樣的怪圈必然出現。
對于語義學的地位問題,Grice將規約所含(conventional implicature)排出在所言之外似乎已在暗示,對所言的研究應該是語義學的,只有那些脫離真值條件內容之外的意義處理才是語用學的研究對象。此后,眾多新格賴斯語用學者繼承了這一觀點,通過提出各種語用理論或原則來為所言和所含劃清界限,以此保證語義學在話語解釋中的地位。最具代表性的是 Levinson對語用學所下的定義:“語用學=意義-真值條件。”而Rumfitt批判Strawson的交流—意向論,提出言語交際不能脫離語句的真值條件,僅用意圖就能獲得滿意的解釋。這可看作維護語義學地位的一個哲學嘗試。
雖然語義學和語用學都以意義為研究取向,但傳統看法是,語義學研究符號與其所指的關系,而語用學研究符號與其解釋者之間的關系。通俗來講,語義學關心的是語言與客觀世界的關系,亦即語句與事物的狀態是否相符,但語用學關心語言與使用者的關系,特別是語言在特定語境下的使用。結果是,二者對待真實性(truthfulness)的兩個完全不同的視角:語義真實性是組合性的,句子是否為真,取決于其與客觀或可能世界之間的嚴格對應;而語用真實性具有主觀性,只要交際雙方能夠接受信息傳遞方面的某種近似性,且不影響當前的交際意圖,就可認為這一話語是真實的。
語用學與語義學的以上差異實質上源自日常交際中話語的特殊性。一般來說,交際中的任何話語都是說話人有意向的使用,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即通過使聽話人認識到我有一種要他知道我的意義的意圖,從而使聽話人知道我的意義。為了讓聽話人意識到說話人意圖什么,說話人就必須選擇那些能夠讓交際雙方都能夠理解的話語,通過該話語,聽話人能夠推知說話人所要交際的意義,并且認為這就是他所要交際的意圖。在這個意義上的言語交際可以看作是以相互理解為導向的社會交際行為,從而具有以此為基礎的主體間性特征。但是,由于語義學以研究語句與客觀世界的對應關系為旨趣,是將話語看作是描述客觀世界狀態的工具進行的研究,必然無法合理解釋作為語用學研究對象的言語交際行為。換言之,用把話語看作非社會性的工具行為的語義學來解釋具有社會性的交際行為必然會導致格賴斯循環的出現。
二 格賴斯循環在關聯下的消解
基于關聯理論以主體間性為其特征的交際行為可看作說話人發出的明示刺激,即說話人設計來吸引聽話人的注意力,并讓聽話人把注意力轉向他交際意圖的刺激。為了達到相互理解,這種刺激自身都攜帶著最佳關聯的假設,也就是:(1)明示刺激具有足夠的關聯性,值得聽話人付出努力進行處理;(2)明示刺激與說話人的能力和偏愛相一致,因而最具關聯性。對聽話人來說,話語的理解過程是一個推理過程。說話人發出的這一明示刺激能夠在聽話人的大腦中激活與之相關的心理概念,形成邏輯式,并以此為起點,結合語境信息沿著消耗最少心力的路線進行非論證性(non-demonstrative)演繹推理,直至滿足他對關聯的期望。簡言之,話語的解釋過程是在最佳關聯調控下的信息提取、加工與合成的過程,該過程也可以用下面的話語解釋程序來表示:
第一步:遵循計算認知效果時耗費最少心力的路線,特別是以可及程度來檢驗解釋性的假設(interpretive hypotheses)(如解歧、確定指稱和隱義等);
第二步:當對關聯的期望得到滿足時停止。
從這個角度看,話語理解的整個過程(即上圖提到的語用處理1和2)都是聽話人基于該話語解釋程序進行推導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聽話人推得的任何意義都是說話人意圖的體現,受說話人在特定語境下的意向性保證。基于此,顯義和隱義的獲得只存在推理過程或方式上的差異。Carston認為隱義具有功能上的獨立性,這一特征可能是由于其推導路徑長于顯義從而具有可取消性特征(即推導的非單調性)。Levinson對這一特征的批評似乎并不能改變顯義推導的語用學性質。一旦我們像這樣將話語解釋完全納入到基于關聯的話語解釋程序,類似于格賴斯循環這樣的怪圈就不復存在了。很多學者對于顯義和隱義基于關聯的推導有過詳細的論述,具體可參見Carston、Wilson & Sperber等,在此不再贅述。下面,本文試圖跳出語言語用學的拘囿,從基于關聯的話語解釋出發,通過展現交際行為以及意圖推導的復雜性來消解上文提到的所言優先假設和所含依賴假設。
(一)所言優先假設的消解:交際行為的復雜性
一般來說,理性的交際行為可以分為言語和非言語交際行為兩類,前者的優勢僅在于其更高程度的精確性和復雜性,語句和言語交往行為中的其他信息一樣,都可以作為明示刺激,即自身攜帶最佳關聯假設,成為隱義推導的前提。從某種意義上講,言語交際行為是強交際,它引進了一個顯現(manifest)的成分,即話語自身,而非語言交際行為永遠都是隱含的,屬于弱交際。作為推導交際意圖的證據之一,話語需要聽話人調用認知語境中的信息將其充實為完整的命題,這個推導過程相對于非言語交際來說容易很多。新格賴斯語用學正是基于此而過度地強調了話語在推導交際意圖中的地位,其本質是一種話語優先的表現,即聽話人必須首先建構話語的顯義才能理解這句話所傳遞的隱義。
但是,任何一個言語交際行為都必然會使聽話人激活除顯義之外的一組命題,這組命題可能以說話的方式、說話人的手勢或面部表情等副語言特征、甚至是話語中的信息片斷為觸發條件,換言之,言語交際行為中的任何特征都可以成為明示刺激,成為推導交際意圖的手段。因此,在成為明示刺激之前,話語與其他言語交際行為中的信息對聽話人的認知處理來說是平等的。對于副語言信息的作用,我們可以通過下面的例子來說明。
例(1):(愛人問我對好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的看法)愛人:喜歡不?
我:(撅撅嘴)
這是一個非言語交際行為,我用了“撅嘴”這個明示刺激表達了“我并不喜歡該禮物”的隱義。對聽話人來講,她需要激活自己的認知語境進行類似于“說話人并不喜歡該禮物”的命題建構。當然,副語言特征也能夠起到襯托話語的作用。
例(2):(回家路上,覺慧和覺民討論先生的《寶島》如何表演后)
“二哥,你真好,”覺慧望著覺民的臉,露出天真的微笑。覺民也掉過頭看覺慧的發光的眼睛,微笑一下,然后慢慢地說:“你也好。”(巴金《家》)
在該例中,覺慧和覺民雖然笑不同,但都恰當地襯托出他們真誠的言語,兄弟之情溢于言表。如果我們把該例中的對話看作是明示刺激,那么這兩個“笑”才是真正的“副”語言行為,是輔助明示刺激推導的規約符號,“說話人通過這類輔助交際特征確保了聽話人獲得他想要交際的內容。”
實際上,任何一個言語交際行為都可以看作是兩類信息的傳遞:副語言信息與話語內容。前者可再分為兩類:(1)說話人的身體信息,即說話人的面部表情、頭部運動、眼睛移動以及手勢等規約化了的行為;(2)話語的物理特征,即話語的聲音特征,如說話的聲調、語氣、方式等等。所有這些信息似乎能夠形成一個明示刺激集合,都可以成為推導交際意圖的前提,都是說話人思想表征的證據。新格賴斯語用學存在的問題恰恰是,把話語充實而成的真值條件內容看作是思想的表征,忽視了由其他因素激發的命題成為該表征的可能性。
(二)所含依賴假設的消解:顯義到隱義推導的復雜性
格賴斯循環生成的第二個假設是,所含推導的起點是所言,這恰恰反映出新格賴斯語用學過分簡約所言和所含之間關系的傾向。首先,在日常生活中交際雙方常常在隱義的層次上進行交際,似乎拋開了顯義的真值條件,比如下例:
例(3):(丈夫坐在電腦旁寫論文,妻子在廚房里喊)妻子:飯菜都涼了!
對丈夫來說,這句話是否為真已不重要,妻子的意圖是叫他趕緊去吃飯,假如他回答說“不會涼的”,妻子也不會跟丈夫爭論說飯菜到底涼了沒有,而認為這是他賴在電腦邊不肯走的借口。一般丈夫會說“好的”來表示這就去吃飯。在這種情況下,隱義雖然由話語激活,但人們似乎并不關心顯義的真假。交際雙方關心的是隱義而不是顯義的建構,由此就會產生這樣的情況:即使聽話人沒有聽清話語中的某個詞語,他也可能根據語言片斷或副語言特征等信息推導出說話人的隱義,獲得交際意圖。比如邀請朋友周末一起去看電影時,朋友回答:“我還要加班呢。”即使沒有聽到“加班”這兩個字,也照樣可以推知朋友不會和我一起去看電影的結論。
實際上,顯義和隱義的這種關系源于話語和思想關系的復雜性。如果我們把話語看作是反映說話人思想的語義表征,這個表征如何間接地反映說話人的思想表征,它是否是其他表征的表征,是否這個元表征才是說話人的思想表征等等,這一切都由說話人決定,比如:
例(4):(A、B二人談論B的口吃治療)
A: Did your treatment for stammering work?
B: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
A: How amazing!
B: Yes, b-b-but th-th-that’s not s-s-something I v-v-very often w-w-want to s-s-say.
此例中,B的第一次回答向A提供了口吃被治愈的直接證據,是 B思想表征的直接體現,并不是語言交際,因為話語只能提供給說話人思想表征的間接證據,如 B以“Yes”來應答。B第二次回答的方式提供了口吃沒有被治愈的直接證據,而在內容上提供了間接證據。如果話語內容不確定,聽話人理論上可以遵循“除真值條件內容之外的明示信息→隱義→顯義”這樣的路徑進行推導,從而出現利用隱義推導顯義的情況。換句話說,一個言語交際行為是一組語言和副語言信息的集合,話語的真值條件內容只是其中之一,聽話人完全可以利用除此以外的明示信息,比如說話的方式、話語片斷等直接推得隱義。言語交際中常常出現口誤現象,卻也能被聽話人正確地理解,就是這個原因。當然,還可能有其他情況,比如,聽話人不理解或無需理解話語,便能獲知隱義;話語的字面意義不準確或不正確,聽話人仍能推得隱義等等。值得注意的是,Sperber & Wilson還提出了一個并行調整機制(parallel adjustment)來解釋以上現象,指的是顯義和隱義之間可以通過相互調節以滿足交際的最佳關聯,這也體現了顯義和隱義之間關系的復雜性。總之,通過話語建構而成的顯義只是將話語作為一個語義表征進行了顯微鏡式的觀察,它與說話人思想表征的關系并不因此而簡化。
三 作為交際策略的格賴斯循環交際行為
新格賴斯語用學者通過引進新的語用原則似乎解決了格賴斯循環,但在言語交際中似乎存在一種顯義和隱義都無法確定的類似格賴斯循環的言語交際現象,比如下例:
例(5):(甲、乙兩位語言學者在談論學者丙,甲問)
甲:丙的這本專著怎么樣?
乙:挺流行。
這里,乙話語中的“流行”既可以解釋為銷量很好、很成功,也可以指該書屬于普通讀物,缺少學術價值。當然,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這是乙故意這樣回答從而把任何隱義的推導都歸為聽話人的責任,但從聽話人的角度看,如何理解乙的回答依賴于甲的意圖——贊賞或貶低這本書,這樣就會產生顯義和隱義相互依賴的情況。這種類似格賴斯循環的交際現象可以看作是說話人利用顯義和隱義的相互依賴來傳遞某種特定的交際意圖的語用策略。再來看一例:
例(6):(教師甲和教師乙在談論剛上任的教學副院長)
甲:你覺得她怎么樣?
乙:是個鐵女人。
這是一個典型的語用含糊現象,乙的隱喻回答能夠激活交際雙方的共有印象,使大量的假設微弱地顯現,以此來達到最佳關聯。但這并未解決“鐵”的含義問題。在這里,它可以解釋為:“做事果斷、干練”,“對人不留情面”,“做事理智”,“不易讓人接近”等含義。雖然這些都是“鐵”作為隱喻的語義塑造,雖然它們都可能是說話人的意圖所在,但是假如甲事先了解乙對該副院長的態度,他就能夠更確切地理解“鐵”這個詞。從這個意義上看,似乎這正是乙想要達到的效果。對說話人而言,他故意利用一些類似籠統、模糊、不確定的詞語,讓聽話人無法根據顯義推知確定的隱義,從而達到傳遞特定交際意圖的目的;對聽話人而言,他既無法通過確定顯義而獲得說話人確定的意圖,也無法通過說話人的意圖來確定顯義,從而認為這才是說話人的交際意圖。顯義和隱義相互依賴,于是都無法確定,這似乎印證了格賴斯循環的存在,可這正是說話人的交際意圖,因而產生了這樣一條推導路徑:“由于顯義不確定而無法推得確定的隱義+相關的認知語境信息→特定的隱義”。
Grice將所言看作是“明確句子中的指稱、確定說話時間以及弄清特定情境下詞語的意義”的結果。同時他將除真值條件內容之外的所有意義看作所含,這種處理方式暗示了語義學參與話語解釋的可行性。新格賴斯語用學并未擺脫這種語義/語用互為補充的觀點,格賴斯循環就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產生。這個怪圈源自人為規定所言屬于語義學,從而出現語義學為語用學的輸入但卻依賴語用學這樣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因此,眾多格賴斯語用學者通過引進新的語用理論或原則來解決這個怪圈,這雖然促進了語用學的發展,但由于沒從這個怪圈的根源著手,格賴斯循環似乎仍隱現其中。
本文認為,言語交際中的話語是以交際理性為基礎,受交際者的意向性支配、以主體間性為特征的交際行為。這一特征暗示,對話語的整個解釋只能由語用學來完成,盡管該過程可能需要借用語義學中的一些觀點或概念,但這并不能改變整個解釋過程的性質。從認知的角度看,交際行為的這一特征可以看作是自身攜帶有最佳關聯假設的明示刺激,能夠讓聽話人沿著消耗最少心力的路線進行推導,從而獲得說話人的交際意圖。這種基于關聯的話語解釋程序不僅徹底消解了格賴斯循環,還充分展現出了交際行為和語用處理的復雜性,甚至還會出現類似于格賴斯循環的交際策略。
[1]Capone,A.On Grice’s circle[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6(5):645-669.
[2]Carston, R. Implicature, explicature, and truth-theoretic semantics[A].In R.Kempson(ed.),Mental representations:The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155-181.
[3]Carston,R.Linguistic meaning, communicated meaning and cognitive pragmatics[J].Mind and Language, 2002(17): 127-148.
[4]Grice,P.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5]Hawley,P.What is said[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2,(8):969-991.
[6]Leech,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London:Longman,1983.
[7]Levinson,S.Pragma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8]Levinson,S.Presumptive Meanings: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0.
[9]Morris,W.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A].In O.Neurath, Carnap&C.Morris(ed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C].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77-138.
[10]Recanati,F.Does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rest on inference?[J].Mind & Language,2002,(17):105-126.
[11]Recanati,F.Literal Mean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2]Rumfitt,I.Truth conditions and communication[J].Mind,1995,(416):827-862.
[13]Strawson, P. Meaning and truth[A].In A.P.Martinich(ed.).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91-102.
[14]Wilson, D. & D. Sperber. Linguistic form and relevance[J].Lingua,1993,(90):1-25.
[15]陳新仁.論語用的真實性[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7,(9):1-3.
[16]龐加光.語用含糊的認知語用分析及其語用化[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8,(4):13-17.
[17]熊學亮.認知語用學概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18]徐盛桓.常規推理與“格賴斯循環”的消解[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6,(3):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