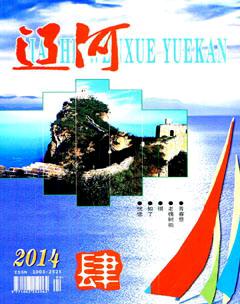正月燈籠紅
楊鵬杰
正月里,徜徉在月色燈影包圍中的刺勒川公園,望著一個個孩童小手牽拉著大手,好奇地在各式花燈垂掛、燈樹叢生、人山燈海的廣場上歡快地穿梭嬉戲,望著燈籠那一閃一閃的橙紅色光團隨風流轉,兒時過年玩燈籠的點滴趣事不由得再次涌入腦海。
記得那還是上世紀70年代末,北方的初春似乎更多的沿襲著冬日的清冷,立春前后依然是寒風凜冽,吹得人瑟瑟發(fā)抖、直縮脖子。進了正月,常常還有皚皚白雪固守著冬的執(zhí)著,靜靜地鋪滿土默川大地,也給每一條街巷里每一盞或大紅或五彩、或走馬或水晶的燈籠統(tǒng)統(tǒng)戴上了雪絨帽,而隨風起舞的雪花時不時地從屋頂、樹梢上打著旋兒飄落到踏雪賞燈的大人額頭上沾掛在挑著燈籠嬉笑打鬧的孩童嘴角。此刻,嘴饞的孩童們會趕忙用舌尖去舔舐那花開六瓣的如飴雪凌,一絲絲清甜甘涼頓時嗖嗖地滑過喉嚨,鉆進心底,一忽兒就激靈靈傳遍全身,仿佛品到了瓊枝玉液似的,瞬間讓這些最盼望過年時可以穿新衣、放鞭炮、走親戚、掙壓歲錢、挑燈籠的孩子們進入正月十五雪打燈那宛如美麗童話般的仙境了。
小時候,在舊城大什字、大南街一帶,從臘月里,街邊便有了賣燈籠的攤點,挨到正月十五,滿街更是紅彤彤一片,那是倒春寒的嗖嗖冷風吹紅的一張張笑臉,那是隨風搖擺如迪斯科的宮燈、花燈、走馬燈的喜悅。街道上隔一兩天還會有一位賣燈籠的小販推著滿滿一排子車的各式燈籠和一些年貨,走街竄巷的叫賣。曾聽老人講,小販是從托縣上來的一位花燈藝人,每一盞燈籠都是以竹為支架的傳統(tǒng)手工制作,從削竹篾、開尺寸、扎竹架、糊紗紙(或絹布)、畫圖案、上色到掃金油,步驟可謂相當復雜,沒有點真功夫和審美藝術是扎不出像樣的燈籠的。每當遠遠地聽到小販的吆喝聲,我們這幫孩子可就按耐不住了,不管小子還是女娃,三五成群的從家里跑出來,跟在賣燈籠小販后面,走德勝街,穿剪子巷,過上柵子,上梁山街,東轉西逛,一路還幫著叫好喝彩、招攬顧客,完全把回家吃飯、大人的斥罵拋到了腦后,屁顛屁顛地不亦樂乎。
那時過年,因普通家庭收入微薄,一般是舍不得花錢買燈籠的,大都是自己制作或者向有制作燈籠手藝的親友鄰里求一盞來掛著,祈愿能照亮來年紅紅火火的好光景。我家的燈籠就出自父親神奇的雙手。有時候,一些街坊鄰居也會禮尚往來的端著些麻葉馓子、糖果丸子來求父親做燈籠。父親是來者不拒,找來鐵絲、彩紙、漿糊、鉗子、剪刀、蠟燭等開始扎制燈籠,于是整個臘月就特別忙碌。在父親靈巧雙手的操弄下,一根根鐵絲變成了燈籠的鋼筋骨架,一張張彩紙變成了燈籠的花衣裳,再綴上金黃的燈穗,貼上“年年有余、馬上封侯”的剪紙畫或者“萬事如意”、“三羊開泰”之類的祝福語,一盞盞年年都不重樣的西瓜燈、猴子燈、八角燈、蓮花燈……最具技術含量的走馬燈就栩栩如生、活靈活現(xiàn)的誕生了。父親說,每個燈籠都是有生命的,那燃起的燭芯就是燈籠的靈魂,所以每尺每寸都認真編制,一絲不茍地完成。望著一盞盞大紅燈籠高高掛起,一戶戶人家和諧團圓,父親便會點燃一只鋼花牌卷煙,由衷而滿足地把眼睛笑瞇成一條縫。
印象深刻的還有正月十五、十六晚上,一幫孩子挑著各自的燈籠去“烘燈”。“烘燈”不知是不是當?shù)氐牧曀祝蟾攀钦f十六那天,孩子睡覺前引燃自己燈籠的同時,許下新年的愿望就一定會實現(xiàn)。那時候的我們可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只把“烘燈”作為一場可勁地哄鬧顯擺和比拼輸贏的游戲,一群半大小子相約在醫(yī)療器械廠門口,成群結隊地東院進西家出,一邊雄赳赳、氣昂昂地顯擺著自己的燈籠如何如何漂亮、精致,一邊激動地湊到一起用各自的燈籠作為武器相互碰燈,目的是要把對方的燈籠碰得燃起來,因為燈籠大多是紙質裱糊,里面點著小蠟燭,一經碰撞便很容易引燃,據(jù)說所有燈籠都被點著了,可是一個好彩頭呢。一時間你碰我,我碰你,追逐躲閃,大呼小叫,別提有多熱鬧了。
時光荏苒,歲月悠悠。如今家鄉(xiāng)的正月,滿城盡是霓虹爭彩,花燈斗艷,像流動的彩虹飄浮在平坦寬闊的街巷里,像五彩斑斕的絲帶拂過男女老少身旁,整個現(xiàn)代化都市沉浸在一片祥和繁華的喧鬧歡騰中,吸引著月亮仙子也輕移探春的碎步,羞答答地踏進家鄉(xiāng)的大街小巷,禁不住萬家燈火的歡聲笑語,揮舞著一席清冽澄明的云袖將漫天的璀璨星光輝映著遍地花燈點點、滿眼燈籠串串,伴著蕩過牛橋五塔寺的馬頭琴曲《祝酒歌》的喜慶旋律和響徹映紅扎達蓋河上空的煙花燦爛,一路穿越青山黑河,縈繞昭君故里,直把個青城點綴得處處流光溢彩、燈火輝煌,裝扮得青城人兒個個容光煥發(fā)、神采奕奕。置身于這片幸福安詳?shù)臍g樂海洋,終于懂了父親當年說過的每個燈籠都是有生命的話,那燈籠里燃起的火紅燭芯不正是一代代質樸可愛、造就美滿生活的家鄉(xiāng)人的不屈靈魂嗎,用善良和摯真為芯兒,用勤勞和堅強做骨架,這樣的燈籠高掛在心間,生生世世都會燃燒不盡,照亮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