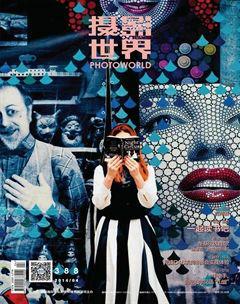新視界
吳曉凌



一年一度的“荷賽”,幾百幅獲獎作品亂花迷眼。但就像一本攝影史中所講,照片的計量單位并不僅僅是“張”,把“荷賽”的獲獎照片集合起來觀看,發現它竟可以被看作一個有機的生命體。仿佛從約10萬張照片中篩選出幾百件憑證,并把這些看似孤立的線索放在一起,描述、定義著這個世界的模樣,供我們采信。
如果只用一個詞來表達瀏覽過今年“荷賽”獲獎照片的心情,我選擇“欣慰”。這個世界并非沒有災難、戰亂、悲劇、不幸、絕望,但重要的是,通過這些照片,我們可以相信,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的力量在一直生長。
年度照片的基調
“荷賽”年度照片所涵蓋的意義就如同論文的論點、文章的主題,與其說它是最優秀的,倒不如說是“荷賽”最想傳達的。
在題為《信號》的照片中,移民們在吉布提海岸的月光下舉起手機,嘗試連接鄰國索馬里的廉價信號,好與國外的親人聯系。本屆“荷賽”評委愛德爾斯坦評論說:“這張照片帶出很多故事。它展開了關于科技/全球化/移民/貧困/絕望/疏離和人性的討論,那么有力、深奧,精致與細膩。照片拍攝得很巧妙,充滿詩意,意味深長,展現了當今世界這些引人關注的議題。”
本屆“荷賽”的作品,整體上超越了對事件、技巧、藝術和觀念等表象的迷戀,更深地聚焦于日常生活和個體命運。再復雜的物體,使用攝影再現都易如反掌;再簡單的關系,想用攝影說清都是挑戰。但在今年獲獎作品中,審視世界狀態,描述人與社會關系的照片俯拾皆是,并在年度照片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照片本身和照片所代表的傾向,奠定了“荷賽”的基調。
突發的災難與日常的“苦難”
今年的突發類獲獎照片,組照都有著真實、冷靜而殘酷的特質。一等獎作品《敘利亞自由軍襲擊檢查站》對拯救同伴過程不厭其煩地描述,占據了組照過半的篇幅,編排相當不“合理”,但所有照片,尤其是彈片橫飛的場景,讓觀者身臨其境,動容于戰爭的殘酷。這是個懸賞式的一等獎,關于勇氣,作為同行,我仿佛能聽到攝影師說:“不服?你來試試?”反正我是非常服氣。
人們已經習慣通過新聞來了解身外的世界,這么做有著天生的缺陷。新聞不僅喜新厭舊,還偏愛壞消息。遠處的災難和離奇更適于消費,收獲名利。
由此產生一個問題,如果只停留于觀看突發事件帶來的感官刺激,這個豐富的世界會不會被突發事件的霧霾所蒙蔽?
兩張單幅獲獎照片,詩化了對災難的表現。《臺風海燕》獲得一等獎,以其美與意義。《最后的擁抱》獲得三等獎,以其血淚與擁抱。
面對災難,人顯得渺小又偉大。即使失去一切,我們仍懷抱愛活著;即使失去生命,我們也懷抱愛離開。因為這樣的照片,遠方的苦難才不僅成為我們庸常生活的消費品,僅僅帶來刺激和絕望,我們得以飛越突發事件的霧霾,看到殘酷世界天邊的亮色。
僅僅完善與修正突發事件的表達也是不夠的,未知生,焉知死。生活很少直面死亡,更多要面對生存與發展的問題。眼前的茍且,詩與遠方。
卡蒂埃·布列松曾提到過一個概念—“日常生活的苦難”。他說,他更愿意表達日常生活中那些更為真切的“苦難”和對苦難的超越。
日常生活類組照二等獎《被占領的生活》,尤其是那張通過地道前往埃及赴約的加沙女子的照片是個再典型不過的范例。超過400萬人居住在加沙地區和東耶路撒冷,政治往往是日常生活的主調,人們的行動受限,受暴力的陰云籠罩。這組照片試圖發現人們歡愉的片刻,他們對生活的渴望,而不是僅僅為了求生。
在“荷賽”評選實踐中,突發新聞題材總要擠占一般新聞和日常新聞的獲獎空間。比如“臺風海燕”題材在獲得突發新聞類單幅一等獎后,又獲得了一般新聞類組照一等獎。敘利亞沖突題材《士兵的葬禮》獲得日常生活類二等獎。
即使如此,把日常還給日常,把一般區別于特殊。認真挖掘日常生活的苦難與表現極端境遇的苦難有著同樣大的意義,某種程度上講,更有挑戰。
顛覆的力量
對于這個世界和觀看者,美麗的照片是安全的,但我更喜歡觸動我的照片;然而相比觸動我的照片,我更喜歡顛覆我的照片。
幾幅安靜的照片,就有這種顛覆的力量。
一幅是一般新聞類單幅三等獎《絞刑前的瞬間》,倚在行刑者懷中絕望的頭,行刑者安慰的手臂,展現了生與死、善與惡、罪與罰、悔恨、無助……太多重的意味。
另一幅是肖像類組照二等獎《母與子》。在我的預設中,中東的照片只和沖突相關,不料突然闖進如此溫情精彩的照片,訴說著生命、成長、依賴與母愛,超越了種族的成見和局限,向所有人敞開—真讓人驚訝。在母親懷里,曾經是嬰兒的強壯男人,原來永遠是個嬰兒。
一般新聞類單幅二等獎《敘利亞阿勒頗的炸彈制作者》把鐵血戰士還原為人。他安靜地蹲在陽光里工作,一絲不茍,讓人不禁想上去和他攀談,聊聊個體和陣營,戰爭與人性。
今年“荷賽”比較觀念性的作品首推日常生活類組照一等獎《失蹤人口的最后服裝》。人赤條條來了又去,衣服不僅是種指代,更是線索,試著了解主人的性情與遭遇,懷念與控訴。觀念作品經常給人距離感,但這組照片雖然冷靜,卻恰當而真誠,沒有隔閡。
中國攝影師陳坤榮拍攝的體育特寫類組照二等獎《日常運動》也帶來關于兩個視角的啟示,航拍帶來拍攝視角的極大變化,但這種視覺新鮮感不是萬能的。最終起作用的仍然是表現視角。具體說,就是不能為航拍而航拍。拍什么,永遠是核心問題。怎么拍是技術的實現。
近年中國攝影師頻頻在體育和自然類別中獲獎,值得關注和總結。初步的結論好像近在眼前:它們是無關意識形態的組別,更多展現藝術創作能力,中國攝影師應該對自己藝術創造能力充滿信心。
其他類別的比賽,包含著對社會的觀察,要求足夠的思維深度,不同的價值觀和立場訴求也影響著中國攝影師的拍攝。中國攝影師需要具體分析的是,這些局限哪些是主觀的,哪些是客觀的,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臆測的。
要我說,解決辦法之一,就是用心表達“日常生活的苦難”。人性在這個維度,有著最深的共鳴和最少的沖突。
攝影是一種方法,不是技術,是一種確認,而非否認。按照這個句式,我們可以無限地接龍,攝影不是創作,而是發現。不是再現,而是改變。
視界什么樣子,世界就是什么樣子。很高興,今年的“荷賽”帶來了不一樣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