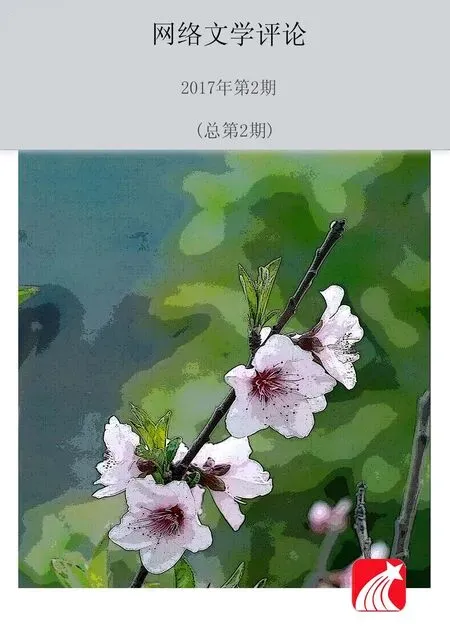打開網絡文學作品的多重維度
——以《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為例
文/羅先海
從1998年蔡智恒《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問世以來,中國漢語網絡文學發展已接近20個年頭。盡管作為中國當代文學新生形態的網絡文學已成為時下顯學,不僅創作量大、傳播廣泛,受眾益廣、批評者眾,且日益受國家高層重視,甚至成為從政府到學界,乃至民間一個繞不開的學術和文化現象。但昔日的“野路子”文學,與當下中國文學版圖三分天下格局中注重文化積淀的傳統文學,注重現實關照的市場文學相比,在讀者甚至批評家眼中曾一度存在風格單一,內容單薄,遠離生活甚至悖逆時代之嫌。以《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作為樣本,探究網絡文學的多重維度,意在呈示歷史化進程中經典網絡文學作品言說的豐富性,為推動網絡文學深度研究探尋可能路徑。
版本之維:老問題與新情況
書籍版本問題研究由來已久,古籍版本學就是關于這一問題的專門學問,新文學以來新書版本批評也成了一批學者開拓新文學研究的一座富礦,目前亦有學者從宏觀涉足包括網絡文學在內的當代文學版本問題。盡管各自關注點不同,但爬梳、考察作品版本變遷及譜系卻已然成為學術界的老問題。而網絡文學的版本之維乃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隨著電腦普及,利用電腦寫作或網絡文學創作誕生以來形成的一個新問題。從歷史性眼光看,有中國漢語網絡文學開山之美譽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也有較為清晰的版本譜系。傳統經典作品一般都會在作為前文本的手稿之后經歷“初刊—初版—再版(重印)—定本”的理想線性譜系,但網絡文學創作卻有所不同,主要表現為版本譜系源頭差異。以《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為例,該作是蔡智恒于1998年3月22日到5月29日期間,幾乎以每兩天創作1回(共34回)的速度,在BBS(網絡討論版)上在線完成。因引發網友熱捧,同年9月,這部當紅網絡在線連載小說(主要是在BBS上連載,有別于當下文學網站寫手“一日三更”式的創作)即由臺灣紅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繁體版初版(臺灣初版本)。1999年11月,知識出版社獲得該書版權,作為該社策劃“網絡書系”首本小說初版了其大陸簡體版(大陸初版本)。2008年9月,萬卷出版公司策劃《蔡智恒文集》,《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得以再版。此外,還有形態多樣的漫畫版以及作為腳本的越劇版、電影版、電視劇版等。
在版本譜系源頭上,《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以反復“key in”的工作形式完成了傳統創作意義上的“手稿”——網絡版稿本。與傳統創作“手稿”是在封閉式環境下由作者獨立完成不同,網絡版稿本在其生產過程就伴隨著與受眾即時互動,作品網絡版后記中說道:當post到了25集,原先預期的效應就開始浮現,信箱中出現了很多為輕舞飛揚求情的信件。于是我再度試著去改寫結局。直到有一天學妹告訴我:故事是你寫的,你的意見最重要。而傳統創作需待手稿完成并在初刊或初版本后才有與讀者互動的可能。另一個方面是物質形態差異,古書裝幀物質載體皆取材于自然界物質材料,如在甲殼、獸骨、石頭、竹木、絲織物、金屬、陶瓷、磚瓦上刻寫文字;造紙術與印刷術發明之后,不同性質的紙張成了書籍主要物質形態;而網絡時代寫作,電子媒介成為創作的主要載體。連載完成之后的網絡版是《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的最初形態,若網絡寫手是先通過電腦創作并儲存電子初稿,則在正式連載的網絡版之前還存在電子稿本形態。好的網絡文學往往都會完成線上連載到線下出版過程的轉變,線下出版也是對網絡文學的一種篩選和價值認定,出版機構往往通過對文字、結構等形式把關,甚至在商業意圖干預、意識形態規范內完成對網絡作品的紙質初版。《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臺灣繁體初版和大陸簡體初版就是這一過程的體現,有價值的作品當然更會在接受、傳播過程中一版再版,網絡文學作品因而就會產生從電子初稿到網絡版再到紙質版的版本之別。據統計,1999年《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拉開了我國網絡文學線下出版序幕(這也是該年唯一出版的一部網絡小說)。據數據統計顯示,隨后網絡文學的線下出版總體呈增長趨勢:2000年出版4部、2001年出版10部,2002年出版8部,2003年出版9部,2004年出版13部,2005年出版31部,2006年出版65部,2007年出版83部。①隨著出版體量的增多,統計難度也逐漸增大。因而有學者急于呼吁:“電腦寫作和出版產生的版本問題盡管已經存在,但似乎還沒有到被認真關注的時候。隨著當代文學史敘述對象的趨近,這個問題將越來越成為一個迫近的現實問題。”②作為新問題的版本之維也應納入網絡文學甚至整個當代文學的整體研究構架之中。
文本之維:小說的賦形
如果說版本之維是《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呈現給受眾可以形象感知的“實”的維度,指向作品的物質本性;那么文本之維則是指用語言文字所表達出來的組合體和語言交往形式,是可闡釋的“虛”的維度,指向作品的抽象本性。根據網絡文學所呈現的版本形態差異,其文本之維也略有不同。網絡版《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呈現給讀者的主要是語言文字表達的正文本,而初版本或再版本《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除了正文本外,還包括其周邊一些輔助性副文本因素。正文本是文本建構的主體,也是文本研究的主要對象。《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正文本,結構簡單,通篇只穿插了4個人物,主題也是通俗的愛情,但愛情故事的通俗講述卻披上了網絡外衣,凸顯了網絡文學當代賦形的價值意義。
劉大先在《當代小說的賦形問題》一文中提及,“文學創作為一個時代與社會賦形,是作家通過文字的形式對他所經驗與體會到的世界進行形象化的塑造,原本雜亂無章、紛繁疊復的事件、人物、情感與隱在的精神脈絡在文字中被整飭、修葺、冶煉、鑄型。這個過程如同修剪打理蔓草叢生的園圃,疏浚泥石堆砌、汊流四出的河道,那些自在自生的事物逐漸獲得了一個或者模糊或者清晰的立體輪廓,被認出來。”③《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面世后,不僅網上熱傳——包括臺灣、大陸、港澳、東南亞、美加地區、澳洲、南非……都有忠實讀者;而且網下熱銷——1998年9月在臺出版紙質版本,熱銷近60萬冊。進軍大陸市場,竟有30余家出版社爭奪版權,最后成為知識出版社盤中佳肴。④甚至因圖書熱銷還帶來各種影視版權改編,衍生出早期網絡文學產業鏈的端倪。盡管如此,對《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文本的闡釋和評價仍應中肯,既不主張過分抬高其文學價值,畢竟所講述的通俗愛情故事并不及傳統經典文學的價值深度;也不主張過分苛刻看待作品,認為“痞子蔡的文字泡沫,正在四處飛揚,這不是文化沉淪,文學衰敗的象征又是什么?”⑤客觀而言,《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非常成功地完成了網絡時代的小說賦形,在這一點上既掩蓋了其深度缺陷,也為它贏得了受眾追捧。
這種賦形首先表現在新鮮、時尚的“網戀”主題。上個世紀90年代末至新世紀后,電腦已經在社會上較為流行和普及。當時大學生尤其是理工科學生,以及剛踏入職場的計算機相關行業人士都是較早一代“網蟲”,大家普遍用文字在網上聊天,開玩笑,發表小說,通過網絡抒懷、感嘆、嬉笑怒罵,甚至談情說愛,發現很多現實世界沒有的樂趣。這正是新興電子媒介時代潛滋暗長,也是前所未有的國民生活乃至精神之“形”,盡管俗而不雅。這種新鮮而又渾然的生活世界是既不同于阿Q時代的愚昧壓抑、也不同于小二黑時代的單純明朗,和池莉“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的瑣碎乏味也相異。因為虛擬網絡的聯通在無奈世界里又增添了一點現代的浪漫和后現代的傳奇。談及為什么選擇愛情故事?也是因為“發生在周遭的或較容易引發寫作欲望的,通常是愛情或友情 ,不止我如此,那時以‘網絡’或‘網戀’為題材的網絡小說相當多。”⑥可見,面對身處世界的新變,很多人都在嘗試通過自身經驗與體會去捕捉新生網絡世界和網絡生活之“形”,但首獲成功卻只有痞子蔡和輕舞飛揚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兩只“網蟲”由網絡邂逅,進而互侃“咖啡哲學”“流體力學”,美麗的約會和浪漫的香水雨讓無數讀者向往傾慕。作者在網絡版后記中描述:在故事接近悲劇結局時,就有網友求救,萬一真要寫悲劇,也請在結局留下一點希望。所以作者又將故事的最后一幕由殯儀館移到醫院,將L君的輕舞飛揚,換為成大中文的一位美麗的輕舞飛揚,也將兇手由闖紅燈的砂石車,變成蝴蝶病。可見,網絡上的悲劇與現實中的情緒已經交融,成為《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為網絡社會和時代賦形的共鳴表征。
這種賦形共鳴的產生還來源于文本中幽默風趣“蔡氏網語”的獨特運用。不僅表現在大量當時流行且帶有共性的網絡用語,如恐龍、青蛙、當機、美霉、ID、MAIL等等,來突顯小說語言的精彩。更表現在其獨特的個性網語,如開篇詩體的plan:
“如果我有一千萬,我就能買一棟房子。
我有一千萬嗎?沒有。
所以我仍然沒有房子。
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飛。
我有翅膀嗎?沒有。
所以我也沒辦法飛。
如果把整個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澆不熄我對你愛情的火。
整個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嗎?不行。
所以我并不愛你。”⑦
類似的還有文本結尾處,輕舞飛揚又以幾乎同樣詩體的藍色的信結局:
“如果我還有一天壽命,那天我要做你女友。
我還有一天的命嗎?沒有。
所以,很可惜。我今生仍然不是你的女友。
我有翅膀嗎?沒有。
所以,很遺憾。我從此無法再看到你。
如果把整個浴缸的水倒出,也澆不熄我對你愛情的火焰。
整個浴缸的水全部倒得出嗎?可以。
所以,是的。我愛你。”⑧
通過這種假設前提推定愛情(不愛或愛)的句式,前者以諧謔的自嘲呈現了一個文明“痞子”,后者以誠摯而又難以挽留的悲傷展現了多情卻又凄婉的“輕舞飛揚”。在這種語言形式美感中,從開頭的諧謔到結尾的真摯展現了網絡愛情的時代境遇。這種詩體plan受到的熱捧從網上延伸到網下,絲毫不亞于當紅流行歌曲的大眾傳播力度。此外,文本中大多依靠痞子蔡和輕舞飛揚的對白推進情節,對話中兩人多是互侃,侃得很犀利,很有趣味,很夸張,同時又很有藝術,這也是文本深得大眾喜愛的原因之一。有網友評價,“對我來說,‘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不只是個故事,它更是新媒體和舊媒體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這是第一部純網絡的文學作品,不管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展現了大眾小說的新方向。”⑨作品通過賦形所展示的網絡世界并不是無中生有,而是作者建構的與現實世界構成某種關聯的文字世界,是作者對文本內外兩個世界經驗與體會的藝術表達。
空間之維:副文本的闡釋
空間之維指向作品線下初版或再版形態的文本層面,是指作品由正文本和其橫向層面大量副文本因素共同構成。“副文本”是法國文論家熱奈特在其跨文本文論研究中最早提出的概念,后又有學者對此概念進行修正,以使副文本概念內涵和外延更適合中國文學研究的實際。指出“‘副文本’是相對于‘正文本’而言的,是指正文本周邊的一些輔助性文本因素,主要包括標題(含副標題)、序跋、扉頁或題下題辭(含獻辭、自題語、引語等)、圖像(含封面畫、插圖、照片等)、注釋、附錄文字、書后廣告、版權頁信息等。⑩正文本是文本建構的主體,而副文本卻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實質上,副文本不僅是整個文本的有機構成部分,且與正文本形成重要的跨文本關系,是保存文本歷史信息,闡釋文本不可忽略的因素。
《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網絡版也有副文本信息,如標題,只是作為源頭的網絡版本副文本因素不豐富,不明顯,且副文本意識還處于不自覺狀態。其臺灣初版本或大陸初版、再版本作品,往往是作者和編輯、研究者、出版商和廣告商等復數作者集體參與,通過多方力量較量、利益博弈,共同形成了布迪厄所謂的“文學場”。較明顯的是《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臺灣初版本在作者和編輯之間有過一場關于標題、序言等副文本因素的磋商,大陸初版本火爆市場也與知識出版社積極主動的商業運作分不開。
標題具有較強獨立性,是與正文本聯系最直觀,且對整個文本起到概括和控制力量的副文本,它是打開文本的窗口,對文本的闡釋起到某種導引和界定作用。“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總體就給人一種曖昧印象,為全書定下言情或戀愛故事基調,在網絡連載時網友“可愛小女巫”就對標題發難:“老實說,‘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真是個爛名字!!!它嚴重地欺騙了我的感情…一開始,因為它曖昧的名字,我以為,或者說,我希望它是一篇不用動用大腦與感情的情色文學;我興致勃勃地從夜貓叫春的三點一刻,等到?男女主角在麥當勞的七點相會,情緒一點一滴地向下滑落…搞什么嘛!?連手都沒碰……” (引者注:所引為網友語言原貌,不符合規范的標點未作修改)可見標題有一種文本闡釋先入為主的優勢。作者也許只是無意中取了一個奪人眼球的書名,網絡版后記曾自述:其實光看篇名就知道我是個不諳創作的菜鳥,連名字都不會取。出版過程中編輯小姐對書名有意見,認為加了“的”字,念起來有些拗口,但作者認為“的”字很重要,不能隨便省略。因為刪去“的”字后是強調“第一次”,而保留“的”字重心在后,強調“親密接觸”,不僅保留了標題韻味,且更符合文本所營造的一場只屬于痞子蔡和輕舞飛揚指尖記憶的網絡浪漫邂逅。甚至在出版商眼里,“書名對圖書也非常重要,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中“的”字很重要,暢銷書的書名特征必須便于口頭傳播,有一個好‘口彩’”。 該書出版后,書名即受矚目,不僅書市上陸續出現署名“痞子蔡”的第二次親密接觸、再一次親密接觸、又一次親密接觸、無數次親密接觸、最后一次親密接觸等偽書,而且報刊雜志標題到處開始出現仿寫“××與××親密接觸”現象,這就是標題效應。
上下游圍堰雖然采用了高噴樁防滲處理,基坑第一節降水也已形成,地下水水位有了明顯下降,但在整個降水系統尚未完全建立前,地下水水位、承壓水水頭都很高,不易成孔。因此在河道清淤后,在河道內填筑2 m厚黃黏土(填筑后頂面高程約為-0.5 m),既為灌注樁的施工提供了平臺,又減小了承壓水水頭,為樁基在高水位狀況下順利施工創造了條件,加快了工程進度。
序跋內容最長,是進入正文本所享資源最豐富的一條門徑。作者一般借序跋闡釋著述原委、寫作動機、作品主旨,甚至交代一些作品版本源流信息,是我們接近作者意圖,闡釋正文本原意的重要史料依據。蔡智恒《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網絡版(BBS)“后記”,交代了創作原委,甚至把作品人物原型及命運走向都做了本事意圖解釋,是了解并闡釋文本的重要資料。可惜這篇網絡版“后記”在正式發行的紙質版中未收錄,因此很多后來讀者都無法準確理解文本的本事意圖。大陸初版本(知識出版社)收入了北大學者張頤武《序〈網絡書系〉》作為該版代序,當時網絡文學作品在大陸出版還未有先例,市場是否接受,讀者是否歡迎都有待檢驗,出版社也是冒著向銀行貸款100萬的風險來做大陸市場第一部網絡文學作品,所以收入知名學者序言既是對作品的肯定,也是對網絡文學市場的預期。大陸初版本以《痞子蔡的——感性宣言》作為后記(跋),相比于網絡版“后記”,少了一些文本本事意圖闡釋,而多了一層冷靜的自嘲和感懷。大陸再版本(萬卷出版公司)收入作者自序,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臺灣初版本出版過程信息,也對初版本不規范網絡符號進行解釋,為讀者進一步了解文本原貌提供了豐富的信息來源。該版以作者所寫《寫在〈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十年之后》作為跋,交代了很多創作動機和原委信息,是解讀文本的重要材料。不同序跋既為文本闡釋提供豐富信息,還成為鑒別不同版本的重要依據。
封面和插圖是與正文本內容緊密關聯的圖像副文本。《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大陸初版本,在封面設計上追求奪目、突顯、有視覺沖擊力,用純正的紅色,不僅明快亮麗,敦厚大方,而且較強烈的視覺感使圖書在書攤上別具特色,能很快進入讀者眼簾,再加上封面標注“網上第一部暢銷小說”,更符合其打造暢銷書的市場定位。書中插圖作為副文本因素則更能進入正文本闡釋的內在肌理。正文中10個章節,每章前均附有插圖(該書插圖為電腦印制,不同于傳統作品的手繪插圖)。正如魯迅所言:“書籍的插圖,原意是在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種宣傳畫。這種畫的副數極?多的時候,即能只靠圖像,悟到文字的內容,和文字一分開,也就成了獨立的連環圖畫。” 正文本插圖恰好可以填充文本空白,如大陸初版本第二章《輕舞飛揚》就配有一張如蝴蝶斑輕盈張開雙翅的長發女子;第四章《見面》配有夜色朦朧的海邊和沉寂淡雅的陽傘、桌椅圖片等,這些插圖往往都與章節內容氛圍吻合,為受眾營造期待視野的同時,也提供了闡釋文本的空間。
附錄雖與正文本互文深度較淺,但在《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中卻是不能忽視的副文本。臺灣版初版本中收入了很多“朋友的話”和一篇“編輯的話”(大陸初版本也收入,但再版本卻刪掉了),這些附錄資料在時過境遷后仍保留了網絡初生時代的歷史現場感,是觸摸和了解網絡文學作品歷史現場難得的史料。具有同樣效果的還有大陸初版本附錄的“痞子蔡的留言板”,使我們至今還能感受到作品當年連載時網上熱傳的氛圍。類似的附錄信息成了我們返回網絡文學歷史最好的在場信息,是不可或缺的副文本因素。
歷史之維:作品的成長
歷史之維主要側重“縱”向歷時性的?作品修改史、文本變遷史以及編輯(含出版者)等參與史,會導致一部作品形成不同的版本,如初刊本、初版本、修改本、定本等等。 經典網絡文學作品理應有其作品變遷史和成長史,主要涉及版本的演進和文本的修改。
原始網絡版不易保存,已經成為困擾網絡文學歷史化研究的實際問題。隨著網絡技術快速更替,《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連載時的BBS早已成了塵封往事,蔡智恒個人主頁及Blog地址也湮沒在茫茫網海,如今要想再睹十多年前作品的網絡原貌已成奢談。也許當下很多網絡文學發表的網絡版還能查詢,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后,技術更新導致初始網絡版保存不穩定問題仍是目前網絡文學研究面臨的困境,這是涉及如何更長時間乃至永久保存原始電子文獻的技術和學術問題。網絡文學在線創作的網絡版,好比傳統作家創作的手稿和當下部分作家電腦創作的電子稿。當“手稿”、“電子稿”或“網絡版”在線創作剛形成時,保存這些原始初稿版的價值往往不會被馬上意識到,但隨著歲月流逝乃至不斷修改,在作品傳播接受過程中乃至逐步經典化之后,這些初稿本又會成為作家作品研究和返回文學歷史現場的重要史料,其價值才會被突顯出來。
從網絡版到紙質版,是優秀網絡文學作品傳播和接受的必經階段,不同版本的修改也是作品成長的重要一環。之所以強調出版環節,是因為出版過程本身便是對作品的篩選、修訂和加工過程,是網絡作品不可缺少的程序,也是必經的門檻。以大陸出版為例,《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初版本最大限度保留了網絡版的真實情況,是我們較能真實接觸作品原貌的版本形態。初版本標點中有很多不符合規范的符號,如“...”和刪節號“……”,只是因為“在鍵盤右下角有個‘Del’鍵,上頭就是一個小數點(.),于是?網友們打字時不必長按切換鍵,順手按幾下Del鍵即可表示標點,兩點、三點或四點,隨你高興。手指容易抽筋的,多按幾點有益健康。” 至于正文中長短句形成的段落,也是因為BBS上的文字接口不具備文字處理軟件功能造成的。而單引號‘’和雙引號“”不規范的使用,是計算機上閱讀比傳統紙張閱讀不舒適,比較不便捷,若出現對話較多的段落,一連串的單引號容易讓?人搞不清楚話是誰說的。因此痞子蔡的話用‘’,輕舞飛揚則“”,如此可以凸顯視覺差異,在計算機上閱讀小說中的對話時較易判讀。 且初版中收入大量當時網友在線留言的“痞子蔡的留言板”和“朋友的話”以及“編輯的話”,都最大程度上為后來的讀者保存了其創作連載和引起反響的初始形態,在技術不斷更新的情況下實現了網絡初稿版價值延續的可能。
從?初版到再版,正文本內容并無大的修改,但萬卷出版公司“新版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中,文字敘述盡量使用了正確的標點符號”, 這是版本演進過程中非常必要的一環。因為不規范標點符號的使用和長短句的形成皆是因為客觀歷史條件限制所致,如今這些問題早已成為過去,若不修正,可能會對讀者接受和作品進一步傳播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造成文本誤讀。大陸再版本較之初版本,不僅盡量使用了正確標點,對于影響讀者接受的長短句段落也有局部調整,更利于作品的解讀和傳播。難能可貴的是再版本增加了作者自序和《寫在〈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十年之后》,序跋文中交代了作品初版過程、初版內文部分問題的解釋、創作原委等信息,這些資料都讓新版本或初版本意義不斷增值。
從歷史之維來看,《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網絡版已成為過去和歷史,但其生命和精髓卻能在紙質出版中得到延續,若作者能有機會為作品再次修改或定本,期望能在修訂不規范標點和段落的再版本基礎上,把其網絡版“后記”修訂收入,且以附錄形式保留初版中類似“痞子蔡的留言板”這些鮮活的歷史細節信息,如此便會形成一個信息更多維、細節更真實,且不斷成長的網絡文學經典作品新版本。
注釋:
①歐陽友權:《網絡文學發展史 漢語網絡文學調查紀實》[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301頁。
②趙衛東:《略論當代文學的版本問題及其處理原則》[J],《漢語言文學研究》,2016年第3期。
③劉大先:《當代小說的賦形問題》[N],《文藝報》,2016年6月27日第2版。
④徐鋒:《〈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火爆書界 “網上文學”嫁接圖書有待觀察》[N],《中華讀書報》,1999年12月29日第3版。
⑤蘇陽:《劉墉·金庸·痞子蔡》[J],《文學自由談》,2001年第6期。
⑥新京報社:《〈新京報〉對談痞子蔡》,《日志中國:回望改革開發30年》[M](第四卷), 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149頁。
⑦⑧蔡智恒:《第一次的親密接觸》[M],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71頁。
⑨蔡智恒:《第一次的親密接觸》[M](朋友的話),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
⑩金宏宇:《中國現代文學的副文本》[J],《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
?蔡智恒:《第一次的親密接觸》[M](朋友的話),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劉擁軍:《圖書營銷案例點評》[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頁。
?魯迅:《“連環圖畫”辯護》[A],《南腔北調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頁。
?金宏宇、耿慶偉:《文學文本四維論》[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6 年第 2 期。
??? 蔡智恒:《第一次的親密接觸》[M],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1、12、14頁。